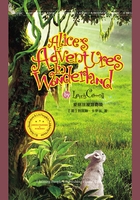推开门,就看见您微闭眼睛,坐着,悄无声音。
一墙之隔的邻居,是一个快言快语的妇人,我听得清她亮着嗓门议论谁家儿子考上了好大学,李家的水果摊缺斤少两;她的两个虎实实的儿子,还因为谁更崇拜纳什和科比,时时展开震动了屋顶的唇枪战,动静最大的,当属他们的爷爷,没有一个周末,不把收音机调到最大,欣赏地道的黄梅戏。妈,这一切,您都蒙在鼓里,您既不知道这位胡子花白爷爷的寿庚,更没有打听他有着很多美丽桃花的老家在哪个方向,您只是安静地坐着,旁若无人地闭上眼睛,甚至也看不出您怨怼自己可恶的耳朵。
时常,我兴致盎然地逛来自北京、上海的商品展销会,或者采访市里春节团拜会的彩排,要么是看到街头,密密实实地围了一群人,原来是谁家的媳妇因为丈夫不轨,撞死在行车道上的一辆东风卡车上。我一路唏嘘着回到家,妈,您安静地看着我笑笑,脸上没有任何风浪。我就很痛心地思忖,您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外面的世界有多丰富,您知道吗,您也许没有看清我的疑虑,您或许是根本不去理会,只是转身默默地进了厨房,细心地做红油面条或是带有鲜汤的米饭。
其实,有些时候,您再三地挑选了中意的衣裳,换上了舒服的软鞋,并且用清水抿湿了额前脑后的头发,把一点零钱用柔软的手绢仔细包好,才“啪”地关严了门。您到离家最近的公园,看跳健身操的女人,看推小车照看孙子的老人,看卖热豆腐的喧闹场面,还有不远处看自行车的那个穿浅紫衣服的妇人。妈,您走近时,试图要与人家随意地聊一些什么,但您的耳朵和因耳朵失聪含糊不清的说话,只能让他们很奇怪、很莫名地看着您,然后,极没有耐心地扭过脸去,给您一个冷冰冰的后背,他们其实是弄不懂您的意思,妈,不要伤心。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宁愿相信,您并没有为此真的懊恼。
大街上天天都发生数也数不清的故事,数也数不清开心的玩笑和暖人的事件,电视里热播的连续剧,即便是如此这般地极尽死去活来之能事,也打不动您的心,因为,妈,这一切您都蒙在鼓里,您都无从知晓,连中国有多少人、世界是个什么、版图是怎样的一个雄鸡,对您都是一个永远的秘笈。
活着,真是太没意思,太可怜、太孤寂了。
还有父亲,有时,他会无端地打断您的话,还有的时候,因为一句话重复多次,而您仍是不知所云、一片茫然,他就暴跳如雷,把东西摔得山响。妈,您实在是不会有别的办法,来获取一丁点的声音,您只有什么都不问,可什么又都不放心,我看到的是您更加惶惶然的焦虑,和更加惶惶然的无奈,但是,您只是安静地坐着,像一个无辜犯错的乖女孩儿。
您看您的孩子,南一个,北一个,东一个,总也难得聚在一起,更别说像小棉袄一样膝下承欢,您又恨又爱那个大红色的电话筒,它丁铃铃的响声再三再三焦急地喊叫,妈妈您也是浑然不觉地闭着眼睛,无聊地打盹。就算是把“妈妈”二字喊得再深情再甜腻再有声有色,您也蒙在鼓里。
于是,我就天真地幻想,如果您能像别人爽朗健谈的妈妈多好。但是,每天每天,您只是呆坐着,盯着自己的脚尖,守着一个空荡的屋子,好像这个热闹的世界与您无关,甚至您的孩子也与您无关,妈,恍惚间,我真想不明白,您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勇气,让您一日日如此的淡然、如此寂然地一语不发?
我不知道,有一种怎样强大的动力,如此顽强地支撑您、锲而不舍地期盼着、热爱着这一天天的日子!不知道是什么让您从不厌倦这份不善言辞的孤独,不在意路人对您毫无缘由的轻视,不记恨那些刺伤心灵的傲慢,从而默默地守着您孤零零的安静,我不知道!
灵魂,是一颗成熟了的童心,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这个人与上天的秘密。
可是,您永远地走了,晚上,在浅白色的台灯下,我想起了您,曾经您就坐在我身边这个棕色的椅子上,悄无声息。此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个苦苦困扰的疑惑,明白了您为何隐忍了那些伤害,为何活得那么淡定和天真,是因为,您早就知道,您对于我们——您的孩子们,是多么重要,您是我们在这个繁复世间所不能代替的唯一,您坐在那里,我们就有一个妈妈,就有一个什么都不缺失的世间,您是以一个母亲的博大与卑微,安安静静地寂寞,这个,您早就知道。
您看看您的孩子南一个,北一个,东一个,像一个个惊恐的鸟儿扑楞楞地回来,从各自不同的那些热闹地方回来,回来也没有挽留住您悲怆的脚步。
妈,只要您活着,不必像别的健谈的妈妈,不必知道新闻里那场动人心魄的现场急救,其实,您什么都不必弄通弄懂,正像曾经,安静地坐着,您就没有失败,没有灰心,就是上苍对我们万分的恩典。
我想,是因为,我们彼此,如此的重要,您才不在意对整个世界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