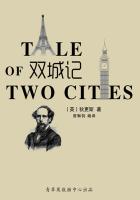以为这晚能与家人挤进包厢一聚,混在人群中为孩子唱唱欢快生日歌,做好了沾染点热闹的准备,可却又变成独自一人的漫漫时光,像进过一个旖旎梦境,提早醒来一无所有,只剩长夜,更显空虚。
出门走下台阶,烈风扑面,溪川昏昏沉沉,缩颈拽起衣领,跌跌撞撞踏上缓缓驶到眼前的车里。
车窗外金色车灯川流不息,她汇进河中央,却不知该去向何方,摘下墨镜露出迷惘的眼。
不想回家,家中也是空空荡荡。
车上就有酒,足够一醉方休,醉之前她嘱咐司机保持行车,无所谓开到哪里,她只当坐进小船,享受摇摇晃晃浮浮沉沉。
家人朋友都隔了心,一个不剩,如今连初恋也不再是初恋,全世界没有一处与她相连。努力伸出手想抓住什么,捏紧了手心才发现肥皂泡一个个碎掉。
司机携她兜兜转转三个半小时,应了一句歌词,往城市边缘开。终于没再听见后座声音,回头一看,大小姐梦得很深。
这种无法定夺的时刻,只好致电让老板拿个主意。
易辙刚结束饭局从夜场脱身,听了汇报默默皱一皱眉。
她家有人能自由进出的怪事还没破解,人事不省地送回去怕不安全,以她的身份横躺进酒店怕又被曝光节外生枝。他权衡再三,让司机把人送往自己家去,他也从另一方向动身汇合。
抵达时间不差三五分钟,车门拉开,密闭空间里酒香浓郁。
她睡得很乖,眼睫一动不动,脸颊烧红娇娇可爱。轻薄的羊绒大衣没有纽扣,只在腰间虚虚系住,玫粉色衣裙张扬地露了一半,零下几度依然光脚穿单鞋是女明星的独门绝技,12厘米鞋跟好似冰锥。
易辙头疼地揉揉太阳穴,俯身进去把她拦腰捞起来。
她毕竟无意识,动了动侧脸紧贴他胸口,双手都勾过去,嘴里却冒出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称谓:“爸爸??”
夜色中清晰可闻。
司机憋着笑,用关上车门的巨响来掩饰。
易辙的脸色像刷了层漆却不复威严,只好转身走得更快,好在怀中人轻如羽毛,不怎么费力。
溪川被卸下鞋就扔在床上,他先管了自己再管她。
外套往衣架上挂好,回头看她慢吞吞侧过身。
他应酬时也喝过酒,话比平常多:“你喝这么多,酒量却总不见长,没天赋也练不出来,图什么?”
她微张了眼,转过四分之三张脸,望他半晌,好像在苦思冥想这是谁:“图醉生梦死,快乐无边。”
他屈膝坐她身边,一手抽开腰带,一手恶作剧似的捏一捏她的脸:“明天又要浮肿,看你怎么上镜。”
“我要请病假。”她像装病赖床逃学的小孩,一说谎先傻笑起来。
“什么病?”他手上宽衣解带动作没停,从衣柜里翻出睡衣往她胸前扔过去。
她蜷腿坐住,把一件衣服正反翻弄来回看,犹如看不懂怎么穿。
醉得只剩下单细胞,易辙叹口气,指望她生活自理根本不行。
她也自知不行,放下睡衣讨好地冲他笑:“轩辕??”
这是终于想起是谁了,叫他从前的姓,语气又是撒娇,听得他很恼火,想起刚认识那段时间她就这样,天生演员,撩人是拿手好戏,撩过又拒人千里,心猿意马反复无常,翻脸比翻书还快。
她需要拥抱又怕被欺骗,矛盾不能自洽,饿极了吃饭,吃饱了摔碗,都是本能。
好歹他也不羁年少过,从来都是他片叶不沾身,没有任人挑逗玩弄的道理,高手过招,输在比她多有一颗心。
这人酒戒不掉,戒人倒是利落,没人能治得了。
明知是妖精,叫你的名字哪敢答应?
他皱着眉直接把她塞进被子,眼不见为净:“不会穿别穿,睡你的觉。”
她连脑袋都藏进被子里,好像快活安逸。
他自己去隔壁洗澡,水要冷,心更应该冷,多想想她的薄情寡义就能达到效果。同样是酒后真言,她说过:“世界这么无聊,不过一起杀杀时间,许你玩游戏,不许我玩游戏?我也没有拦着你不让找别人,谁要认真都变得无趣。”
他想想没错,划清界限的时候她就很认真,的确无趣。在公司要拉开距离,避免闲言闲语,条条框框多了一堆,设限的总是她,毫无意义。一个戏子,身姿摆得再正,在别人眼里都是男人床上睡来睡去,谁管你那摇摇欲坠的名誉。声称要及时行乐又放不开,横竖都是她说了算。为此跟她吵过架,可吵架谁能吵得过她,牙尖嘴利,到最后觉得自己也过度认真了,变得好无趣。
这样若即若离,神经被碾断许多回,已经十分迟钝,她要做什么他只管配合,不再去动一点脑筋想动机原理,工作上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哪还嫌神思空闲。不过总是有心冷到底的错觉,随便扫她一眼又热起来。
她肯定被憋坏了,早就凭本能钻出来呼吸,胳膊夹着被子一侧卧躺,顾头不顾尾。微弱月光下,整个后背裸在外面。
他可不想像个保姆给她盖被,那还叫男人?自己到处漏破绽怪不得别人。
扔下浴巾,带着未散的水蒸气,从身后把她揽住,体温飙升。
叫她名字也叫不醒,确认了可以放胆胡闹。
她一觉睡到日上三竿,还肌肤相贴醒在男人怀里,吓得魂飞魄散,从棉被里把自己当鱼雷一样弹射。
易辙眼睛都没睁,翻身躺平,抬起一只胳膊盖在眼上挡光:“跟剧组请假了,说你也被传染感冒病倒。不好说女一号失心疯喝到烂醉如泥,传出去丢人。”
她头痛欲裂,卷着被子坐好,佯装镇定:“最后把我送你这来了啊。”
“深更半夜没有垃圾回收站营业。”他遮着半张脸,主要是不敢露脸,佯装坦荡,生怕一句话露怯激得她跳下床直奔厨房提刀回来。
房间里静下来,剑拔弩张。
她感受到那根从左侧太阳穴穿到右侧的无形钢钉,到这地步还想回放出什么残存记忆,只能从他露的半张脸上搜索作案证据。
他被沉默逼得冷汗森森,决定干脆先发制人,抬头蹙眉瞪她:“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理直气壮的态度让人不禁自省,是不是失忆中干了什么惹他不高兴的事?
她满腹狐疑躺回被子里,睡意全无又不敢再动,还不如先想一想,手机放在哪里。摸了摸枕边,没有。这又不是自己家,他哪会那么贴心。
手里没东西消磨时间,以她的性子连一刻钟也熬不了,看落地挂钟秒针走过一圈,就跳下床自力更生去冲澡清醒。
隔间门关住,他才长吁一口气,偷笑庆祝劫后余生,又不免嘲笑自己,不过成年男女耳鬓厮磨,何必这么怕她,好像惧内。有些人也是,看着是母老虎实际是纸老虎。
一句腹诽还没想完,纸老虎突然猛地拽开推拉门,探出个水淋淋的脑袋,又吓得他无端哆嗦一下,幸好她被水糊着眼没注意。
“我洗发水呢?”
她在这里本来是有一套东西,可是太久不来,他嫌占地方认为过期就给扔了,说出来又成了欠她的。
他啧一声:“挑什么?就用我的会死?”
“你的洗不干净发胶。”
说得好有道理,竟让人无法反驳。
只好爬起来出门给她找,找的是储藏室里没开封的一套,扔了她的总要留个退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而然就变成这种奴才伺候主子般的局面,做人应该有点骨气。
易辙把新洗发水拆了封搁在浴室外地上敲敲门,等她伸手出来拿。才不是主子,分明是宠物,这么想才心理舒坦。
他在另一个房间洗漱完,回床边发了半天呆,她才裹着浴巾出来:“我的衣服呢?”
语气不客气,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跟在他身后,又追加一句:“我还要吃药。”
“什么药?”他动作慢下来,回过头。
“布洛芬。”
“怎么了?”
“头疼。”
“活该。”他继续翻箱倒柜,找出两条裤子,发现怎么也找不到衣服,才想起昨天跟她置气,把睡衣从她手里拽走直接扔床边地上了,绕到另一边床侧捡起来拿给她。
她没有接,脸上明写着“地上的脏衣服我不要”。
要把这件事捋清,势必涉及讨论“谁扔的衣服”之类细节,他才没那么容易中招,简单粗暴把衣服蒙她脸上,爱穿不穿。转身出去找药,回来她还坐那里,衣服扔一边,瞪着他,犟得要命。
他不跟她一般见识,把药塞进她嘴里,也随她爱吃不吃。自己拿起手机翻阅公事信息,前三条是广告部门的琐事,只需回复“好”,第四条来得更早,六点多钟,是他刚替她请好假睡回笼觉的时候,底下人征求意见:溪川早预定好的综艺,明天就要录制,今天一早得到消息杨雪也要挤来上同一期,要不要推了改期?
郭俊那事之后,吴澜才消停了几天?连双方粉丝骂战都还没平息。她也真精力旺盛。
易辙边回微信边问:“杨雪要跟你上同一期综艺,不行吧?”
溪川把含了半天的胶囊硬吞下去:“当然不行了这不废话么。”
他听这一声蜂鸣警报,诧异地抬头,看她像火苗一样窜起来,心想您也精力旺盛,突然起念逗逗她,笑着继续往手机里输字:“不如一起参加吧,谁不想看女明星扯头发打架?”
她居然当了真,伸手来抢手机:“扯秃了算工伤?你负责?”
“我负责。”打打闹闹多幼稚,他刚发完消息,不屑地扯着嘴角仰脸,任她把手机抢过去。
确认了已回绝才罢休,却不想一个失策重心不稳,人跌在他身上,头还是晕,被他吻住两秒才醒过神。
四目相对,火冒三丈,有人平日戏里戏外勤于练手,耳光扇得娴熟。
他气定神闲把脸转回来,像只被摸了一下:“今天请假,明天旷工,扑到我身上来杀时间,又想玩什么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