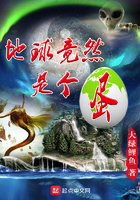包祥失踪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申的耳中,这一下真是吓得他六神无主,昊天惊雷。一边把家中的家丁全部散出去寻人,一边赶忙来到县衙,请县令大人拿主意。
县令林尚荣正在床上和他的姨太太们快活,忽然听人来报,连外面的衣裤也来不及套上,穿着内衣便滚下了床。
一见王申便劈头盖脸一顿骂,直骂的上气不接下气,瘫坐在太师椅上。堂下跪着的王申,身如筛糠,他知道这次闯下了弥天大祸,只得一声不吭,任他数落。
林县令坐了半晌,这才喘过气来,喝了口杯中的凉水,盯着王申问道:“他知道多少?”
“大人,这……小的所有事情都是派这个亲随出面……”
“这么说,克扣赈粮、买卖人口……他是都知道了?”
“是,”王申说这个字时,只觉得喉咙发干,浑身无力。
“你个蠢货,”林尚荣怒不可遏,手中的杯子一下摔到王申脑袋上,“啪”地一声脆响,碎的满地。
王申只觉得脑门金星直冒,一些粘稠的液体顺着头发滴到肩上,可是他连动也不敢动,依旧跪的笔直。
林尚荣还是不解气,走下堂来,用脚狠狠地踹向王申的胸口,直将他踹得翻倒在地,喘不上气来。“你个蠢货,你个蠢货……”
王申擦了一下嘴角沁出的血,战战兢兢道:“小人的错,小人的错,小的已经派出家中全部人马,前去寻包祥下落,大人恕罪啊!”
林县令俯下身子,正对着王申的耳边喊到:“我早就吩咐过你,我们的事情不能只交于一人之手,怕的就是有这一天,如果那个包祥是落在阎罗王的手中,再一交代,咱们一个也跑不了,通通人头落地,说不定还要灭九族!”
“不会,不会的,大人。包祥随我多年,一向忠心耿耿,就算……就算是被那阎敬铭抓去,量他也不会出卖我,出卖大人……”
林尚荣啐了他一口痰,“呸,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了?什么人最可靠?人最爱惜的是什么?”
王申忙道:“小的不敢忘。大人说过,人最惜自己的命,死人最可靠。”
“你这个蠢货,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如果早些把他灭口,又岂会落到今天这地步?”
王申哭笑不得,心想,他是我的左膀右臂,哪有人会没事时自断臂膀的?可口中却不敢如此说,只道:“大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您给小的出出主意吧!”
林尚荣一时沉默不语,盘算着。他心中自是焦急万分,可如今再分对错为时已晚,自己和王申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这个船一翻,一个都别想逃。为今之计,只有尽快确认包祥的下落,如果他是自己逃走或出了其他纰漏,那还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如果他真的是被阎敬铭这个阎罗王抓去了,那就必须快刀斩乱麻了。可是如何确定他有没有落入阎的手中?如果落入阎的手中,那他是招了还是没招?这有得两说了。
“王申,你听着。你先去派人将衙中所有人等全部派出去,寻找包祥。一旦找到,立刻押回县衙,不得有误,如遇反抗,格杀勿论。就算把新平县城掀过来,也要找到他。再者,你马上去找那什么阎洪,从他嘴中探探口风。”
“是,是,”王申磕头如捣蒜,应着出门去了。
荒弃的宅子里,包祥被五花大绑在一张椅子上,董老玉狠狠地抽了他两巴掌,他这才悠悠舒了口气,睁开眼来。一个老者正坐在他面前,神态肃穆,不怒而威。另一边,就是那个卖女的汉子,正恶狠狠地看着自己。他用力挣扎了几下,可是这麻绳太紧,直勒进皮肉里,不动还好,一动生疼。“你们到底什么人?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绑爷?”
董老玉也不说话,直接一拳照着他的眼眶砸去,直打得他天昏地暗,眼里仿佛有无数的星星闪着金光,泪水和着血水直流。还没等他缓过神来,鼻头又中一拳,这一拳打的他一嘴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鼻骨歪在一旁,血水和着鼻涕,混着上面流下的眼泪,流入口中,痛不堪言。眼见这第三拳又要在太阳膛上开花,忽然老者开口了:“快住手,莫要打死了!”
董老玉这才停下了手,一把狠狠揪住他的辫子,问道:“说,你把李家声弄到哪里去了?”
这厮脑中一片懵懂,口中的血水呛到了喉咙里,憋不住一阵咳嗽,血花四溅,嘴角的涎水淌个不停,闭着一只淤黑的眼睛,“谁?谁是李家声?我不认识你,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打我?”
“放你奶奶的狗臭屁,”董老玉无名火起,拽着他的辫子往后拉,一绺头皮已被从额前掀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玩意,装给谁看?再不老实,老子把你头拧下来。”
包祥不得不紧贴椅背,直感觉头皮火辣辣地疼,口中连呼吸都困难。一旁的阎老不禁皱了皱眉头,低声喝道:“好了,董三,你还想不想问出家声的下落?这要是把他弄死了,咱可就问不出家声下落来了。”
董老玉总觉得不好好修理他,手就痒痒,可如今听了阎老的话,决得也是,这万一打死了,自己白费力不说,还害了兄弟。
阎老见包祥渐渐安静下来,这才问道:“你姓包,是县丞王申的亲随?”
包祥瞎着一只眼,忍痛回道:“爷坐不改姓行不更名,正是王大人随从包祥。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头,还不快放了我?”
“呵呵,包祥。好,好个威风的随从。你可知老夫是谁?”
包祥一歪头,不屑一顾道:“老东西,我管你是谁?在新平地界,你是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窝着。”
这一番话又把董老玉惹恼了,挥着拳头又准备打一顿,被阎老劝下了。阎老笑道:“不错,你们新平县好深得水啊!老夫从踏入这里,就已经感觉到了。”
包祥见这老者不卑不亢,谈笑风生,心中也是一惊,因为如果换成常人,自己的这些话已足以将他激怒,何况自己还被缚着。于是他脑中快速地转动,忽然一个人名进入他的脑海——阎敬铭。阎洪曾对自己说过,阎敬铭身边现在除了他,还有两个帮手,一个是李家声,另一个就是什么远房表兄董三,这眼前的大汉,莫不就是董三?那么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督赈钦差,朝廷的工部侍郎阎敬铭?
包祥心中慌乱,如果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阎罗王”,那自己真的完了。可是,他的心底又涌现出一丝希望,和很多绝望的人一样,他们总是期待着奇迹,至于奇迹在哪里,没人知道。他快速盘算着自己的胜算,李家声还在自己手里,自己的主子王申此刻一定在派人找他,而阎敬铭身边并无其他帮手,还有就是阎洪,只要阎洪把消息传出去,一定会有人来救自己,一定!
阎敬铭轻轻咳嗽了两声,盯着包祥的眼睛,说道:“你是不是在想,会有人来救你?”
“啊!你怎么知道?”包祥大骇,这人真能看穿自己的心思?
阎敬铭笑而不语,只是盯着他的眼睛,包祥不得不移开目光,他觉得此人的眼神中,仿佛能长出手来,透人心内,洞若观火。终于问出:“你,你就是那个钦差阎大人?”
“不错,老夫正是阎敬铭。”阎老并不隐瞒,因为此刻自己身在新平险地,手下无一兵一卒,现在唯一能起些作用的,或许就是这个名号。一个堂堂钦差大臣,莫说一个下人,就是县令亲自来此,一般也是能震慑得住的。
果然,包祥在得到这个答案后,脸色变得苍白,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觉得自己在他面前,就如同一只蝼蚁,什么时候死,只在他一念之中而已。自己能做什么?等待?等什么?王申还是县令?他们就算来了又能怎样?
他忽然又想起了他的儿子,他原本有两个儿子的,可后来因病夭折了一个,留下这唯一的香火。平时他虽说在外面心狠手辣,可回到家中,他也还是孩子的父亲,虎毒不食子,何况这是他包家唯一的香火啊!这么久他从来没有对外人提及此事,甚至连回家都会小心谨慎,防止别人跟踪。因为他在外积怨太多,保不齐哪天就会被仇家寻了仇,所以,只有王申——他的主子,知道他的一切。如果自己说出了主子的秘密,恐怕他包家的香火就断了。衡量再三,他还是决定死扛着,什么都不说,只要王申平安无事,也许,他的儿子应该也能平安无事!
“包祥,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了,我想,你应该也知道我找你何事了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阎敬铭笑道:“难得你还对主人忠心不二,如果李毓的随从也和你一样,恐怕他也不会糊里糊涂地死去了!”
包祥又是一惊,暗道这阎罗王好像已经知道了李毓的死因,他到底还查到了些什么?怎么阎洪从来没和自己说过?
阎敬铭起身,绕着包祥的椅子踱步,边走边说道:“我知道你心中在想什么?你肯定在想,王申会派人来救你吧!那我就奉劝你一句,不用再痴人做梦了,我早已从巡抚大人处调来人马,莫说王申他们找不到你,就算找到了,他们也不敢妄动半分。”
此话一出,不要说包祥,就连董老玉也满脸狐疑,心想这老头什么时候调来了兵马?人在哪呢?连自己也被蒙在了鼓里,要早知道就不费那个劲,直接率兵冲进县衙不就得了。他哪里想到,阎大人这么个大官,平时一本正经的样子,竟然还会骗人。
包祥一听此话,自然对钦差大人也是深信不疑,以他的身份,莫说调些兵马,就是拉个军营驻扎进新平县城,恐怕都不是难事。这样一来,心中刚刚滋滋燃起的最后一丝希望,顿时被浇灭了,只剩青烟一缕,面如死灰。
阎敬铭细细观察着他的表情,这个阅人无数的官场老手,早已经能够察人入微。中国官场有一套奇怪的学问,有人称之为“厚黑学”,这当中包括许多官场人士行事的精妙奥义,厚黑者,脸厚心黑也。而察人,于这一切学问来说,就如同万丈高楼的地基,乃官场必备之技能。正所谓:用人不察,何以知人,知之不深,何以任人,任之不当,何以善用?他自己能够在朝廷的一片浑水中几落几起,游刃有余,除了自己刚直清廉之外,便全靠这“察人”的本事了。
阎老继续说道:“你猜那王申等人,此刻正在做什么?若是老夫所猜不错,他们此刻必定在全城搜索你的下落。可是,就算他们把你找回去,你觉得他们还会再相信你吗?他们会信你什么都没有说?官场之上,有几个值得信任的人?何况你只是个下人而已!”
包祥想起了孙翔和牛连升,正因为县令大人说的那句:死人才是最可靠的。自己亲手杀了这二人。如果此时自己再回去,王申、林尚荣,真的会相信自己?亦或和那二人一样,被杀了灭口。其实不用细想,也知道结果大抵就是后者无疑了。所以现在,他是一个不能露面的人,就算有机会逃走,恐怕最后也只能是个死!
“你不要说了,我不想听!”包祥心里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线,被阎敬铭的几句话推倒了,他不想再听下去,他的心越来越凉。
“呵呵,不想老夫唠叨并不难。这人哪,哪个没有个牵挂,包祥哪,你应该也有家人吧?”
“你想干嘛?我…我没有……我没有家人。”包祥有些惊慌失措。
本来阎老也只是试探一下,可如今,他可以肯定,这个包祥是有家人的,而且,还十分在乎。继续道:“其实,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应该为你的家人着想。王申他们若是找不到你,必然会先将你的家人控制住,而你也必然能想到这点,所以,这才是你最后的支撑罢了。”
包祥此时已经汗流浃背,那些汗浸入到被绳子勒开的肉里,就像被盐水泡着一样疼,又仿佛有千万只虫蚁爬过,奇痒难忍。
“不管如何,包祥,结果只有一个:就算你什么也不说,没人会相信你,你和你的家人都会被灭口;当然,你说了,也会死。但是,如果你肯说出你家人的下落,我或许能派人救他一命,只要你肯与我合作,老夫阎敬铭,可对天地起誓,保你家人活命!”
董老玉在一旁看着包祥阴阳不定的脸庞,浑身汗如雨下,连嘴唇也苍白干裂,两只眼睛空洞无物,若不是一开始便在,还只怕把他当成个病入膏肓之人了。心中不禁对阎老多了一丝敬畏,暗道:这以后自己当了大官,要是也这么厉害就好了!
包祥空洞的眼中,浮现出儿子的身影,这个没娘的孩子,如果自己再不在了,就算没人杀他,在这样的世道,也是万万活不下去的。那狡猾如狐、奸诈如狼的老爷们,又怎么可能会放过他?自己无论如何,都再无回旋生存的可能,可儿子不能死,包家唯一的香火不能断,否则九泉之下,他也死不瞑目。救儿子靠谁?只有阎敬铭,他不像那些人,满嘴谎言,一肚子男盗女娼。至少他是个清官,这样的人怎么会说谎呢?现在或许,只能赌一赌,把这个筹码押在阎的身上,至少不是毫无把握?
终于,包祥放弃了抵抗,“阎大人,你说保我家人一命,是不是真的?”
“当然,老夫一向言出必行。”
“好,我有个儿子,叫包凯,住在鱼脊巷东边第四家,大门上有块门牌,写着新平县三十区正户和字第十八号。你派人去把他接来,我见到了儿子,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
阎敬铭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的包祥不再垂死挣扎,而是选择合作,这是他到新平后最好的消息,看来,所有的一切都要水落石出了。
董老玉独自穿行在夜色里,鱼脊巷,印象里是个不长的小巷,在城的西北角,很是偏僻。这一路和平时不同,不时出现举着火把巡逻的衙役,甚至还有的人沿街逐个敲门,进屋搜查。董老玉心中猜想,这些人大概就是在寻找包祥。心中担心包凯,万一他被人抢先一步掳走,那今夜阎老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所以脚下不觉加快了步伐。
鱼脊巷,因形似鱼脊而名,两头细中间宽,东边“一,二,三,四”,董老玉一家一家数过来,吹亮手中的火折子,凑近一瞧,果然门上有个铁牌,最后刻着……十八号,就是这家了。他掏出梭镖,从门缝插入,一点点拨开门闩,推门而入。小院子里很静,简简单单的三间房,东边房门没关,董老玉进去一看,一个十岁左右的娃娃,正倒在草席上呼呼大睡。董老玉怕夜长梦多,直接拿块麻布,把他嘴塞了,扛在肩上便往回赶。
一路上,搜查的人越来越多,动静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