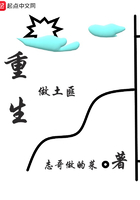只过了个把时辰,天就黑了下来,家声将马拴在村口的一片林子里,便独自摸进村去。夜很静,静的只能听见虫子叫声。村口的几户人家似乎没有人,黑灯瞎火。直到一户大院,才能见到门缝里透出光来。院墙不是很高,家声绕到院后黑暗处,提了口气,翻身上了墙,伏在墙头盯着屋里。过了片刻,似乎并没有人声,这才翻身落地,朝前院去。
院子很整洁,堂屋两侧是耳房,可以看出平时这是一个比较富庶的人家。家声绕道耳房之间的黑影里,向堂屋内看去,只见一妇人坐于堂前,而堂屋内却停着两口棺材。棺材前是一张案桌,上面燃着一炉香,点着两只白蜡烛。那妇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面色在烛光的映衬下特别苍白,一身素衣,穿戴得很整齐。
这时从堂屋的偏房里传出几个人的声音,家声这才注意到,旁边的房里还有人,似乎正在吃喝。
只听得一人道:“大哥,咱们这次能窝在这过几天安身日子了,来,再喝几杯,这家的酒香呢!”
“你们多喝,虽说能躲这几天,可就怕万一谁报官了!”
“管他姥姥的,这村子哪里还有人嘛?留下的都是老人娃娃,有个屁用?走都走不动了还报官?你看这婆娘,死了老汉儿子,不也是只能在这等死?要不然咱们来了,她早一家下黄泉了!”
“那是,大哥你放心,小六说得对,我们在这绝对安全,今天晚上你可要好好轻松一下了。明天咱们再杀头牛,几天不吃肉,浑身不得劲啊!”
房内你一言我一语,家声为了看个真切便走到窗子下,用手指沾了唾沫在窗户纸扣了个洞,这一看心中一沉,三个人围着桌子,那面向自己的不是殷兴又是哪个?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让自己找到这厮。手中不自觉抽出短剑,便想进去逼出哥哥的下落,可转念一想,这三人一起,自己进去不见得能讨好,何况他们一大伙人肯定就在附近,万一惊动了,不仅就不出哥哥,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想着便又稍稍藏身起来,师傅曾经留话:擒贼先擒王。
半个时辰后,三人醉醺醺从房内出来,经过那妇人旁边时,三人大笑地调戏,妇人竟然一动不动,任他们上下其手。殷兴将另外二人推出门外,嘴里嚷嚷道:“你们…出去,莫要…坏了我的…好事!”
那二人嘴里也是支支吾吾,脚下踉踉跄跄地走出了院子,殷兴插好门闩,那两人还在门外拍着门板,说着大哥你自个快活,咱兄弟就听听也舒服嘞。殷兴不管这二人,任他们门口闹去,直接走到那妇人面前,一把抬起她的下巴,凑近道:“怎样,今晚同我睡吧,你不想和你那死鬼男人和儿子一样饿死吧?”
那妇人不说话,只是用力转过头来,殷兴大笑道:“好犟的娘们,够劲,我喜欢。”说着进房内拿出了两个馒头,一手还端着一盘菜,放到她嘴边,“我看你吃不吃。你如果宁肯饿死,我就敬你是个烈女;如果你吃了,那就别犟,好好地把爷伺候舒服了,以后只要有我一口就有你的一口。”
那妇人不知道多久没有吃过东西了,虽然一动不动,可脸也再没有转过去,眼睛只是直直盯着面前的食物,渐渐地喉咙开始吞咽着口水,眼睛圆瞪,殷兴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我说过,想吃就拿,饿的滋味我晓得,何苦难为自己呢?”说着将馒头靠紧她的嘴唇,终于,她再也不犹豫,抓起两个馒头就往嘴里塞,馒头太干了,噎得她尽量把脖颈伸直,嘴巴张大,那殷兴见状,哈哈大笑,又从房内拿出两个馒头塞到她手上,还拿出酒壶给她灌了两口,她此时就像一个饕餮,只要是能吃的她来者不拒,一个亲眼见过身边人饿死的恐惧,就像一口绝望的枯井,这些食物如同慢慢渗出的水,枯井急需、渴望着水的注入。
殷兴猛然将她的衣衫拉开,她并不反抗,因为顾及不了,他一把又扯下她的裤子,将她抱着放平在那案桌上,便解开了自己的腰带。
她只是吞咽着馒头,任眼前这个男人怎样对她,她只是要将饥饿赶走,别的,什么感觉也没有。等她将所有的能吃的都装进肚子,殷兴也停止了动作,门外两人也没了动静。
家声轻声走到门口,看着那瘫软在地的殷兴,又看了一眼那个妇人,捡起地上的衣服扔给她,她好像并不关心他从哪来,只是如同行尸走肉般站在一旁穿着衣裤,家声找来绳索,把醉倒的殷兴五花大绑,嘴也塞了个严严实实。等这一切做完,殷兴还在打着鼾,家声在他脸上拍了拍,并不能醒。
此时那妇人已经穿好了衣衫,她走到家声旁边盯着殷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家声见状反而不知是该安慰还是怎样,忽然她夺过家声手中的短剑,对着殷兴赤裸的下体,一剑挥去,家声想拦为时已晚,这家伙以后再也做不成男人哩。殷兴那厮哪里经得起着削铁如泥的一剑,直将他痛醒,瞪大眼珠,嘴里直呜呜,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子滴下,这酒,已经完全醒了!家声拿起那厮的裤子覆盖在伤口,血水已经流了一滩,家声不能让他现在就死,还要救人呢。也许是流血过多,那家伙竟昏死过去。
直到三更时分,血都已经干了,殷兴才悠悠出了一口气,醒了过来。此时那妇人已不知去处,只有家声一人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家声见他醒来,用剑搭在他脖子上:“你不要喊叫,我让你开口!”那厮赶忙点头。家声一把拔出塞他嘴里的布团。
“我哥在哪?”家声问道。
“我…我不知道,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走!”也许刚才的伤口还疼痛,他每说一句话,就会直吸凉气。
“殷兴,你从冯家沟把我哥掳走,怎会不和你一起,你到底将他怎样了?”家声此刻听说哥哥不在,心道肯定被害了。手中短剑一用力,殷兴脖子上立刻开了个口子,血渗出来。
“小爷饶命,小爷…饶命。我并…没有杀他。那天从你们村子回来,我们想,留着他也没甚用,还要多张嘴吃饭,所以半路我们就把他捆了扔在了个破院子里。我真的没有杀他!小爷不要杀我!”
“扔在哪里?你随我去,否则我要你偿命!”说罢,家声不管他疼痛难忍,直接扛着他出了村子,放在马背上,带他寻到了林家桥下边的村中一户人家,家声将他拎下马,殷兴指着门户,“就是这家,就是这家…”
家声敲门,没人,再敲门,还是没人,家声一脚把门踹开,原来门并没有闩住,家声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找了个遍,却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是在地上找到了一堆麻绳。那厮看到绳子,忙道:“你看,就是这绳子绑的你哥,那两个结是我惯打的结,我没有说谎嘞……”
家声心道,看来这厮并没有说谎,哥哥既然解了绳索,应该也是逃脱了,可是怎么会没有回去?只是如今线索也断了,唯一确定的就是哥哥并没有死在这群人手上。
如今怎么处置这个家伙?杀了?师傅让他不要乱开杀戮。留着?只会害了更多的人。不如送官吧,让官府来办,可能更加稳妥些。想着家声又重新上了马,回到了那妇人家中,寻得笔墨,将殷兴一伙人的恶行和藏身之地写下,欲将她一并救走,可她却执意不走,说是她留下稳住他人,等官兵前来一并拿了,不是更好。
家声便不再勉强,负着殷兴一骑奔出几十里,遇到了稽查的官兵,这才将殷兴及那封留字一并放下,这才掉头回去。
话说官府得到这消息,正值打击流寇匪患之高峰期,县衙连夜报送了州府衙门,第二天守备便派出总兵葛清泰等带兵往捕,余匪虽负隅抗拒,怎奈官军奋力攻击,击毙贼匪一百多,剩下的都被捉拿归案。
这些消息,家声也是后来进县里,看到城墙外挂着殷兴的人头,还有墙上的告示才知晓的。家声看着那快风干的人头,心中说不出的滋味,但不管怎样,总算为冯家沟那些死去的乡民报了仇了!
话说张小婉被董老玉护送到家后,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张家坐着好几个人,为首的小婉认识,为首的那个正是胡记钱庄的徐掌柜,两边站着的是徐掌柜带来的四五个壮汉。张德利瘫坐在一旁,手中的旱烟袋挂在手腕上,地上的烟灰成了堆,而小婉的娘脸上尤带着泪痕,一脸死灰。见小婉到家,那徐掌柜的脸上笑开了花,褶子里开出喇叭花一样,笑盈盈走上前迎道:“哎呦,张大小姐回来了,咱正和你父母提你呢,这正是白天不说人晚上不说鬼啊!”
小婉向爹娘问好,可张德利看都不看她一眼,只是头埋着,不住地叹气,小婉又去看她娘,她娘一把抱住她竟哭出声来。
“娘,怎么了?”又回转过来问徐掌柜:“徐掌柜,不知今天上门何事?”
徐掌柜笑道:“张小姐好记性呢?这前些时是您亲自到我们柜上借的银子,怎地忘了?”
小婉道:“借银我自然记得,可我明明记得是期限半年,如今还差一月,怎地徐掌柜就上门来了?”
徐掌柜又慢慢坐下,用手抚了抚那几绺胡须,慢声道:“我知道,当时签的借据是半年,可我们钱庄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旦借方有什么突发情况,可能还不起借款,那我们钱庄有权提前收回借款本金,以防止烂账的发生。这个规矩一般的生意人都懂,而且全国的钱庄都一样,不信你可以问问你爹,或是到别的钱庄打听打听?”
小婉望向他爹,张德利对着她点了点头。徐掌柜又继续道:“自古欠债还钱,何况咱们还有签字画押的白纸黑字。今天我上门,正是为此事而来。你们一家再商量商量吧!”
小婉蹲在地上,问她爹:“爹,咱把钱还了不就是了,怎地如此?”
张德利痛苦地挥了挥手,对女儿道:“还,我自是懂得。可家里哪里还有银子。前不久粮行赚的都进了货,本想着大赚一笔,到时候别说还债,就是再买几个铺子也是绰绰有余。哪曾想,这些进来的货竟被那土匪抢了去,如今我们家连以后的活路都没了,哪里还有钱还债啊?”说着,张德利用力拍起桌子,呼天抢地来。
听了爹的一番话,小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他们张家竟然连几百两银子竟也凑不齐了?她拉住她娘的手:“娘,这是真的吗?我们家前一段生意那么好,怎么会没存下银子?”
“女儿啊,你不知道现在的粮价多贵,你爹为了多赚钱,每次赚来的钱都投了进去,这土匪一抢,可不是要了咱的命了啊……”
张德利也哭着道:“都怪我,都怪我,人心不足蛇吞象,只想着钱滚钱,哪里想到留条后路啊……”
小婉对爹说道:“咱们还有铺子,房子,当初不是抵押了吗?大不了咱们把房子给了钱庄,我们去冯家沟家庆哥家居住,总不会没有办法的啊?”
张德利拉住女儿哭道:“他们现在不要房子铺子啦,这不值钱哩”!
“怎么会不值钱呢?徐掌柜,当初你可是估过价,说咱家的房子值四百两的,这些钱还钱够了啊?”
徐掌柜如同看戏的一样,在旁边静静听着这一家呼天喊地,他心中很过瘾,听到小婉问话,他哈哈大笑:“我的大小姐哦,你真是个不见世面的女子呦,你可晓得,如今这房子不值钱了,你就是出去送恐怕都不见得有人要啦!”
小婉盯着他,摇头道:“不可能,不可能,你骗我哩,房子自古就是人们的安身之本,最是值钱的,怎么可能没人要?”
徐掌柜看着她也摇头道:“我没有骗你,你可以自己出去问问去,看我有没有骗你吗?”
其实呢徐掌柜说得不假,这自古物以稀为贵,粮食现在是最稀缺的,打个比方,小麦从前是三百文一斗,现在已达到三千六百文一斗,基本翻了十倍,粮价这么贵,就算是颇有产业的富人,想吃口饭,也得卖房卖地。然而灾荒一来,吃饭成了唯一重要的事。除了粮食,其他东西没人稀罕,物价跳崖式下跌,当时有句话叫“典衣十不付一,卖物百不给三”。
有些有钱人才用得起的紫檀椅、红木桌,在这时唯一的价值是烧火用,别的一无是处,还有地方“四五吊钱可以买合院一座,三个馍即可得好地几亩”。这时候,房子早已经没人买了,很多人守着豪宅,却也成了饿死鬼。
小婉喃喃道:“这么说,咱家的房子现在是一文不值了?”
徐掌柜一拍大腿道:“就是这么回事!你们张家粮行也是打开门做买卖的,都知道咱行商的讲个’利’字,如今你们家落了难,我也很同情,可是咱钱庄也是做生意的,不是开善堂的,咱还有这么些口子张着嘴等米下锅嘛,所以啊,你们张家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筹到钱,让我们也好回去交差啊!”
小婉看了看那周围的几个彪形大汉,知道今天这事不可能轻易了了,可她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
她娘只是哭,张德利烟袋里的烟叶子早已经都化了灰,半晌,张德利忽然向徐掌柜跪下,求道:“徐掌柜,求您高抬贵手,我知道现在县里官仓正在放平粜米,你容我想想办法,如果我铺子能够弄来这平粜米,那还你银子就没问题了,求你容我几天……”
徐掌柜眼睛一转,露出半个眼白,笑道:“张老板,你说笑呢吧?这平粜米自古都是官仓米厂出的,哪里有民间的粮行出售的?你这就是欺我外行了吧?”
要说这平粜米是啥?其实就是是官府当时平抑粮价的一种措施:丰年由官府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粮,是为平籴;荒年用平价出售粮食,是为平粜。史书有记载,清代的“平粜”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四十三年,“以京城米贵,命每月发通仓米三万石运至五城平粜”。不过,这个政策最终确定是在雍正年间。雍正在继位之后不久便设置了米厂用以平粜。雍正四年,因“五城设立米厂,俱在城内僻巷,老弱穷民,籴买甚难”,谕令巡城御史“在城内添设米厂几处,以便穷民”。这一年,“京仓好米发五万石,分给五城,每城领米一万石”。后来在灾疫之年,官府就会不定期举行平粜,比如乾隆十六年,就平粜了三十次,最长的时间长达两个半月。到现在正好是光绪三年,北方多省旱灾,百姓流离失所,各省便效仿之前的京城,下令由官仓平粜,只是这平粜米粮从来都是有官府把持的官仓米厂经营,从不会放至私人粮商手中。
张德利现在也已经乱了方寸,只是给徐掌柜磕头,“咚,咚,咚……”额头上都已经渗出血来。小婉扶住他,用帕子按住他爹出血的脑袋,哭道:“爹,不要再磕了,已经流血了,再磕怕是要出人命了……”
徐掌柜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斜着眼看着,嘴里叫道:“哎呦,我的张老板哦,你这我可是担待不起。我不是说了嘛,我也是有苦难言哦!这钱庄也不是我徐某人家的,都是东家的,我不过是个在柜面上帮忙的。如果你们还不上钱,东家可不会这么轻易饶过我,你们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
张德利拉开捂着头沾了血的手帕子,爬到徐掌柜面前,道:“徐掌柜,你说咋办?我听你的,哪怕你要我张德利的命,我也拿给你!”
徐掌柜一抖长衫,道:“我可不敢,我只是要欠债还钱,可不敢闹出人命官司来。实在不行,我只有告上县衙大堂,让知县大人给你们全家判个罪,你们一家子坐个几十年大牢再说喽!你可要知道,县衙里好多大人都在咱钱庄吃着利呢!哼!”
张家的人这回是彻底绝望了,张德利只是悔恨之前赚钱的时候没有一早把银子还了,一贪心成千古恨;小婉娘只是已经哭干了眼泪,这个老实巴交、夫唱妇随的老实妇人,如今也已经没了活下去的希望;只有小婉,她想着既然徐掌柜知道他家的情况,今天还带这么多人上门逼债,必然有所求,而并不是要将他们往大狱里送。
小婉看着徐掌柜,跪到了他面前说道:“徐掌柜,您今天上门肯定不是为了把我张家人都关进大牢,如果还有一线希望,求您可怜,给我们指条路吧!”
徐掌柜一看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在自己面前楚楚可怜,赶忙一把将她扶起,轻声道:“哎呦,我的好闺女,快起来起来,这不是心疼死老夫了,这救命的法子不是没有,只是不知道你肯不肯照我说的做罢了?”
张德利如同黑暗中见到了火光,眼中腾起一股亮光,忙问道:“掌柜的,请讲,只要能够做到的,我张家人绝对刀山火海,肝脑涂地!”
徐掌柜站起身哈哈大笑,对着小婉说出了他心中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