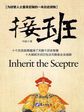从此,她没有笑过,也变苍老了,两眼网满了血丝,痛苦像只无形的大手,揪住了一颗纯真无邪对革命抱着无限向往的心。
陈毅后悔了,他不该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她,那种遗嘱式的安排,岂不把姑娘吓死?
他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但是,各地捕杀AB团的枪声却更加重了姑娘的疑虑。她在那些用刀砍死、用红缨枪戳死,用石头砸死的AB团的血洼里,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现实。
大打AB团的声势有增无已,使肖菊英感到大祸正在敲门。
1930年11月至12月,一个月中,不到四万人的一方面军,就打了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
杀就杀吧,一枪打死一刀砍死也好。可是,不,有的竟然用生锈的铁丝刺穿睾丸牵着去游街。
陈毅接到了去总部开会的通知:
“时候终于到了,”他暗自思忖,“这是一出鸿门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死就死吧!”他真正要托付后事了:
“菊英,我去开会,……”陈毅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能讲得太明,他指指墙上的挂钟:“等到下午六点钟我还不回来,你就快走,也不要带任何东西,那就出不了村了,一定去信丰城,藏起来。如果我没有事,我就派人找你回来,如果无人找你,你就别回来了。”
这是陈毅生活中的一大错误,他既没有想到妻子是那样脆弱又是那样刚强。
肖菊英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叹。只是低首垂目,漠然无语。这种悲极凄绝之气,使陈毅为之悚然。
他回来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在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过得太容易了,而他的妻子却忍受着比两个世纪还久的毒刑。
肖菊英认定她的命运已经定了。她开头总是反驳自己:“一个日以继夜为革命工作的人,怎么能跟反革命连在一起?”
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不会推理,却会比较,正在火线上杀敌的红二十军的领导人不也成了AB团吗?她弄不懂许多革命者为什么都让AB团这个鬼魂附体,把自己拖下黑色深渊?她认为丈夫已被邪魔选中,不会再回来了。
一时间,她心如枯井:逃走有什么意思?活着有什么意思?
一个稚嫩的心灵能经受住两个钟头的煎熬吗?其实,陈毅骑马的身影一在远处树林里消失,她就受不住了。一整天,她的眼睛盯着窗外,不饥不渴也不困,只盼望那白马的身影从树林后面钻出来。
墙上的挂钟残忍地向前走。“当!当!当!”敲响了下午六时的最后一声。
整天的烈火焚烧已经使姑娘不能多忍受一分钟,她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她不能就这样离开陈毅,她要带走他一点什么东西。
她仰起惨白无泪的脸。看见墙上贴着陈毅笔录的一首诗。这是唐代祖咏的《望蓟门》:
沙场烽火连胡月,
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
论功还欲请长缨!
“弘,我们走吧,离开这煎熬人的世界!”
她是那样平静而又坚定地把丈夫的手迹揭下来,塞进自己的怀里。象个醉酒的人,踉踉跄跄跨下门前的台阶,走到院内的一口半枯的井边,此时,晚风呜咽,满天阴霾,村庄犹如荒坟,一个求死若渴的妇女,倒撞下去。
“咕咚”一声,结束了一个人的悲剧,却没法结束时代的悲剧。
陈毅埋葬了妻子,尽量不让这颗殒落的石子击起舆论的浪花,好在死人如蚁的动乱年代,死个年轻妇女不过小事一桩,谁去过问飘落的一片树叶?但他的心海却狂飙怒卷不能自持,陡生出一种毁灭一切的激情。
他先是怨恨自己,不该预告凶信;继而怨恨菊英,不该如此脆弱,竟然寻此短见。
在山崩地裂的感情冲激之后,他终于平静下来,望着室外黑暗的夜空,吐出了两个字:
“怪谁?!”
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回答的难题!伤心一入黄泉后,再得斯人又几年?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激情,使他把眼前的斗争高度抽象起来:
那是来势迅猛的泥沙俱下的浑浊洪流,由高山之源汹涌狂泻而来:初时,还是涓涓细流,可是千百条细流一边奔泻着一边扩大着、接纳着、积聚着,沿着雨淋沟、大冲沟啸聚而来,推波助澜,涌入河床,万源齐汇,越滚越大,越来越猛,裂岸惊涛,势如万马奔腾。
夹岸芦苇一齐倒伏下去,有几杆梗直的、幼稚的或是尚不清醒的芦苇来不及倒伏,就“嘎巴”一声齐腰折断了。
不倒伏即断折
“菊英,你是不是在这大肃反的洪峰下的那杆稚嫩的芦苇?”陈毅悚然而惊似有感悟,“难道我就不是一株既倒伏又待折的芦苇?洪峰是不可抗拒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既是芦苇,又是波澜,你冲激我,我冲激你,推波助澜的不正是那些倒伏的芦苇吗?洪峰似乎是没有的,是一批芦苇去摧折另一批芦苇,可是,没有洪峰,芦苇能互相摧折吗?
不,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种现象也许古人早已概括过了: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宁都会议,不再是肃反会议,这是用数以千计的同志的鲜血换来的。但在会议上仍然翻卷着与肃反相同的洪峰。仍能听到受屈的冤魂的哭泣。他跟周恩来的翠微峰金精洞的交谈能否有效?陈毅想像不出周恩来在这不可抗拒的洪峰面前是如何摆脱困境的。
四、变通之法
会议继续召开。
周恩来为会议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运用了自己的全部才智,但他知道,事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也如此。
思想左倾的人并不是事事都左,而且在某个问题上很右,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是事事都右,有时也很左。这种二分法,连老祖宗都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就是说他也有不智的时候。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另一件事可能办得很糟。
他仍然认为前方委员们是对的,但硬顶必将受到加倍的反击,有时毁灭性的!曲则全,枉则直,陈毅和他在金精洞的谈话的深意就在这里,在肃清AB团时,陈毅的遭遇他是知道的,无疑是经验之谈。
阶级斗争有时很残忍的!周恩来不能不有所变通,如果他和毛泽东不能同时保留,就是保留一个也是好的。但他还是争取两个都能保留,不能不带有讨价还价的色彩,他说:
“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可以贡献很多意见,以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同志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由泽东同志负指挥全责,我负责监督计划的执行。”
这个换了说法的提议,基本上等于没有变动,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对。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提议,周恩来不能只手回天。
“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毛泽东感到争取无望,退意已决,他缓缓站起来说,“我留在前方是不适合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有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毛泽东忽然感到,知不可为而不为,乃是明敏洞达之举,急流勇退,未必就是坏事,他平静下来,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说:
“也许大家还有许多话当着我的面不好说,我现在可以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