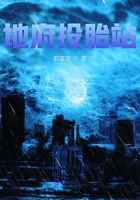雍武皇帝惊愕,大怒道:“肖氏大军建立以来,将士们人人争相立功,从没有发生过战场逃亡事例,国耻啊!军营大帐的兵士全部调到北境去,转告那里的士卒将领,务必将轺军赶尽杀绝,到时人各赐爵一级!如若有逃亡者,依战阵军法从事,立斩不论!”
“父皇明鉴,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有将领若不应命,当场革职!”肖焜又冷冰冰的加上一句。
众臣见安定王杀伐决断如此凌厉,全都躬身一拱齐声道:“保家卫国,共赴共难。”
北境战争爆发,京城里的贫民百姓一无所知,街面上一片安静,因为生意不景气,铺门早关,流言依旧。
暮色再度降临时,一辆带蓬马车进入南城门,越过长长的白石桥,辚辚进入了灯火通明的京城。
凝月下了马车,接过费嫂递过来的霆儿,母女俩望了望眼前的客栈匾额,从容地走了进去。
霆儿身上长了粟粒大的疙瘩,秦州的郎中久治不愈,费嫂无意提起京城有郎中愈术高超。凝月爱子心切,加上半年多了还没有肖衡的消息,于是抱着儿子再次来到了京城。
第二日一早,赶着前去会郎中。郎中说声无妨,开了膏药,嘱咐凝月五日后复诊。
凝月舒了口气,在客栈细心照料霆儿,又趁空打探肖衡的消息。那些流言自然落入她的耳内,她也是淡淡的笑了笑,并不在意。
看来,肖衡还在轺国,她必须耐心地等待肖衡杀回京城。
然而才过一天,官道上扬起了飞尘,一队铠甲骑兵风驰电掣般飞向皇宫,沓沓的马蹄声震响在耳际,隔着老远也能听见。
凝月还在纳闷着,有人冲进客栈大呼小叫起来:“不好了,轺军冲破北境,朝京城杀过来了!”
一时惊叫声四起,人们议论纷纷,满脸惊恐。
“要是肖衡在,十个轺国也不怕。”
“安定王最多算是纸上谈兵,看来翼国有难了!”
“要是肖衡真的是安定王所杀,安定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祸国殃民啊!”
凝月不动声色地上了客栈的楼梯,一进房门,到底掩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费嫂道:“娘,肖衡要回来了!”
而皇宫内已是一派惊慌失措,短短几天,轺军能够冲破大翼重重防线,长驱而入,让人所料不及。连肖焜也是铁青了脸,垂眉陷入沉思。
众臣心头一片凝云,谁也不敢妄自猜度。纷乱之中,肖焜竭力装出泰然神色,微笑道:“有我煌煌肖氏大军,上天庇护父皇,必无大碍。”
雍武皇帝急问:“翼国危在旦夕,焜儿有何良策?”
肖焜慷慨激昂的声音:“请父皇将王盔授与儿臣,儿臣亲自北上督战。储君能身先士卒,将生死置之度外,必定激起将士雄心壮志,消灭来敌!”
“焜儿说得在理,那便如此这般了。”雍武皇帝大为高兴,赞赏道,“焜儿有这般品性,朕甚感欣慰。非常时期,朕下旨,明日殿授兵符玉玺,传位于焜儿!”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个节骨眼上,没有人提出异议,众臣匍匐跪地,颂词哄嗡涌出。
肖焜从殿内出来,朝着钟鼎广场走。广场上莫名的变得很空旷,寒鸦声似在遥远的天际传来,丝丝渗着寒意。肖焜无端的害怕起来,仿佛这天地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他必须独自承受。
轺国背盟进逼,宋鹏欲报国恨,他面临两边压力,却无人帮他。
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
如果肖衡还在……
有尖细的声音针一般刺入他的骨血,他慌乱地捂住了双耳。那声音渐渐加大,眼前皆是叠至沓来的人影,肖衡、冷凝月、殷雪玫……如海中潮汐无边无际地扑了过来,几乎淹没了他的神经。
他轻颤着,疯狂地吼了一声。再睁开眼时,宫内仍是杨花如雪,点点碎碎在空中飞舞。远处,张公公正指使着内侍宫人,他们来往不停地忙碌着。
肖焜恍悟,明日便是自己登基大典,中兴霸业正如这繁花火热的景象,一片勃勃生机。
他眼波一闪,神色又恢复了宁静,匆匆离开皇宫。
第二日辰时,洪亮沉重的大吕钟声撞响了,声音穿透天际,沉沉昭告天下,一位新君王即将诞生。
司礼大臣站在六尺高的王阶上,随着一声高亢宣呼,雍武皇帝携皇后在宝扇宫女的簇拥下,缓缓步入正座。
王令一出,一排长长的传声直传宫门。顿时,殿外大钟大鼓如春雷遥遥滚来,跟着是京城四门城楼的钟鼓声遥相呼应,似乎整个京城都在欢呼呐喊。
肖焜面带微笑,玄衣纁裳十二纹饰的衮服,三光之耀,照临天下。他踏步朝着主殿而去,两边一片肃然,遍地匍匐跪满了朝贺的文职大臣。感奋之余,仿佛有连绵的声浪从天外飞来,又悠悠散开。
站在王阶上,虽然缺少全副甲胄的武将司马,红毡铺地的甬道两旁站立一排御林军,个个执矛束甲,堪称威武雄壮。肖焜依然满意,慎重接过雍武皇帝手中的青铜王盔,衮服翩动,引起殿内朝臣一片惊叹。
翼国朝野素无虚礼,朝中百余名大臣从殿外鱼贯而入,同时,两百多名捧着铜盘酒盏的宫人,在张公公的带领下,分两排川流不息地给诸臣轮换上酒。
肖焜双手接过张公公呈上的酒盏,向诸臣一挥袖,慷慨陈词:“今灭轺军,人各三爵!”说完一饮而尽,如此三爵。
“臣等谢太上皇、谢太后,谢吾皇!”
新皇亲赐陈年王酒,谁个不是心旌摇动?三爵下肚,浑身似火烧,骨架子却是软绵绵的,紧接着摇摇晃晃,一个接一个的栽倒在地。
正座的雍武看得真切,断然惊呼:“酒里有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