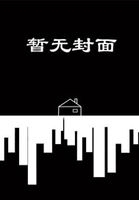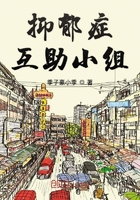东洋列岛,新年伊始,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每个月忙忙碌碌都有花期。一月梅花,二月桃花,三月樱花。这花是一种比一种开得娇软,桃花已失去了梅花的挺拔,樱花更没有桃花的翘首,简直弱不禁风,一阵风过,就飘下一大片。然而赏花的事却是越闹越红火。樱花从南到北,从冲绳岛到北海道,步步进军,日本人用个很形象的词——“樱前线”。那不夹带绿叶的樱红,野莽莽的,让人们恍惚身处的不是人间,而是某个不可把握的地方。那些樱树下的飘荡着的不阴不阳的日本小调,摇曳着的怪里怪气的舞姿,那些天当房、地当桌的人们,那些头发梳得精亮的男人和涂着厚厚脂粉的女人,那些汹涌的赏樱人潮,都让我们在感觉不可思议的同时,又有着隐隐的惶惑。果然,一场大雨就使得这一切销声匿迹了,宛若造物主将世界翻了个面。
提起日本的花,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樱花。但日本的国花并不是樱花,而是菊花,然而樱花却是象征大和魂的。日本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物哀”,就是对物之易逝的伤感,一如对只开十多天的樱花。在中国,也有“转蓬之概”、“忧生之嗟”,比如晋人。但晋人由“哀”而转狂狷,日本人则是由“哀”而沉湎。“哀”不是达到“不哀”的手段,“哀”本身就是目的。这似乎更符合“哀”的本质了,当我们哀伤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别人把我们拉出来,诉说,也只需要你倾听,诉说本身就是目的。那种开导、劝导的企图是令人讨厌的。实际上,沉湎于“哀”,有一种“哀”的美,凄绝的美。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了不少樱花,最著名的一幅《花明り》,题作“明”,其实并不明,不是明艳,而是凄艳。
日语中有个美丽的词,形容樱花飘落——“樱吹雪”。“美少女战士”北川景子的一首歌,就叫《樱吹雪》。据日本《广辞苑》解释,“樱吹雪”就是樱花的花瓣像雪花一样纷乱飞舞。那年在东京上野公园,就看到了这种情景,梦幻一般,让你分不清是雪纷纷从天上降落,还是花瓣纷纷飞上天离去;分不清是来,还是去;分不清生,还是死。日本人把死看成是新旅程的开始,他们把死叫作“去天国”,我们中国虽然也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是真的恐惧死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走这条不归路的。但是日本人似乎不。2004年10月12日,一天之内,日本就有两起集体自杀案件,富有意味的是,其中一个就发生在琦玉县以观赏樱花闻名的美之内公园。
四男三女共七个年轻人,租了一辆车,车内放了四个炭炉,烧炭自尽。他们还把车窗用胶带密封,还在车外盖一大片蓝色帆布,显示死意坚定。在日本,自杀不是个别现象,东京以西的静冈县的热海,就是“情死圣地”,更不用说大量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以死的方式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作品。三岛由纪夫切腹,川端康成打开了瓦斯。川端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人生最绚烂时自杀的,有人用“人生最璀璨时,不忍见樱花凋落、杜鹃悲鸣”来解释死因。三岛事件,看似因为“忧国”,但也难说没有对自身生命的恐惧,不能忍受健美的身体终有老朽的一天,他要趁自己还没有衰老,把精彩定格下来,让其产生“刹那的永恒”。某种意义上说,与其日本人追求的是活得精彩,不如说追求死得漂亮。
从织田信长到三岛由纪夫,到川端康成,太多的日本人像樱花一样在瞬间灿烂之后,慷慨赴死,以达永恒。灿烂,死亡;瞬间,永恒;乃至其中包含着的耻辱与光荣,这几对意义完全相反的词,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糅在一起,但在日本人思维中统一了,在樱花的品格中统一了。我甚至想,之所以不了解日本,是因为不了解樱花。“二战”期间,当盟军舰队遭遇日军“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撞击,看着成群战机樱花般凋落,直坠在军舰甲板上,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是,发生了什么了?在日本这民族身上发生了什么?在日本人内心里发生了什么?这些彬彬有礼的日本人,这些爱花爱美的日本人,他们怎么了?我们不明白日本文化有着两面性:文雅而又暴躁,赏花落泪而又杀人不眨眼。
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的小说《一年后》,讲了一个奇特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惠理子失恋后,偶遇男子田村。但田村已有女友,他们就在田村女友去美国的一年期间,定下了爱情契约。她对田村说:仅仅是这一年,能和我恋爱吗?
这毋宁是个残酷的故事。这小说后来被搬上了银幕,片名改成了《东京万寿菊》。万寿菊,是一种有很特别香味的菊花,但它只有一年的生命期。在这一年里,开花,结果,然后凋谢,就像那场爱情。导演市川准阐述说:其实并不是每一场爱情都能天长地久的。确实,像万寿菊那样短暂地开放,然后迅速枯萎的爱情,在现代的社会随处可见。
枯萎了没问题,如果尚未枯萎,那怎么办?甚至爱还可能会越来越浓烈。人毕竟不是物,物租了一年,该归还就归还,人不行,人是有感情的。常听一些人说不敢养狗,害怕养出感情来了,舍弃不掉。人是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要控制自己的感情,无异于揪着自己的头发要飞起来。那么,怎么能控制这爱只能到一年为止?
我常想,人最可怕的是想到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其实末日突然降临,并不可怕,在你还没感受到苦难的时候,苦难已经结束了。所以那些突然被夺去生命的人,还应该是幸运的,被车撞死,被突然飞来的东西砸死。相比之下,跳楼就比较残酷了,从落下到着地,总有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怎么办?类似于“凌迟”,刽子手杀“二·七烈士”林祥谦,一刀一刀切他的肉;曹禺《原野》里的仇虎复仇,是把仇人的孙子杀了,让仇人活着,活受煎熬。所以麻醉死亡是人道的,让意识消失;所以拿枪自杀的人就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一扣扳机。我青春期时,老焦虑自己将来怎样死,我总是必死的,可生命就像吹大了的气球,要让它消失,只能把它压爆。为什么会有气球这比喻?因为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的自己就是一个气球,它被吹得满当当的,眼看要爆炸,我不知该怎么办。当然我可以解开扎口的线绳,但是我就是解不开,人是不可能解得开自己的结的,只能任它膨胀。它几乎透明了,马上要爆炸了,但是它还没有爆炸,它只是用爆炸吊着我,漫长地等待爆炸,不可自拔地走向爆炸。可怕的不是它要爆炸,而是它走向爆炸的过程。
这不是《一年后》里的事情,是另一个故事。他和她,三年前认识并且相爱。他们的期限是三年。三年之后,她必须离开他去她丈夫所在的城市,这是不可改变的。在这三年里,他似乎忘记了这个事实,他觉得她就是他的,只有她去她丈夫那里探亲时,他才明白她不是他的,不能忍受。他不能忍受她和她丈夫在一起,不能忍受她丈夫奸污她,但是她丈夫有权利对她这样,他是她的丈夫,那也不叫奸污,叫“同房”,甚至叫“做爱”。每次她去她丈夫那里,残酷的现实都会顿然摆在他面前,他都会痛苦不堪,像间歇性精神病发作,直到她回来,一切暂且平息。假象掩盖了真相,她还会不会再走,姑且不管了,反正过一天算一天。但是现在,她要彻底离去了,彻底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了!已经定了离开的时间,余下的每一天都得数着过了。过一天,就走向死亡一天,他清晰地看着死亡在一步步走近,他简直崩溃——倒不如,把它给掐了!
据说古巴革命后,被判处死刑者可以有个最后的愿望,许多人选择了向行刑队发出“开枪”的命令。既然不能把握生,那就把握死。迎向死亡,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当然最好是最初就死,不让爱情发生。现代人有句话:不要爱,只要取暖。女主人公最后跟田村告别,她说:这一年过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