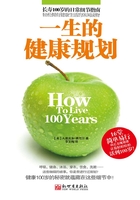临了四月,屋里的暖帐撤去,我卧在哥哥的软塌上,听着外头翻书声踏踏。
“你的字从小就被人夸迥劲锋锐,如今想来那些让都有先见之兆。”
我走过去细瞧,怎得发现有些翩柔起来。
“眼熟?”他抬笔,在宣纸上默下一字:鸳
“你不在的时候,我就看着你幼时习过的书,做过的女工,那些字画都放在我的竹筒里,学着烟儿的字,心里也能宽慰点。”
他指的不在,应是我去了北境。
“鸳字,是我的封,我六岁那日追着宫里娘娘的飞鸟玩,父皇身边的内官大人见了就说了句公主日后必定是一幅凤相,巧着父皇那几日正要给我加字,顶着百官的指责硬要给我上宁鸳二字,他说要让我做桾朝第一栾鸳凤,飞的无忧无虑,说这世上有只大鸟,飞得最高,身披紫云彩翼,浴火直上,跟这宫里的杂玩意是不能比的,如今想来,也没什么不同,我从未见过那大鸟,也只是宫里的一只小鸟,比起宁鸳的名号,我喜欢你们唤我烟儿。”
“烟,是你的乳名,我只会记得它,只会记得你是烟儿。”他在纸上又落下一笔,于那上头的鸳字更为鸿鹄。
他摇摇头坐了下来,“为人夸赞又如何,若有亲近的一人肯认可我...”他眼神冷空几分,蹙眉笑了起来,“可惜他好似从未表定过我。”
我深知他所说的那个人是谁,只随着嗔笑两声故作未听到,他从浮着桑叶的红参汤面上回过神来打量我的衣裳。
“你近日穿的好生素净了,女儿家该娇艳些的。”
“那些衣裳好看,我贪玩不想弄脏了,再言,近日尚衣司的也没给我送新鲜衣色来了。”
“是了,我后宫暂未纳嫔妃,姑姑也住在宫外的府邸,三司用度开销皆往小了去,乐坊舞司也许久未进新人,那几个老人也该坐尽风头了,如今丧期一过内宫上下便无需过于节俭,往年宫里宫里头用的绣锦绸缎都是从苏京进来的,”他思索,“是哪个都督僚官进奉的来着..”
我听得苏京二字头穴上打了个冷哆嗦,忙瞅向他,“往年你总直接问得马侍中。”
“是这么回事,你倒记得比我清楚,他内人的弟弟也在朝中做官,苏京、南关两地的衣缎,今年催催,挑些好的先给两位太妃送去,你也留下自个喜欢的,苏京三月来渔水得利,税库也充裕不少,想来今年的缎子必也美得新奇。”
“哥哥可是记错了?侍中的内戚名富殷,不过是个小粮官,怎得有本事负责京缎的送奉?”
他微顿,手中的茶碗持在那儿,道:“粮官?你怎知他?”
我浅笑,“马思源常带着他进宫不是么?烟儿都眼熟了,我婚嫁那日的百官送礼单上也有他,排头还不小,又是送的最早的,那颗明珠又大又亮,,晶莹剔透的压过好几个大臣的礼。”
他蹙眉,颜色皱肃一刻。
“确实风头不小...”回过头来,“你方才说什么?夜明珠?”
“是,色泽纯得几十年难遇,这东西连着西昌的湖潭,从山里头挖了数天,不然便是泥沙风化,现于地面上来被人们索了去,父皇说这是祥瑞之兆,便给了他。”言谈间,不时向案台上的折子瞄去,“对了,我方才瞧你阅折时神貌肃态,可是生了忧心事?
他一笑,笑的那般容璨,揉着我的指心。
“四祥同你说的吧,我不过是顾不上进午食,这些家伙,只要看见你,我任何烦心事都抛之脑后了。”
他叹了口气道:“近日贩盐盛行,各都府行了我令,将地方税断了两个月季,也帮扶了那些在京桾的商户,竟还压不住这些断腿子,越发猖獗,不良歪风日上,百姓心中不得信服,物价高得太疾,许多人连饭都吃不上。”
我凑向他耳边,将今日事付诸于哥哥,“此事在江边流传较泛,不少人都曾亲眼瞧见富殷的亲信同有贩盐之嫌的矿商来往之密。”
他有些惊奇,眼中留转着利光,盯着马思源的那厚厚一刀折子。
....
我走出内殿,在回云烟阁的路上又碰见秦淮,他定是受了令前去。
晚间进了食便急急伏在内屋,将和亲时公宴上的礼单寻了个遍,也未在箱子里翻到那颗珠子。
“殿下找这个做什么?”
“它在哪儿?定得帮我找出来。”
既是通上下找也无果,我只好上塌歇息去,听得外头阿娜达同扫地的小宫女说笑。
“淑太妃今在戏坊听得那曲儿我也在场,瞧见有两个着西域衣裳的歌伎登台,怀里抱着三面玲珑琵琶。”
“那玩意儿我在关外也见过,倒是新鲜的,近来宫外也从西南族来了许多人,她们的衣裳虽薄,倒也包的可严实了,都是上好的蚕丝织出来的螺圈纹。”
....
我一早醒来方进完食,阿娜达便领着一黑影走近殿外。
“殿下,青衣廷侍卫秦淮求见。”
我正襟危坐,遣了阿娜达几人,见他一身干透的雨蓬还覆在肩上,风风火火的站在了跟前便晓得昨夜发生了什么。
我猜的果然没错,富殷一个粮官,竟可要了苏京都护的贡品运进桾城,可见他便是负责运送那些东西进城的,还能抢了都府的功劳,马思源若是知晓此事,便能明白富殷为何只是个小粮官,若是上了四品那些事反倒招来眼色藏不住.
皇兄彻夜派秦淮查了富殷和马思源的党派,又命随从府潜伏,发现富殷确有在府内同几个商户,都府官员宴笑。
我还特意问了阿婴今皇兄上早朝可有大发雷霆,她摇头道与平常一般,看来哥哥想等证据确凿了再算账,他的私心是想借此事打压太尉一把,可我并未顾及那些,我坐在马车上,被秦淮送到宫外,二人再分别从两头取了马,郊外碰面。
车上我想着昨日皇兄交代的事。
“我知道那几个亲信运盐的私地,许还能从中找出他们路线的行踪轨迹。”
我向他请缨亲自帮衬调查,毕竟我手中有些消息。
“烟儿,我不想让你做这些事。”
“哥哥是担心我会孤身有险?这怎么会呢,你派几人同我一起去瞧瞧便好了。”
他几番思虑,想着我的确是知晓此事一些消息的人。
“那好吧,你必定万分小心,切记不要暴露身份。”
...
“殿下,到了附近。”秦淮接我下来
我同他在路上聊了起来,哥哥让他和我一起,也是个可信的。
“上次看见你,还是在斗场,一副伤横累累的模样,转眼就成了我哥哥的心腹,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宫为臣?”
在我看来,他这样浪迹天涯的人应是和萧逸云他们一样不会对他人俯首称臣的。
“有没有想过?老实说没有,但也未尝不可,活着没有什么事不可妥协的。”
活着没有什么事不可妥协的,我脑子一直想着这句,妥协了谁,妥协了什么,在这世上究竟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了。
“殿下,小心些。”
我们行到临郊外的一片屋外,附近总有一些风吹草动声惹人注目,我掏出追衣画的图纸。
“就是这了。”
我下马看着这一圈,正面的这堆林草屋四周杂草丛生,里头传来嘤嘤作响的动静,越发靠近,便有一股泠冽之气,若有埋伏,我二人从方才便已经被盯上了。
“殿下走慢些。”
秦淮走上我跟前,手搭在腰间的剑上,那上头还有昨雨夜干透的血渍,我身下一阵冷风,那会是谁的血死于刀下了呢。
推开门,沉重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掩面走进去,到处是虫网和堆满的草堆。
走到那几十袋沙袋前,我们互视一眼,他一刀插进去,泻出了滚滚泥沙。
“都是干沙。”他揉搓着。
已被掉了包,我们还是来晚了,他在屋子里搜罗着,然我瞧着地面上的足迹约莫半天前还有人在。
簌簌-
院子里吹进一阵落叶,令人无法察觉的声音里参杂着微微波动。
“谁!”
待我转身时秦淮已跳上了屋顶,轰隆隆的脚步从房梁上传来,我捂着耳朵直觉头晕眼花,四周都是饶人的铃铛声。
一青衣影掠过水井旁,我见那两人厮缠在一起,难道见秦淮如此吃力,怕是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
“秦淮!”
我扑过去,一掌欲打在那人胸膛上,可惜还是擦过一点,眼前一阵翻滚,是那人用脚靴将我有意踹了出去,耳边尽是打斗声,我却觉得那踹是带着轻柔的,麻烦的是在那一刻我也与那张脸相视。
“江映才!?”
他穿着便衣,背过手立在了井口上,秦淮与他暂未有谁上风。
他挑眉看了我一眼,摘下了面布。
“好久不见,你这三两下功夫还真是一点没变,阿逸说的不错。”
“你怎么会在这!”
我欲起身间,秦淮冲过我身侧。
“殿下还是让开!”
他趁说话袭了对方一下,即是这三两下,怕也摸清了彼此。
“秦侍卫!你们停下,他是我朋友。”
秦淮停了一刻,江映才笑了笑,“能被你称作朋友,看来江某的酒也没白招待出去。”
“殿下,此人出现在这,心机叵测,于我们而言许有危险。”
“江某无意,收手的话还请你的刀先放下。”
我推开秦淮的利刃,“好了好了,看在我的面子上,相信我。”
他收回刀,看向依旧浅笑的江映才。
我叹了口气,“喂,你还没说呢,怎么在这。”
“天下之大,江某何处不可走动。”他径直走下来,略过秦淮身侧,瞧都未瞧一眼。
“站住。”对方又持起剑拦住他往屋子里去。
看来这回言可不能令秦淮信服,他甚至早就清楚他的来历。
“江青江映才,虽非朝廷捕犯却也同捕犯萧逸云一窝,与城中商甲亲密交好,这些年待在桾城本就心思叵测。”秦淮看向我,“公主,还是不要轻信他为好,在今日出现此地,断不是偶然。”
“呵,”江映才摇头,“你也是个江湖过客,做了宫官的果然是不一样,口中全是官僚之气啊。”
我见两人神色难谙,恐下不来台,嘴上还是偏着秦淮些。
“今日情形不一般,你讲不出个所以然,最好在我们两眼下走动,待会再问你。”对着江映才道完便走进了屋里。
…
此地暗沉,眼瞧着我们三人快翻了个遍,也没找出个有用的来,秦淮又一边注意着江映才的动作。
“这是什么?”
我摸过桌角一片湿漉,指上黏稠的很。
秦淮走过来,“蜡烛是昨夜燃的,香油已结凝,定是烧了些什么。”
我们向地上的纸屑摩挲去,正好透过光影瞧见江映才腰间袋囊里的银光。
“你方才在这待了半天,可发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