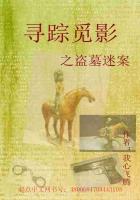我感觉门好像极快速的就从里面打开,他看见是我,脸上似乎并没有不愠,等我再抬眼与他对视,见他仍如往常般绷着脸,让我以为开门一瞬那如同冰山雪莲难得一见的一点笑容是我的一时错觉。
“我来给三爷送药膏,是治疗伤口的金疮药。”
他瞥了一眼我手中拿着的小瓷罐,迟疑说道:“送药?我这里什么金疮药没有。”
他的语气极淡,却像冰棱扎心,就知道此行是自讨无趣,转身要走,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夺过我手中的小瓷罐,“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是金疮药还是歪门左道的毒药!”他打开半扇门,自己回身朝屋内走去,我追着他真想照着他结实的后背打上一拳。他猛然驻足回身,我收拳整理发丝,“我说你是属狗的你还不乐意听,你是有多大的气性全拿我的后背出气。”他语气很轻,让我分辨不出是在说笑还是真的。
“你可不是说我属狗,你是说我……”我话到嘴边才发觉好像又进了他的圈套。
“我说你是什么?”他追问道,眼中有些许得意。
我原地白了一眼,“没什么。”
他站在灯下斜眼睨着我,“是真的好心给我送药?”
这个人警惕性真高,难不成以为我会有让他伤势加重的企图,往药膏里加别的什么东西,真是让人看不透。他果然捡了一支银针扎进药膏里去试,故作一脸严肃一丝不苟的认真神情,气得我真的要在原地翻白眼了。我定定的站着瞧他,到底要看看他能不能试出毒来。
“你大概……是觉得愧疚吧!”他低沉的脸突然扬起看向我,眼中的神情复杂难懂。
“随你怎么想。”我垂下头好像自己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咬着唇自己都在后悔自己这突如其来的善心,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觉得愧疚的!
他放下银针用干净的帕子擦了,背身朝向我,竟解下自己的衣襟露出宽厚的肩膀,我吓得魂都飞了,赶紧捂住自己的眼睛,开始后悔今晚是不是该来这里,后悔深更半夜的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从前读野史的时候就看见过笔者记载,皇室子弟或富家公子怪癖颇多,叫人悚然,这位爷平时那么冷峻骄傲,喜怒无常,谁知道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癖好?
“你还愣着干什么?”他的声音阴冷中透着急迫。
“嗯?”我感觉自己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他侧过脸,影子在烛火下跳动,“还看不清你的齿痕吗?我可没长那么长的手臂能全部够着它们!”
我走近,果然见那些伤口在灯下红得醒目,有的暗红结痂,有些已微微发肿,真没想到自己居然这样厉害。微微兴奋之余,看着他优美健壮的后背,肌肉线条很美,肤色正中,又对那几条碍眼的疤痕有些生气,像百年的青釉陶瓷裂了纹,快要完成的山水画卷被不小心撒了墨,而这些疤痕的始作俑者竟然是我。我指肚沾了药膏轻轻点在他的伤口处,可能是指尖太凉了,他身子微微一颤,我对着手指哈了会气,指肚点着他的伤口,再把药膏均匀的涂在他的这些伤口处,轻轻吹干。他桌案后的翠竹屏风上投着我俩交叠的烛影,烛火跳动,人影幢幢,“好了。”我竟然有些思绪飘飞。
他一直很安静,待我走到他身前他才抬眼看我,那眼神里仿佛透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热度,我轻轻帮他整理衣服,怕那些药膏被贴身衣物蹭掉影响药效,我多少次给四爷更衣,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站在他的身前手竟然有些发抖,他和四爷不一样,比四爷身子结实身量长,更像男人而不是男孩的身体。两人离得近了,第一次感知陌生的气息从另一个人身上有温度的传来,好像是第一次认识,我有些冰凉的手触碰到他温暖的身体,他身子一凛推开我的手,仿佛有些窘迫又有些不耐烦的说道:“不会给别人穿衣就别穿。”
我被他推开,一双手突然不知道要放到哪里了,在裙子上搓着指尖残留的药膏,“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他阴郁的声音冷不防的从身后响起,清晰中又带着迟疑,“那天……那个姓万的护卫为什么要截你,他说得话有没有一句是真的?”
我抬眼,见他衣冠齐整,神色如常,想起那日他和陆影突然出现,也不知听见多少我与壮汉的对话,“哪句话?”我问。
他垂下眼睑又后悔有此一问似的,“没什么。”
不管他听到了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那壮汉是荣王府的护院,害死了我父亲,逼我跳下大河,险些丧命。”
他在灯下怔了怔,“还真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看来那日陆影下手还是太轻了!”
“那三爷呢,您望着那片玉兰的时候一定是有什么故事吧。”
他目光闪过一丝柔和,但很快被他一贯的冰冷覆盖,“没什么,你可以走了。”他冷冷的开口,已垂下目光转身坐在灯下那堆成山的文书前,随意拣起一本翻看,不知为何,我被他最后一个眼神撩拨得心绪有些不宁,他心门紧锁不善表露,可他真的就如他外表看起来那般高傲自尊冰冷坚硬吗,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