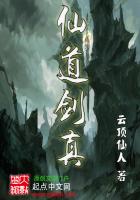话说一见离村后遇到周易,从他处收获颇多消息。
“你要去的话也简单,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去乌兰的应该很多,不过得转车,我估计,怎么也要十天。你既然要出远门,就该先好好准备一下。这样,你跟我回去,今晚在我家住下,明天我送你去我们驿站,给你介绍个走远路的,怎么样?”
一见正考虑要怎么去乌兰,毕竟那么远,自己又是头一回只身在外,处处蹑手蹑脚,听到周易这么说,像见到了救星,毫不推辞的谢道:“那真是太好啦!说实话,我已经累的不行了,一天都在赶路,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呢。”
“我这有干粮。”
周易一边说,一边从马背上的包袱里掏出一张素饼和水囊递给一见,笑嘻嘻的说到:“你说咱俩是不是有缘?你出门第一天就遇上我,我叫周易,你叫周一见,真是巧。”
一见接过干粮就开始啃,然后咕咚咕咚的灌几口水,边吃边附和周易“嗯嗯~是哦~”三下五除二吃完手中饼,水也喝的没剩几口,将水囊还给了周易。
边说边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镇子边缘,眼看日头已挂西山,约莫有四五点了,一见问到:“你家在哪啊?”
“喏,那就是。”
顺着周易所指方向,不远处便是一幢小屋,屋前有一棵大树。
落脚处就在眼前,想到终于可以休息了,一见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十多分钟后二人一马终于来到屋下。
还没等周易招呼,一见已经一屁股瘫坐在门前台阶上,累得后仰在地。虽然是入秋了,但是仍旧有些热,今天又是个大太阳,末班车的蝉们在门前的大榆树上做最后的欢愉。
就在一见躺倒小憩时,周易已经将马拴好,此刻正在给它上草料。
听见动静,屋里传来一询问声:“是不是易儿啊?”
问话的想必就是周一的母亲了。听到屋里人声,一见赶紧爬起来,候着。
周易在外回到:“妈!是我!”
从里屋走出来一位看上去有四十岁的妇人,腿脚不便,拄着个棍。一见见到,又看周易在忙过不来,就上前搀扶,口中恭敬的喊道“伯母好!”
这一声伯母却是让周母吓出了一个哆嗦,身体就要往后退。也不知道是胆小还是怎样,像是被一见这个陌生人给吓着了。
这让一见很是尴尬,连忙解释到“伯母,我是周易的朋友~”
此时周易已经上草料,来到了屋前,喊了声“妈,您慢点~”,然后将妇人牵进堂屋坐下。
“这是我朋友,今晚来我们家住宿。”
“哦~哦~孩子,我眼睛、腿脚都不方便,刚才不好意思啊。”周母看向一见所在的方向,好像是对着空气说一般,看那妇人,眼中似蒙了一层白雾。
“没事的阿姨,刚才是我鲁莽了。”
“来来,快进屋。”周母笑笑,然后就让周易招呼朋友。
“知道了,妈。您先坐着,我去准备晚饭。”
“伯母,我去给周易帮忙~”,说着就跑了,都没等周母反应。他可不想留下来,觉得有些尴尬,也不知道该跟老人家聊些什么。
两人在厨房忙活起来。
说是厨房,不过是在屋子后面搭建的一个遮着炉灶的棚,烟囱穿过棚顶,升起一阵浓烟,乳白色,跟浓积云一样。不一会,变成了袅袅青烟。
在母亲卧床这几年,一见和伊伊也经常帮父亲料理家务,做饭也还过得去。看见一见手脚利索,这倒让周易没想到。
“你和伯母,一定过得很苦吧?”一见边帮忙边问到。
“还行吧。很小的时候,那会父亲刚走,母亲也因为爆炸闪瞎了眼,后来腿也摔了,就那会过得比较苦。后来习惯了,慢慢就好了。”
眼前这个消瘦的身影,越是将这些苦难说的云淡风轻,一见越是感受到其中的心酸,以及现在,周易身上的那种坚韧和强大。有感作为一个同龄人,当别人在接受真正的磨砺时,自己却是在无忧无虑的耗费光阴,现在虽称得上有些苦难,但却因此整天沉溺在悲恸中,抱怨命运的残忍和不公。如果仍旧待在吉科村,也许到死,自己都不会懂得什么才叫苦,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不一会功夫,晚饭就做好了。红薯粥,咸菜,还有素饼。榆树下,三人围坐在桌前吃饭。
此时才六点多,比周易母子俩平时吃饭的时间早了个把小时。往常回到家,周易还要挑着水桶去浇菜地,这样隔一夜,早上蔬菜都水灵灵的,拿去镇上好卖。卖完菜后就去驿站接货。因为不知道要去远处还是只在镇里,周易每天早晨都会做四个素饼,两个留给母亲,两个带在身上,要是当天回来,就将那一张留着晚饭上吃。
这是从周易母亲那知道的,说起儿子,妇人似有说不完的话。
不知怎的,一见吃饭时有些为难。
吃完饭,周易服侍母亲洗漱睡下。两人将凉席抬到树下。看着这满天繁星,和方才周易母子,一见想起了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和妹妹嬉闹、母亲教诲自己…感慨不知何时才能再感受到家人的温暖。
虽是清苦,但周易母子相依为命,亲情更浓。饭时,一口菜,却也让来让去,天半黑,微微月光勾勒着沧桑面容,却见她的笑容依旧那么慈祥。
“长途马车一般走的比较早,明儿一早,我就送你过去,至少在这段路上,你可以放心。我也会拜托明天的师傅到了地方之后再帮你寻一个去乌兰的,他要是有认识的人,你这一路上就更保险了。”
一见还没做过马车,自然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虽然不好意思,但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知道的,这会问到:“在哪中转啊?还有…路费大概要多少钱?”
“应该是恩巴市,在乌落境内,挨着龙族的边界线。花费嘛,我记得好像是七个银币。要是几个人一起,一人四个银币。”
乌托索国所使用的是世界通用货币,由金锭、银锭、金币、银币、铜币构成,依次是十倍关系,一个铜币约是两块钱,在吉科镇可以买四个包子,在乌兰,只能买两个。
听完,一见心里有了底,自己所带的盘缠,是足够到乌兰了。
“你一天能赚多少钱?”想起周易也是马夫,一见有些好奇的问到。
“远近还有货物的种类,每天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在五铜币到一银币之间。不过我是有马无车,扣掉租赁驿站的车钱,能落三五个铜币。”
这么一算,一见觉得去恩巴市的费用也不是很贵,毕竟周易说去恩巴市要五天之久,两百多公里的路程。
“如果有一天,你有了很多钱,你会做什么?”
“先把欠的钱都还了!”周易一跃而起,坐在凉席上,一见的这个问题,周易显然是设想过很多次,“那时候我爸刚过世,我妈又残疾,跟外面借了不少钱。我不喜欢欠别人钱的感觉,每天赚一点攒一点,还好已经还的差不多了。”
“还完钱之后呢?你想做什么?”
“我要给我妈看病。之前给我妈看病的医生说我妈的眼睛不是真的瞎了,是蒙了一层障,有专门治这种眼疾的药的,只是比较贵。等我攒够了钱,我要把她的眼治好…”
周易仰头看着星空,叹了一声,接着说道:“等她能离得了我,我想去外面看看。你知道吗,让我煎熬的不是每天起早贪黑,忍饥挨饿,而是听着车上的人描述着外面的形形色色。我知道有海,海水很咸,但我却不知道海是什么样的,真的有吃虫子的花、会发光的鱼吗?”
周易觉得自己像是一本有字无图的百科全书,读起来索然无趣。
对于生活,一见从没有过什么期待和想法,如果今天没有遇到周易,也许依然漫无目的的在街巷晃悠,饿了吃困了睡,而心底唯一的想法:变强,也是那么的虚无缥缈,永远只是一个念头而已。
也许是因为吃了太多苦承受了太多的重,想要逃离,去享受天真烂漫的生活,但,谁又能说他这念头生的错了呢?最起码,一见眼前的这个人,已经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没有逃避,也没有后退,正在实打实的和艰苦抗争,并且,不曾失去心中的善意。
聊着聊着,来了困意,两人睡去。
一大早,吃过早饭后,周易便送一见去了驿站。怕中意的师傅接了别人的单,二人来的早,这时候驿站里只有两三个人。转了一圈发现那马夫还没到,周易便和其他人打听起了昨天陈虎的事,得知那陈虎自街上一闹后便再没有出现,一见和周易心中默契,就没有再问下去。
谈话间,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男子牵着马车来到驿站,这人正是周易所等之人。
“孔大哥!”周易远远地喊了一声,等人来到跟前,带着一见上前将事说了一遍。
“没问题,小老弟,这你放心,保管一根汗毛不少的把你兄弟送到地方。一见老弟,你是要包我的车还是要跟别人搭个伙?”
“跟别人搭伙吧,这样孔大哥辛苦一趟也可以多赚一点。”
虽说周易一脸放心的样子,但是面对这个一点不比陈虎面善的中年男子,一见心里还是有些怯怯的。
当然,省这两三个银币并不是一见身上盘缠不够。周多吉给他备了五个银锭和十几个金币,以及些许平时用的银币,财不易露,做父亲的嘱咐过一见。钱在吉科村并无太多用武之地,有各种补助,又衣食无忧,家家户户都有不少余钱。
趁着等别人来搭伙,周易和一见在这临别之际忽然有了说不完的话,转眼见,街上已经聚了不少人,眼看拼车的人也到了,临上车前,一见走到周易的马旁边,从包裹里拿了他的两个素饼,和水囊,然后朝他憨笑:“这个就送给我吧,也算作对大哥你的念想。”
这是一见第一次用大哥这个称谓喊周易,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别扭。
一见这一喊,周易也是一怔,然后一阵欣喜。
“你路上要小心,虽然你没说为什么要从那地方出来,但我知道你也一定不容易。总会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的。还有,”周易凑到一见耳边小声说到“记住!不要透露自己是吉科村人,尤其对乌迪族的人。”
道别之后,孔师傅驾着马车,载着一见和另一人出了城,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一见走后大约一刻钟,周易一脸疑惑的打开一张小纸条,看完后急忙跑去马边,伸手一掏,果然有一个束口袋子,这一看,可是不得了,周易就要上马去追,刚骑上去,马儿踱了几下,却也不见他走,又缓缓的从马上下来,在原地愣了许久。
片刻后,竟然伏在马旁埋头哭了起来,手中紧紧攥着那张纸条。
“大哥,你行囊里有钱,快收好。看好伯母的病,做一只自由的鸟。”
纸条是一见上马车的时候塞给他的,还特意嘱咐周易过一会才能看。袋子里装的,是整整五块银锭和十枚金币。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张饼,一顿周易舍不得出的午餐。雪中分炭何其珍贵,所以一见想尽可能的帮助一些周易,不让他这黑暗中夺目的篝火熄灭,也是为自己驱散心中的阴寒。
应该说是幸运,出门的第一天,一见就遇到了在自己心中成为榜样的朋友,让他体会到了除了亲情之外的另一种温暖。这,也是若兰想让这个世界带给一见的礼物之一。若干年后,若二人再相遇,又不知会是怎样的情景…
秋分刚过,天越来越短,一日也只走得五十公里路,七八个小时,除了吃喝睡,马车几乎未停,一路也是过了不少山,阅了不少湖。五天的路程,孔师傅为了让氛围不至于太冷,时常讲一些段子,或者拉拉家常,胡天侃地的,慢慢的,一车人也就都熟了,氛围也活跃起来。
说来就是这么巧,那车上的另一位,也是个少年,名叫何远志,十八岁,乃是五象拳馆葛青松的徒弟,这次出门是奉师命去恩巴请一位善治内伤的老医师,为的,正是他那被逐出师门的师兄——陈虎。
“这也太衰了吧,不小心惹了一个,怎么还跟来一个”一见心里暗暗叫苦,同处一车,心是扑通扑通的跳,却又好奇,问到:“你那师兄怎么会受了内伤?”
何远志一脸无奈,说到:“我这个师兄啊,前几年就被师傅逐出师门了,没想到这次,师傅又要将他…”
话在嘴边,却又是想到什么,何远志转而说到:“我这个师兄啊,以前可没少欺负我,那时候我才十来岁,整天被他呼来喝去的,一不小心就被揍个狗趴。”
对这个师兄,何远志看来是有不少埋怨,说个没完,完全忘了一见问的是陈虎为什么会受了内伤。就这样唠叨着唠叨着,何远志竟然饶了回来,说到:“昨天晚上师兄来拳馆找师傅…”
话说昨天下午,陈虎撑回住处运气调息,想化解体内那股绽气,但调动真气与之对抗时竟发现,那股气劲虽少,却异常强悍,如果说自己的气犹如一堵气墙,那股气则像是一枚锋利的针,轻松穿过陈虎那并不细密的包围,游离在其体内不断的进行破坏。自知这股力量不是自己所能化解的,陈虎倒也聪明,吃了一些闭气散,就去找葛青松了。
这闭气散,是葛青松给陈虎的,原本的功效是在修行前吃下,然后强行运转周天,以此达到修炼的提升。就好像先将水库拦起,待河道干涸之后清理道渠的阻塞,再开闸放水时,水流自然更加的迅猛流畅。而现在,陈虎服用这闭气散是为了减缓体内真气的流动速度,减少所受伤害,拖延时间而已。
来到拳馆外,陈虎已是气喘吁吁,再加上内伤,浑身虚汗。因为闭气散的缘故,陈虎这种平时依赖惯了运气调息的人,现在一举一动全靠肉体的力量,一时难以维持。
陈虎敲了敲侧门,开门的,就是何远志了。一看是这个小不点,陈虎也不招呼,直接跨门进去,推开何远志就往里走。
“带我去师傅房间。”
何远志知道师傅和陈虎平日的来往,所以也不阻拦,前面领着,就到了葛青松的门前。
难得的敬畏之心,陈虎稍整衣衫,轻叩两声,在外喊道:“师傅,弟子陈虎求见。”陈虎对他这个师傅倒是一直十分恭敬,也不枉葛青松一直以来的偏袒。闭气散,一金币一剂,葛青松私下大约给了陈虎二三十剂。
“你来何事?不是已将你逐出师门,不得再入我五象拳馆吗?”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还请师傅相见,徒儿有事相求。”陈虎抱拳,躬身回到。
一对木门嘎吱打开,门后的是一年近五旬老者,一身青色长褂,一撮撮似犬牙的花白短发,正是五象拳馆现任馆大拳师主葛青松了。看他脸上挂有丝丝汗珠,想必刚刚是在练功,月光之下,仔细看些,老者身上还萦绕着淡淡白气。
陈虎见到师傅,不敢挺身,而葛青松瞥见陈虎的脸色,也没多说什么,便示意让他进屋了。
何远志本想进去服侍师傅左右,来到门前,没想到直接被吩咐让回去睡觉。好奇心作祟,何远志并没有乖乖听师傅的话,关了门后屏气凝神,偷听起来。
屋内,让陈虎盘膝坐下后,葛青松的第一句就是“跟谁动的手,伤成这样?”
“回师傅,都是徒儿不长进,被一个十三四岁的毛头小子伤了。”陈虎有些羞愧,不敢抬头看他师傅。一见个头小,看着确实不像十五岁的样。
“十三四岁的毛头小子?胡说!什么时候竟学会诓为师了?我观你真气微弱,什么样的毛头小子能让你气尽至此?”葛青松对这个逆徒的本事还是清楚的,别说十三四岁,就是二十三四,这镇里能伤他的能有几人?
“徒儿不敢欺瞒!今日就在街上,我欲教训一个弄脏我衣衫的小马夫,谁知途中冒出那个小毛孩挡在前面,徒儿觉得面子过不去,就要教训他,哪想那小孩竟然这样厉害,只是一拳,就将徒儿…而且,您看!”陈虎亮出自己的左腹伤处,撕裂的衣服下淤青一片。
“绽气?”葛青松一脸惊愕,连忙拽起陈虎的胳膊为其搭脉。
“气息凝滞却也浑厚,你吃了闭气散?”
陈虎点头。
又细细查验一番,葛青松才发现果真有一股气在陈虎体内窜杀,五脏虽无大碍,却引得心脉为之一颤一颤,这才相信陈虎受伤不假,但仍不信这是十三四岁孩童所伤。
葛青松自己今年四十八岁,虽非天赋异禀,却也不差,后天又极其努力,到今日才将绽气娴熟运用,而如若陈虎所言不虚,十三四岁就能将绽气运用于实战,恐怖如斯,且不管这小孩究竟是什么人,其背后势力可见一斑。
闭气散的时效还未过,不便医治,葛青松便询问起那名少年的情况,可惜事出突然,陈虎也只是记得一见所穿的是寻常的灰白色上衣,束口长裤,长相虽然就在脑海,但一想到细节,记忆总是闪躲,实在描绘不出个所以然,让葛青松很是无奈。
片刻过后,闭气散一过时效,葛青松就开始为陈虎疗伤。
只见他俩双双盘膝而坐,老者在后,调息运气后右手提掌聚气,呼吸间,见他右掌上萦绕淡淡土黄色雾气,随着手掌贴向陈虎头顶,大量柔和真气缓缓渗入。感知真气入体,陈虎连忙运转周天,将这股浑厚气息从百会穴向周身引导,循至各穴,捕捉那一丝丝入体绽气。
葛青松原本以为事情会很顺利,凭借自己的浑厚真气,驱散那区区几缕羸弱气息,还不是手到擒来。但是没一会,葛青松也有了和陈虎那时一样的感受,虽然他的气,比起陈虎的要致密很多。但见那几缕绽气被捕获之后,总能突破包围刺穿过去。
持续输出大量真气,葛青松也有些吃不消,脸上汗水吧嗒吧嗒的滴落在衣服上。已感到棘手的葛青松没有停下手来,倒不是对自己还有信心,而是别无他法,只能多输些真气给陈虎,尽量去护住他身上脏器经脉,为去找别的法儿争取些时间。
终于停下手来,葛青松面容疲惫,而陈虎,虽然知道气劲未除,但有师傅的真气护体,也是安心了许多。稍作调整,两人起身坐下。葛青松一脸凝重的问道:“那个少年,用拳头伤你的?”
“正是。”
“如果我猜的没错,那个少年,可能,是一位大剑师,至少,也是一位巅峰剑师。”
“大剑师?!”
陈虎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但这话出自他最信任的师傅。回想那个模糊的人,后怕起来。
器斗术修炼与体斗术完全不同,凭借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体斗术修炼起来更容易,所以拳法、腿法修炼起来要比剑、枪、棍法等更易精进,更容易出成绩。修炼前期,体斗术同阶要强于器斗术,但是优劣并存,大师级以上,则反过来了,器斗术的凛冽绽气可以轻松击破体斗术的罡气,更何况还有攻击距离的优势。到了圣者级别,凭借以气化形,器斗术圣者就是一人对上两三个体斗术圣者,也是丝毫不虚。
不过,器斗术的修炼也更为苛刻,除了更加繁琐艰难的修炼内容,对天赋的要求也要高的多。这也是很多剑徒、棍徒在修炼多年后无法突破师级的瓶颈后,转去修炼体斗术的原因。
“你体内那游离真气,依特性,应该是器斗术中的剑气无疑了,你呀,应该是庆幸自己走运,没让那位用剑,否则,你也就回不来了。”
葛青松摇摇头,叹了口气。到了自己这把年纪,能有多大的造化,已经可以看见底了,想这世界之大,果然是人才辈出。又看看眼前的陈虎,不觉有些失望和无奈,若不是自己一味骄纵,疏于管教,也许,凭他的天赋,晋升到大拳师之后再受大师伯点拨一二,自己有生之年也许还能见证这五象拳馆诞生第二位拳圣。可惜啊,可惜…
“你以后留在馆内,不得外出。经次一败,当明白你和这世界上某些人的差距,也别自诩天才了,世界之大,你我不过尔尔。至于你的伤,为师会为你想办法。为师也老了,你若再不改…”
陈虎转身跪在葛青松面前,双手握膝,说到:“师傅,徒儿知错了!前些年徒儿年轻气盛,不知分寸,惹了不少事端,让您老人家为难。在外这些年,徒儿心性已是改了不少,虽偶有争强好胜,不过好些面子,都不过分。徒儿本是孤儿,乞丐一个,幸得师傅抚养…”说着说着,陈虎的声音哽噎了起来,“徒儿视您如父,若能留在师傅身旁,我定潜心练拳,修身养性,不再让师傅失望。”
陈虎这番话,倒也是出自真心,就算以前,对师兄弟再蛮横无理,对葛青松倒是一直恭敬孝顺的很。一番肺腑之言,陈虎脸上已是垂泪几遍了,都说相由心生,此时陈虎的脸似乎也柔软了不少,咪咪小眼被泪水洗的也是柔和许多。
葛青松也是上了年纪,见徒如此,眼睛憋得通红。让陈虎起身后,向屋外喊道“远志!”
这一喊吓的躲在门外偷听的远志一冒冷汗,麻溜溜悄摸摸走到门前空地上,应到:“什么事,师傅?”
葛青松拉开门,吩咐到:“去给你师兄收拾一个床铺出来。现在你师兄有伤在身,重归师门,这件事你们师兄弟知道就好,不要声张。”
“知道了师傅,我这就去。”说罢,何远志就要退下,又听见师傅叫他。
“远志,这些个弟子中就你最乖,明日你替为师去恩巴找一下你郭师叔,邀他来馆里为你师兄诊治内伤。”
“郭师叔?他住在恩巴哪里?”
“他在经二街上开了间医馆。还有,记住,路上不要耽搁。”
“师傅放心。”
“还有…”
何远志又作揖道:“师傅还有什么吩咐?”
只见葛青松从袖口中摸摸索索,拿出两块银锭,递给何远志,道:“盘缠都不要了?”
何远志接过银两,憨笑着说到:“谢师傅,那多的钱,我给您买点什么东西吧?”
“出发前去陈礼记买两包茶饼给郭药师带去,其他的自己留着花吧”说罢摆手回屋了。
马车上。
说完了前因后果,何远志从提着的茶饼中拿出一个块递给一见“这可是陈礼记的茶饼,香极了,你尝尝!”
一见接过饼子,味道确实不错。
“我看你也才十多岁吧?叫什么名?怎么一个人呢?”
“我叫周易,今年十五了。想去恩巴学个手艺。”
何远志口中的郭师叔,让一见有了主意。
自从一见知道了这五象拳馆出过一位拳圣,对拜入拳馆也是有些想法,可惜自己跟陈虎已经结下了怨。而且一见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葛青松口中的大剑师了?当时那一拳虽然自己是卯足了劲…
“难道说自己平时所练的,就是葛青松说的绽气?难道…自己已经有大剑师的实力了?真的假的?”越想越激动,一见内心简直不敢相信,“是我真的这么强,还是他们太弱?”
这些想法不断在一见的脑海中翻腾,久久不能平息。在何远志提到那位在恩巴开医馆的郭师叔时,一见想到,这未尝不是自己接近五象拳馆的机会。而且为了不引起何远志的怀疑,妨碍到自己接近郭师叔,“学个手艺”,是一见苦思良久想到的最妥的原由,甚至期待着何远志会不会主动替自己引荐。
机智过人,这是一见第一次这样夸自己。
实际上,若是和眼前的何远志正儿八经的对上,只需一招,一见保准败下阵来,陈虎那次,只能说是意外。
听到一见管自己叫周易,孔师傅也不做声,虽不相熟,但周易他还是了解的,一路听来,他甚至怀疑这个管自己叫“周易”的小小少年,没准就是何远志口中所说的神秘大剑师。只是…孔师傅早年也是拜过师练过拳脚的,观一见气又短,步子也虚浮,又觉得自己异想天开。
后面两人闲聊,又问及家底,一见照搬周易,没办法,自己不会扯谎,所认识的人又不多。
这何远志,简直就是个话篓子。也不知是不是在拳馆憋得太久,一路上都说个不停。从自己年幼多病,到后来当徒弟,细至自己什么时候学会运气什么时候学会罡气,甚至平时是被一众师兄怎么欺负的、拳馆的伙食、师兄弟拿了生活费是怎么花的,该说的不该说的反正都说了,而且说得那是昏天黑地眉飞色舞。
而一见,竟然听的起劲,好像在为自己以后的徒弟生涯做预习一般,尤其是当何远志讲到他是怎么哄得师傅给他这个后学开小灶的时候,听得是格外认真。
那正是何远志自己总结出的廿六字真言,“溜须拍马”心法:知长短、明喜恶,大事忙小事拣,一尊二捧三争面,常伴左右树心间。
一见跟着一字一句的念,然后听着何远志解释其中种种:
要知道自己的长处短处,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事,要了解别人,投其所好,避其所恶,这样,上,能事半功倍,下,不会被穿小鞋;
与自己能力相差甚远的事不要躲,力所能及的事不要懒,细小琐碎的事挑拣着做,要会甄别和选择;
尊重与捧场,会让别人乐于与你相处,但不要一味的贬低自己,只有相互的尊重,才会有真正的信任;
要时不时露个脸,刷个存在感,否则做的再多再好,有好事时想不到你,都是白搭。
一见倒不是想日后靠这二十几个字来溜须拍马上位什么的,自己孤身一人,以后也没个倚靠,所以,学好如何与别人相处,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顺顺利利的朝自己的目标前进,这言行之术还是很有必要的。人与人之间,靠实力说话固然可以,但适当的交际手段,是为上计。
孔师傅在前面驾着马车,听着何远志一番高谈阔论,笑到:“没想到你年纪也不大,倒是很懂人情世故嘛。”
何远志道:“哎,没办法呀,不然每天我得在拳馆受多少欺负啊。愿苍天怜我啊…”说完,三人呵呵笑了起来。
一见也跟何远志聊起了自己所知的各种机械和能源矿石,说起这些也是滔滔不绝,竟也有些眉飞色舞。吉科村里没有私塾,小孩子都是由父母或有学识的长辈教育,这就让他们有非常多的闲暇时间,自会认字开始,一见的大伯周多可留下来的那些带着插画的书他便爱翻,也是自那时起,培养了对这些东西的兴趣。
当然,一见对这些经历已经做了一番修改。
从未接触过一见所说那些的何远志也是听的入神,而后一路上,二人就这样你来我往,越聊越投机。时间过得飞快,第五天上午,一行人终于来到位于吉科镇西北的恩巴市。
补:屋外月光银华,陋室内灯光昏暗,一见看到周易将伯母伺候躺下后又仔细的将被子压了压,这份母子情一见感同身受,又想起饭桌上两人之间的弄清,在屋外不禁叹到:“夜半月华光,烛影烁寒窗。缺月耀星辰,慈目映银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