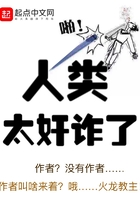三层甲楼游战船后面尾随着一艘乌篷,和游战船比起来显得异常较小。入夜时船身里亮起灯光,透过轻纱遮挡的窗户依稀能见舱一具曼妙身姿正挑灯夜读。
船头,抓着卤猪蹄的矮胖子有一口没一口啃着,黄色油渍顺着嘴角流下,享受至极。
船尾,腰插雕龙笔的阴阳人负手而立,江风夹着岚沧江特有的寒意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男人似无感般,漆黑眸子始终一动不动。
舱里传出悦耳书声:月连碧,洞湖庭,左起苍,右落黄,弓满星落九地荒。炎武败,千门素,三山五岳坐观唐。镌龙绣虎摆棋木,摇扇纶巾下子人,素目悲恸话凄凉。坐凤升,驾鹤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鲲鹏何物沾莫迹,云瑶赋歌踏声来。回首望,轻身落滴涟漪浪。何须狂,裹布泥足逍遥王……
书声于此戛然而止,啃猪蹄的矮胖子出奇没有继续嚼肉,坐在船头望着波光粼粼的江面整整出神。身处庙堂,或者说到过金鳞的人都知道这首词的出处,正是那座被冠以东胜三绝之一的邀月湖上,第七根镇湖倚琴柱上的《少年聊发狂草》上阕,那位人称七窍玲珑仙转世的季家二郡主所书,还记得当年这幅词横空出世时,惊得多少文人士子从此不敢执笔,甚至连高高在上的州主原本打算为这幅词题字,思来想去后却终究放弃。至于原因,似乎那位九龙袍天子只说世间万字皆难托起此柱之重。所以不了了之。
阴阳人收起严肃表情,再看乌篷内倩影时竟出乎意料带出丝丝悲凉。跟随天之娇女十几年头,可以说他是看着萧寒蝉长大。只可惜那座高高在上的金鳞何以同时落下两个天骄,既生瑜何生亮,古国的荒唐莫不是再次上演。
轻叹声,这位往上追溯几代有着正统后唐皇族血统的男人伸手触帘,却在指尖碰时悄然落下。微微摇头,不愿去打扰这位老太宰的掌上明珠。
船内,从金鳞跟到岚沧江的萧寒蝉懒坐在细草蒲团上,面前是一张小木桌和一盏清油灯,此时的骄女右手托腮,左手握着竹简,简上的内容正是从镇湖倚琴柱上沓下来的《少年聊发狂草》,她盯着龙飞凤舞的墨字渐入迷离。
不多时,萧寒蝉放下书简,拢了拢胸口衣领,江风来的越发冰凉。起身,撩帘,踏上船头。矮胖子在门帘撩起一半时就很识时务挪到旁边恭候,此时见女主子出来,肥肉乱颤的圆脸挂起象征性的谄笑。
抱着双臂的萧寒蝉遥望十里开外的三层甲楼游战船,半晌后喃喃自语:“权势争斗,以命相搏,摆棋人落子之意岂是那般容易轻易看穿,武夷之行看似季家驱你省亲,你又何尝不被当做最佳诱饵,如今金鳞庙堂年轻一辈争斗看似你四王家占了上风,却不知这份上风是那般摇摇欲坠,甚至倾倒之时很容易将你碾至粉碎,就算如此,你依旧愿意为他卖命?”
眼神逐渐迷离的骄女突然笑起,摇摇头自问自答道:“自然,谁让你是四王府的狗呢,只可惜你这条狗能猖狂到何时,你不知,我也不知。葬送在这条岚沧江里的狗命不下万计,任你命再重,恐怕江水也托的起。不像她,能寥寥笔墨变枯柱千万斤,实在让人想拿却拿不动,你和她比,差的太多。”
叹口气,停顿几息,忽然偏头看向站如石桩的矮胖子,不知是询问还是吩咐,道:“你说,今夜是他安然无恙,还是我那位未来夫君铩羽而归?该来的都布置好了?”
一脸茫然的矮胖子不出意料摇起头,比起夜黑风高杀人的勾当,他更愿意和背囊里那十来根卤猪蹄共度春宵。
没有得到答案的萧寒蝉自嘲一笑,再吹了会江风便返身走进船舱。
这一夜,是终点,亦或是真正的开始。
子呜湾,因其入夜凤过呜咽声不绝而得名,以前叫呜咽湾,后来大楚名士郑仲景说湾内声似士子无病呻吟,久而久之就被叫成子呜湾。此地是冕凉城的入江口,湾内竖插二十七根倚江石柱,相传冕凉地是春秋大士鬼谷入云梦山的起始点,鬼谷立地成仙后洒下二十颗糜粉,千年后变成这二十七根石柱。又有唯恐天下不乱之人散步石柱上有成仙窍门,能参透者便能追随鬼谷先生足迹寻觅仙踪。当然,此等异想天开之言只被众人当做茶余饭后的笑谈,也没人真傻到把石柱凿开来看。不过有一事倒是不假,因为二十七根倚江的存在,子呜湾水路错综复杂,格外隐蔽。
此时,入江口最后根石柱后。
装着鱼剑的黑色战船扬起半帆,江风吹得帆布鼓胀作响,若不是那条手臂粗铁索连着水下船锚,战船早已以离弦之资冲将出去。
这种鱼剑战船又有个令各地水师头疼的名号,就是敢死船。船头鱼剑以高精铁打造,长二十丈,占据船身一半还多点的长度。船体修长,极适合顺风冲锋。战船上除了鱼剑外没有其他武器,船员也只占到寻常战船一半,据说登上这种战船前,水手们都会喝碗绝命酒,领百两安家银,说到底便是此船杨帆时,九死一生刻。
桅杆下,银盔黄面将领仰望天色,手中遥望镜已经不知被他开合几次。面前,十七个黑衣蒙面水手肃穆静立。登船时他们都喝了绝命酒,领了安家银,只不过没人知道这次的目标是谁。甚至直到此时此刻,也搞不清是冕凉城里那位异姓王准备造反,还是真有敌袭。不过对他们来说,一百两的银子是比天还大的诱惑,做水师一个月不过两钱银子,这还是平时水师衙门富裕才能拿到手,更多时候有几个铜板已经是天大的好事。
本打着捧着官门铁饭碗的想法,哪知入错了行,又抽不得身,只能浑噩度日。
黄面素甲将领拉开遥望镜,再次仔细扫视江面,岚沧江虽然是东胜州里的主要水道,主供商贾人士,但子呜湾这片水域入夜后却鲜有船过,不仅因为石柱的存在,还因为此地多暗礁,加上北向南的江风在此处明显增强,所以大部分商船都会选择远离子呜湾的地方过夜,等天明再重新出发。
视野中,一个极不起眼的光点由远及近缓缓出现,黄面将领眼色猛震,将遥望镜插入腰带,回身面对众人,训话道:“今夜我等十八人踏上鱼剑船,就是要将对手沉葬在这岚沧江底,提督大人将此等重要任务交与我们,身为冕凉的勇士,兄弟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有!”众人齐呼。
黄面将领满意点头,继续鼓吹道:“好,各位不愧是我冕凉儿郎,请大家放心,此战之后,你们的妻儿老小自会有人照顾,你们每个人的名字,也都将刻在提督府那面功德碑上,被全城百姓瞻仰。此次是三十年来我冕凉水师第一次出战,我们一定要打出精气神来,让对手知道我们的厉害,明白没有?”
“明白!”
一一扫视船上每个人,黄面将领从左至右依次走过,替他们正襟,替他们打起,末了回身挥手命令:“第一组,扬帆,目标西南。第二组,准备好火药,听我命令随时引燃。第三组进入船舱,给我加足马力,冲锋。”
令下,十七蒙面水手纷纷行动,秩序井然执行黄面男人下的每一道指令。
帆起,桨动,鱼剑战船飞速驶出子呜湾,如游鱼般没入夜色下的粼粼江水中。
三层甲楼游战船上,简单用过晚饭后宁仙安重新躺上铺了冰原雪狐绒的卧榻,西暖阁里的一众下人,数细心还得算朱鹮妮子,白天从七马木流换成游战船时,妮子特意把绒毯取下来,虽然如今已经入夏,但夜里的江上依旧寒意十足,主子出行怎么也得体面点不是。
宁仙安百无聊赖翻看起吃饭时从木箱随便翻出来的《上亭烂花白马枪杂耍集》,这本书原先放在游书楼四层,铸的是南宋名将岳飞的生平事,其中也包含当时闻名于世的岳家枪法。书的作者是西楚有名的枪王韦怍,相传如今的七十二路啸马银枪就是自岳家枪法演变而来。
做事周全的妮子朱鹮此时正领着下人安置沐浴屏风,即便身在船上,她依然努力维持主子在西暖阁中的生活习惯。
狐媚喜鹊自然还是和少年白起待在一起,只不过眼下不比白天,捧着《习水观阴战事录》的少年就像久旱逢甘霖,一字一字细读,偶尔象征性搭一声妮子。弄得妮子很是尴尬,想说话吧,又不好打扰,不打扰吧,又没啥事做。所以窗户边就出现很不和谐的一幕。媚劲十足的女子隔老久说句话,捧书读的少年也隔老久答一句,任谁都能瞧出二人压根是焚琴煮鹤。
至于袁泊虎,用过晚饭后就背着巨斧下到二层,顺便把于易俭和王伯山也叫下去,缘此楼梯口就只剩下半老徐娘的红芍,和人熊般的魏石开在坚持守楼梯的重要差事。
夜深时,除了读书的少年白起还蹲在油灯下津津有味品咂字海,其余几人皆已沉沉睡去。
然而这种静谧并没持续多久,就被火急火燎跑上来的甲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