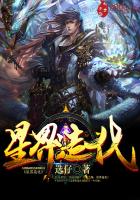“四条腿的牲口天生就是被人骑的命,跑的撒丫子快,赶明儿把这些畜牲全部砍成两条腿,和咱金鳞的走卒比比脚力,赢了的做人,赏他个百两黄金,输了的当牲口,也让咱马棚里换换花样。”
背着百十斤重的世子殿下一路狂奔,少四爷宁仙安不忘调侃一番,豆大汗珠顺着额头流下来,心想前天夜里和那半老徐娘的花娘子共度春晓也没这么累。
“太宰家两匹的卢不错,老骨头每次见那两头畜牲眼睛都放光,只可惜那几个狗奴才不开眼,也不知老东西哪辈子修来的福分,能得到那几条忠心的驴草,要不你想个法子,喂几个狗崽子春药也行,把的卢搞到手。”
脸面白净的季可道显然被勾起兴趣,轻轻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这话要是落在旁人耳里,估计只会被扣个失心疯的名头。
东胜州州府金鳞城里冠以太宰之名的有且仅有那一个,当朝一品,手握整个州地文官生杀大权的裁决者,位列三班。
当然,倘若知道说这话的是从狗奴才少四爷口中说出,大抵只会会心一笑,七真三假吧。
为啥?
因为这位真是爷。
上气不接下气的宁仙安突兀咧嘴暗笑。一想到给金鳞四大神捕喂春药,那场面,估计有点意思。
眼见马队越来越近,他忍不住朝背上黄冠青年呛声道:“话说回来,那蒙汗药你哪弄来的,驴草的咋吃了没效果?”
自诩少三爷的季可道扯着微弱气息回道:“花娘子闺房里拿的,不是你告诉我那有吗。”
宁仙安脚下猛地趔趄,好不容易稳住身形苦笑道:“我的主子大爷啊,你是真实诚,那包蒙汗药被我稀释了十倍,给花娘子用的,拿来给驴草的吃管屁用。”
季可道没好气辩解道:“你不早说……”
赑屃碑!
相传千年前东胜州第一任州主开疆拓土之时偶得龙物赑屃,有安国震邦之效,后以人力打造界碑托赑屃之上,置于大荒山脉门户,以此定为州国边界。
过赑屃便入东胜。
碑下,宁仙安小心翼翼放下季可道,自己则一屁股坐在地上,靠着赑屃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身前二十步,一列马贼驻马而立,为首者虎皮革衣,豹头环眼,左手勒缰绳,右手垂于腰间执一阔口马刀,朝碑处怒目而视,喝道:“跑啊,怎么不跑了?千杀的狗东西,今日定要让你二人生不如死。睡老子的女人,还,还狗草的……”
马贼首咬牙切齿,说到最后眼眶都开始泛红。
强憋着笑意的宁仙安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在赑屃上,眯起眼皮朝马贼首裤裆瞄了眼,嗤笑道:“不就是切了你档里黄豆大点东西嘛,至于追你爷爷两百多里地?”
“再说爷爷我从来都是讲道理的,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睡你女人了,这大荒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母的都是你女人?爷我看你那匹马还是母的呢,咋的?也是你女人?”
“放屁,黄口小儿,死到临头还敢逞口舌之利。小的们……”
宁仙安蔑了眼跃跃欲上的马贼,反手拍了拍脑后的赑屃碑,道:“我说,这是啥知道不?别怪小爷没提醒你,在这块地界上,还没人敢动小爷我一根毫毛。”
“哼哼,毛没长齐的东西,口气倒是不小,小的们,谁先抓住这两小子,赏花雕女人。”
贼马首一声令下,加上花雕女人的诱惑,众马贼登时气血上涌,纷纷猛夹马身,暴冲而上。
“驴草的狗,要女人不要命。”宁仙安狠狠呸了口,抓住季可道的手朝旁边就地滚出半尺,躲过射来长矛,紧接着将后者护于胸前,脚下发力越过赑屃碑。
“想跑?”
马贼首目中寒光迸射,脚掌狠踏马镫,身体飞跃而起,与此同时,道道肉眼可见的蓄力波纹在其周身翁然乍现,半息时,力纹骤然而凝,由虚转黑,随即如流水般汇于马贼首前,于虚空勾勒。
再半息,一个漆黑的“刀”字跃然浮现,以马贼首为中心缓缓转动。
“还是个练家子?”逃跑间隙瞟了眼身后的宁仙安大惊失色,脚下却是不敢停下动作,死命往前。
断刀,斩!
马贼首右手阔口马刀举于头顶,左手牵引飞旋“刀”字浮于身前,阔口马刀悍然落下。
顷刻间,“刀”字再如流水般飞速附于刀口上,原本精亮的刀刃闪电般变得漆黑如墨。
马刀斩下,一道憾力刀纹爆射而出。
气机锁定。
直逼宁仙安后背。
“你别管,我来挡。”眼见刀纹逼近,缩于宁仙安怀中的季可道强撑欲起,右掌上已见力纹升腾。
“你干啥?不要命了。”宁仙安狠狠瞪了季可道一眼,一把抓住后者抬起的手掌,双臂用力紧了紧,“你的命比我精贵。放心,我这狗奴才福大命大,死不了。”
咻!
如墨刀纹疾驰而近,不偏不倚正好落于宁仙安后背。
咳!
一口老血喷出,宁仙安如被千斤重力击中,裹着后背的布衣瞬间化为糜粉,一条血印自后凸显,延生至腰间,而他也沿着刀纹方向飞扑而出,落地拖出足足五米方才停下。
“仙安。”眼见宁仙安气息萎靡大半,季可道怒不可遏,挣扎着想要挣脱怀抱,然而动了几下却发现环住他的手臂比套狼的夹子还紧。
“咳咳,不是,叫你,别动,嘛,老子,挺得住。”宁仙安佝偻起身子将季可道护在身下,大口大口咳着老血。
众马贼蜂拥而上,将二人围在中间。
马贼首狞笑着走来,子孙根的伤势加上刚刚动了气力,让他脸色苍白至极:“跑啊,怎么不跑了?哈哈,放心,还没折磨够呢,老子可不想你们就这么死。”
“小的们,把他们绑了。”
宁仙安强忍背后剧痛,嘶哑喊道:“等等。”
贼马首眯眼道:“怎么?还想耍花样?”
匍匐着坐起身的宁仙安喘息道:“小爷我都这样了,还能耍什么花样。”
贼马首冷哼:“那就乖乖束手就擒,跟老子回去。小的们……”
“诶诶,不是叫你等等嘛,着啥急。”宁仙安一只手撑在地上,缓了两口气后抬头瞧了眼马贼首,再抬头,望了眼天上,嘴角忽而弯起,大喇喇坐着说道:“爷自打下生开始就从没当过圣人,下三滥的事倒是做的不少,真要和你掰扯估计能把你耳朵听起茧。”
“旁人眼里所谓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爷只当是狗屁,留口气把酒言欢赏花阅美人不比死了强?就像你们,缩在大荒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还不是为了给自己留口气,真是带把的主,就一路杀到金鳞去,站在“皇”字门下大叫三声姓季的都是驴草的,老子敬你是条汉子,说不好摆几坛子虎跑和你叫嚣几番。”
“只不过,你不是这号人物。”
贼马首额顶青筋逐渐暴起。流寇也好马贼也罢,刀头舔血为的就是性命和名声,他从不以好人自居,纵横大荒山数载,在这一带好歹也落个不错的名声,何成被一个看上去小自己两轮的黄口儿如此戏谑过。
九州上有胆子犯事的勉强称得上狠角色,犯了事还敢跑到无主之地称王称霸的算得上狠人,称王称霸还能保住性命的更是狠人中的狠人,恰恰贼马首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后那种。
贼马首深吸口气,面目狰狞道:“小子,本来打算留你条命到天明,不过现在老子改主意了。
宁仙安突兀笑道:“这话原本也想说给你听。”
早已越过赑屃碑的马贼首闻言心头猛颤,视线急速扫过周围,直到确定这地方除了自己一帮人和两头待宰羔羊再别无他人后,才稍微放点心,“小子,少在那虚张声势,老子这就送你上路。”
宁仙安强撑起摇摇欲坠的身子,后背传来的灼烧感让他忍不住吸起凉气,“和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这就叫差距,明白吗?哪怕在江湖这滩浑水里打家劫舍,也要稍微讲点道理,就像小爷这样,死也让你死的明白。”
宁仙安指了指天上,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说道:“往上看。”
早已习惯追杀和被追杀的马贼首身体骤然绷紧。
力纹再现,如墨“刀”字流水般汇于身周。
做完这些后才闪电抬头。
入眼处,蔚蓝穹顶下一个肉眼可见的黑点不知何时出而盘旋。
大荒山里鸟兽多,偶尔能见三两只飞禽于空盘旋并不出奇。
被大当家一番态势惊到的众马贼同样抬头见到盘旋大鸟,不过以他们的目力自然看不出个中蹊跷。
马贼中有叫嚣者。
“一只鸟而已,这小子又在虚张声势。”
“没错,老大,这两人鬼精的很,指不定还在打什么主意,咱们好几十兄弟的性命都折在他们手上,别跟他们废话,看我取他们狗命。”
和手下群情激奋的模样不同,马贼首盯着黑点的眼神却是几经变换,从平淡,到深凝,再到惶恐,仿佛正做着何等挣扎。
雨隼,而且是东胜州独有的鸾隼,众观九州大地,只有极东和极北之地才产出这种灵隼,不同的是极东之地所产名为鸾隼,以快著称,极北所产名为迦楼,以猛著称,皆为禽中之王。
凝视片刻,马贼首突然散去周身气力,转而直视笑容可掬的宁仙安季可道二人,沉声道:“山高水长,他日若能得见,你我再算今日之帐。”
众马贼闻言皆惊,倒是宁仙安好似瞧白痴样看着他,冷笑道:“说了爷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的道理,爷我两岁就烂熟于心,你觉得我会放走一个天天念叨我比念叨自己女人还多的贼?”
马贼首充耳不闻,大手一挥示意撤退。
见他如此决绝,众马贼这才察觉到些许不寻常,纷纷后退。
“想跑?”宁仙安面容陡然变得狰狞,环指入口,清凉的哨声直冲天际,而后半息,天空中鸾隼发出更为清凉的啼鸣声,声传数里。
眼见马贼们仓皇遁逃,宁仙安喉咙里猛地发出如兽吼般低沉冷声:“小猫,今天你敢放跑一个,爷爷我扒了你的猫皮。”
声落时,阵阵虚脱直扣脑海,宁仙安终是撑不住伤痕累累的身子,侧身倒下。季可道眼疾手快将其抱住,轻柔地将他脑袋放在腿上。
与此同时,大地忽而急速颤抖,两股黑色洪流从东边浩荡驰来,激起漫天尘土。
当头,两柄兽案将字旗赫然扎眼。
一绣虎,上书“袁”。
一绣狼,上书“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