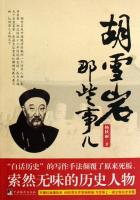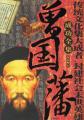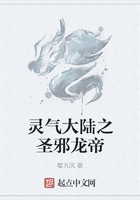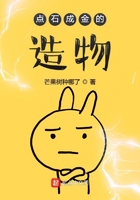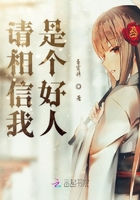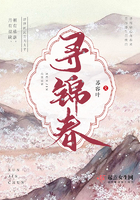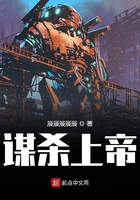1946年7月,为召开国民制宪大会,雷震不停地穿梭于各党派之间,尽管有第三方在不断斡旋,但中共出于自身利益以及对当时局势的全面考量,拒绝参次这次制宪国大。青年党则以民社党是否参加为前提,亦未提出参加此次会议的最后名单。在雷震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先拿到青年党出席制宪国大的名单,并公诸媒体,然后再由雷震亲自出面敦请民社党参加这次会议(详见第十三章:“制宪国大”背后)。而制宪国大后政府改组,以期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雷震又承命奔走于民主同盟、民社党、青年党之间,自1946年11月27日起即与各方进行广泛会谈,并在1947年年初将会谈带入磋商具体事宜阶段。民、青两党这时均主张由国民党与中共先开和谈,如不成功,再议改组政府之事。1947年1月8日,国民党派员前往延安,蒋介石嘱咐雷震将此事通知民、青两党。十天之后,中共正式答复,声明重开和谈应以1946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及取消宪法为先决条件,蒋介石未能接受。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与民、青两党的商谈才正式转到政府改组方面,仍由雷震负责从中协调。1月20日,政府方面的代表在立法院与民、青两党会谈,对改组方案,青年党表示同意,民社党仍迟疑不决。此时雷震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青年党对于名额分配不满,要求增加代表名额;民社党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争论不休,张君劢不赞成参加联合政府,汪世铭等人则认为“民社党应在行政院有主导力量” 。雷震及时抓住了这一分歧,反复做工作,一再强调“今日局面,要实事求是,三党合作,应以国民党为重心,然后始能挽救其政治局面。” 2月中旬,民社党终于同意参加立法院、监察院、参政会、宪政实施促进会,只是对参加行政院与决策机构仍持有保留意见。
在当时,雷震被记者公认为“南京第一忙人”。著名记者、现任北美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的陆锵先生于1979年3月21日雷震病逝后的两周,撰文回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期间记者们对雷震的总体印象:
当时,和谈新闻是头条新闻,南京、上海和全国其它各地以及外国派驻南京的记者,都钻头觅缝,废寝忘食地去打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人的各人的主要来源,各人有各人的新闻网。可是每遇和谈进行到关键时刻,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想去问问雷震,出了什么岔子,有了什么希望。因为,他身兼政协秘书长,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国民大会筹备委员,后来又是国民大会的副秘书长,由于他忠诚对事,热诚待人,在各党各派中,建立了信用,结交了好多好朋友,不少人都愿意和他讲知心话,因而,他所掌握的情况就比较全面、可靠。
当时有许多政客似不愿与记者们打交道。他们“畏记者如虎,或视记者为敌人”(陆锵语),雷震则尽量满足记者的要求。当记者看到雷震双眼布满血丝,仍在不知疲倦地接受他们的采访时,心里过意不去,有时也会说出一些比较客气的话。每逢这时,雷震就会说:“用不着讲客气话,我们大家都是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奋斗嘛!”秘书长的工作事无巨细,由于雷震办事一向认真,就显得格外地忙碌。他既要参加各种会议,又要去黄埔路官邸向蒋介石直接汇报,更要考虑到各党各派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小至一张卧铺车票,大至名额分配不均,等等,这些都需要由雷震亲自出面来安排或解释。这一时期,雷震每天工作在十六个小时以上,没有娱乐,也没有假日,有时需要休息一下,但走进西桥五号家门时,常常又是记者先生、小姐“守株待兔”地在等着他,只好又强打起精神接受他们的采访,实在是支持不住了,“顶多打两个呵欠而已。”由此可见,雷震当时之所以使出浑身解数,终日周旋于各党派及记者之间,“决不是单纯的折冲樽俎,而是有一种理想在支配着他,这种理想就是他晚年以身殉之所表现的志节” 。
雷震与蒋介石结缘,首先因为他与王世杰的亲密关系,其次才是在国民参政会。当然,雷震本人特殊的政治才干,也应是蒋介石委以诸多重任的原因之一。从客观上讲,雷震留学日本多年,蒋介石也曾在日本学过军事,自然会有一种“同为留日的亲切感”;雷震二十岁就在日本加入了国民党,其介绍人又是戴季陶、张继这两位国民党的元老,“对党性的成分当无问题”。1926年回国后,又是王世杰早已延揽的重要干部,由于蒋介石对王世杰的信任也因此而延及对雷震的一种信任。雷震在国民参政会期间,受到王世杰的器重而委以秘书兼议事组主任,被蒋介石看中之后,又增加了一些兼职,如国防最高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专门委员”,参与当时的预算审议工作;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成立后,蒋兼任会长,雷震兼任该会的秘书。在国民参政会附属的委员会中,大凡由蒋介石本人兼任会长的,即派雷震出任秘书;凡与各党派成立的联合组织,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也是任命雷震为秘书长。
国民党内部当时有两大派系相争,即所谓“CC系” 和“政学系”,都在蒋介石面前争宠、效忠,“眼看着雷震已由‘单线作业’与蒋介石建立了直接关系,与其嫉妒他,不如拉他‘入伙’,所以这两派的人物对雷震都尽力拉扰,张群组阁时雷震被任命为政务委员即为明证。” 但“独往独来”的雷震,无疑是一位坚定的“拥蒋派”,每逢关键时刻,都表现出一种忠诚不渝的立场。1949年1月,朝野上下要求蒋介石下台的呼声日渐高涨,王世杰、雷震、胡适等人均为反对蒋下野的少数派人物。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 通电要蒋下台,国民党CC派人物刘百闵也认为,蒋的下台可使腐败势力“无所依恃”,青年党左舜生甚至主张蒋介石“放洋出国”,张君劢则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作者注)前致函蒋介石,劝其下野……1949年1月3日,王世杰给雷震打去电话,表示“蒋介石不宜下野,战局仍有转机等”,并约雷震一同前往李宗仁处,以“探听口气”。雷震也认为蒋介石即使下了台,李宗仁也无力维持中国的局面。
在当时倒蒋的势力中,以团派人物黄宇人 为最激烈者,雷震对此一直深感不安。1949年2月20日,他约黄宇人夫妇至中山陵梅花山观赏梅花,借此机会二人“交换对时局的意见”。黄宇人对蒋介石认识颇深,认为“蒋以个人第一,权力第二,儿子第三,国家第四”,并斥责蒋介石“二十年之工作,完全是为保持自己之权力”,对此深恶痛绝……雷震当场批评他“不够恕道”,竭力出言为蒋介石辩护。其实早在1937年,雷震本人就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一种支持。当时他有一种很现实的想法,即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才能抗日救国,这个观点多少受其“政学系”的影响。对雷震来说,建立统一的政府不仅是救国的条件之一,也是步入现代国家的方法;而统一的政府应力行法治,整治社会腐败;政府内部需要养成一个廉洁的风气,为达到此目的,唯有公平的用严刑重典 。雷震还认为,好的在野党应当持有两种正确的态度,即若不能出以友谊而支持现行政府,也应持一个客观的立场来批评政府。
这些都反映出雷震“身为国民党员,对党的感情与期盼,使其更注重实际,即以国民政府的胜利为优先,亦以民族思想……为优先,对于政府有侵害人民权利措施,采取容忍态度,不予苛责,劝反对党人士多多包容,呈现思想与行动的落差。” 正是由于这一点,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雷震试图以“拥蒋救国”为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在种种场合下,也不止一次当面向蒋介石表达“速谋重大改革的意见”。尽管无效,却也尽了知无不谏的职责,这在当时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中,可说是无出其右者。从1939年到1949年止,雷、蒋二人的“缘”与“情”渐次达到了一个沸点。关于这一点,马之骕认为,雷震“本来是具有‘民主宪政’思想基础的人,但他自从当过‘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之后,因与蒋介石建立了浓厚情感,所以对他的民主自由理念不无影响。譬如他对蒋‘言从计行’,事无巨细作报告;无论对党内外人士,无论在任何场所,只要有人批评蒋介石的不是,而雷震当即提出解释或答辩。” CC派人物刘百闵戏赠雷震“新CC”的绰号,其中无不暗含嫉妒之意。在刘百闵看来,雷震对蒋介石的效忠程度已不亚于某些“CC分子”了。
尽管如此,仍不能抵消雷震在内心对蒋介石的某些看法,毕竟他是一位有着自由民主理念和素养的人。他之所以拥蒋,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只不过是一种“孰先孰后”的选择而已。随着日后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深度认识,内心的民主宪政意识再度萌发,以致于在不久的将来与之渐行渐远乃至决裂抗争,这都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决定下野,当天下午他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常委宣布此事,下午三时乘专机飞往杭州。这天晚上,雷震与王世杰乘夜车前往上海。在日记中,雷震这样写道:
蒋公下野,改造依然困难,如稍有不慎,则自趋崩溃,因德邻先生(即李宗仁,作者注)一派亦无人才,恐不易大刀阔斧来改造也。惟今日之局面必须改革,我前次曾于蒋公面前陈之,劝其以最大决心,最大勇气,如北伐时之勇气改革现局,并提供意见,当时蒋公听得颇不耐烦,不到一月局势演变如此,蒋公自己亦要负责。
1949年2月12日,雷震在上海胡适的寓所用完午餐,两人就当前的局势推心置腹地谈了数小时。其间,胡适示以陶渊明一首小诗表明心迹,雷震看过之后,认为这“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种桑长江边 / 三年望当采 / 枝条始欲茂 / 忽值山河改 / 柯叶自摧残 / 根株浮沧海 / 春蚕既无食 / 寒衣欲谁待 / 本不植高原 / 今日复何悔?”也就是在这一天,胡适对雷震说,蒋介石曾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 。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适的这一番话在雷震内心引来相当大的悸动。从某种时空来讲,雷震后来之所以在台湾组党与国民党威权体制相抗争,受胡适等人(包括蒋廷黻)的影响为最大,这也是晚年雷震在精神上与胡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9年4月3日,雷震、王世杰等人赴溪口看望下野的蒋介石。这一天特别冷,到达后“蒋经国来迎,同至宁波午餐”;当晚,蒋介石在其老宅约餐。席间,雷震将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意欲筹办《自由中国》杂志的设想报告给蒋介石,“渠表示赞成并愿赞助”。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听到胡适、雷震等人意欲筹办《自由中国》杂志这件事,以当时蒋对胡适的尊重,以及他对王世杰、雷震等人的高度信任,自然会支持这件事,绝然不会想到《自由中国》这份经自己同意创办的杂志,在若干年后会成为挑战国民党威权政治的舆论重镇,更没有想到雷震这位忠诚幕僚将成为自己政治上的最大敌手。这一切都缘于雷震具有民主政治理念这一事实,他虽然一度拥护蒋介石,甚至超过了国民党内部其他人,可一旦在时局出现嬗变而又无法进行调和时,最后的抉择又必然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上的走向。雷震与蒋介石的关系由亲密而分离,看似偶然,实又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