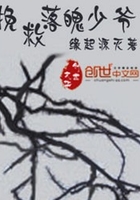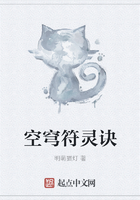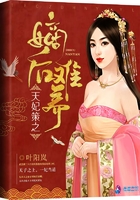1946年1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受命出任秘书长的雷震,此时已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位显要人物。这里所说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别于1949年后受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人民政协”,故今天我们习惯称之为“旧政协”。
“旧政协”无疑是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在经过重大较量和妥协之后,理性地朝着和平的方向迈进的一个政治产物。具体地说,是在国共两党于1946年1月正式签订“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这一停战会议基础上而召开的,“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战协议在早晨签字,上午10点方开成了政治协商会议” ,如果没有这次停战,“在政治上也就无从协商起”。无论如何,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可是由于“日本投降国共两党争着‘受降’,国内许多地方已由共产党给解放了,受降接收了,国民党却不予承认……就在各处打了起来。后由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停战,就由马歇尔代表美国居间,组成停战会议” 。
1945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支能够真正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最具号召力的政治力量。其它一些政党,如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主同盟),虽对国民党多有不满,由于自身之实力,则往往不能与国民党相抗衡,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党派并无自己的军队。因此“所有在野党派,除共产党可以用武力抗争外,其它党派对国民党所作所为,均敢怒而不敢言” 。中国政治大格局因抗战八年而出现的这种实质变化,逼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停止内战的问题,并由此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这也是当时美国政府竭力想促成的一件事情 。
在此之前,即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就抗战胜利后时局发表《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呼吁“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重要问题”,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政府才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人飞赴重庆,国共两党在经过反复商议之后,签定了一份《双十协议》,确定将召开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1946年1月“旧政协”的由来。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选中雷震为大会秘书长,不外乎他在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任内,为人诚信,办事得力,颇得人缘,无论各党各派或无党无派的参政员,都愿意与之打交道;尤其是当各方意见不相统一需要沟通时,多由雷震出面负责协调解决。不过,在马之骕看来,雷震这个秘书长的任务非比寻常,因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数十年,党人已养成‘坐大’的习性,各党派积怨已深。尤其共产党一直是刀枪相向,而今要面对不同的脸色,不同的意见,以笑脸言和,当然要费一番周章。究竟如何沟通、协商,藉以达到各党各派合作之目的,就要看秘书长的修养与其运筹帷幄的方略了。”
“旧政协”于1946年1月10日开幕,至1月31日闭幕。大会的目标与任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各党派相互协商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从而实行宪政。与会者来自五个方面,其中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党代表五人,社会贤达人士九人,总共三十八人 。在这些代表中,原有参政员占二十二人超过半数以上,雷震在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时,与这些代表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大会分设五个小组,即宪草、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等。既然这次大会的目标在于实行宪政,就必须先起草宪法,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立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显得十分必要;而将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也不能由国民党一手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又必须改组其政府,以容纳各党各派,于是又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政前,其中有一个过渡时期,必须有一个共同纲领,即有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小组,当时只负责调处停战,国共两党军队如何才能变成国家的军队,也就是实现军队国家化问题,尚需协商解决,所以军事小组的设立,则担纲此方面的重任。
这五个小组都是围绕国家即将实行宪政、走向和平统一而工作的,环环相扣,互相渗透,一个也不能缺少。经过二十二天的激烈争执,会议总算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协议、国民大会协议、宪草问题协议、改组政府协议等五项。
这些议案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国府委员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它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对于长期推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来说,事实上并不想真正履行这些协议,1月31日会议闭幕当天,宪草问题即已暴露出来。这一天上午八时,在综合小组会议上,为清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商决尚未取得协议的若干问题,争执了很久,一直开到下午二时才取得了最后的协议。当时民主同盟总部在重庆国府路300号,政协会场在300号之东的国民政府礼堂,国民党中央党部在300号之西,彼此相距不远,其间各种消息传递得很快。据梁漱溟先生回忆:
政协综合小组下午二时散会,国民党中央就于三时起开会一直到六时,好多国民党人如谷正纲、张道藩等在会上吵啊,吵啊,顿足嚎叫,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蒋才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盖蒋视政协如无物),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蒋流露出宪草有修改挽回余地,伏下了祸根。
“政协宪草”之所以出问题,与当时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有关。
关于宪政模式,当时存在三种蓝本:一,英美式的国家宪政;二,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对于国民党来说,当然要标榜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并早有一个“五五”宪草作为蓝本;民盟大多数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多半趋向英美式宪政;共产党也知此时若提出苏联式宪政恐怕不会通过,所以希望能有一个英美式宪法就行了,只要能打破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权的政治局面就是最大的胜利。周恩来曾对马歇尔 说:我们愿意要英美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 。这样一来,三种宪政蓝本就剩下了两种,问题在于如何折衷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需要政治上的相互妥协。这时民社党的张君劢提出:应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原有“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