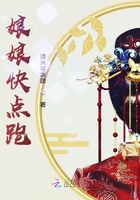奉忝十七年。
“宁儿,终有一天,我要去沙场做一个将军,统领十万大军!”八岁的武驷站在石头上,眼里满是骄傲。
石头下站着个八岁的小女孩,怯怯地看着他,不敢言语。
武驷看小女孩好像不感兴趣,怏怏地从石头上跳了下来。巧的是石头本身大又锋利,武驷的脚钩在边缘,竟直愣愣摔了下来。
“哎呦!”武驷的手臂蹭掉了一层皮,此时正火辣辣地疼着,“嘶……”
阿宁看到这一幕,慌了神,想到师父交给她的什么什么草药,也不知功效,就胡乱地抹在了武驷身上,抹完药,又想到师父说的:在宫中要谨言慎行,不要招惹是非。于是竟抛下武驷回了自己的住处。
她的师父是宫里的画师,师父的祖上是行医问药的江湖郎中。便是在为大王武夷作画之际,恰巧带着阿宁的缘故,让武夷喜欢上了这个小丫头。这几日宫里热闹,武夷就准了阿宁在后宫来去的自由,让她去陪公主殿下们玩耍。
这会不过晌午,阿宁却回来了。师父最知她的秉性,虽看上去柔弱胆怯,玩起来把戏却是最多的,这么早就回来,一定出了什么事。
“阿宁,你做了什么?”
阿宁也不好隐瞒:“回师父的话,驷殿下他……他摔伤了手,我心里害怕,没有管他就跑回来了……”
“什么!”师父心下一惊,虽说长公子之位已定,可这三殿下在大王面前却也十分讨喜。且不说是否是阿宁出手伤的他,就是阿宁对他不管不理这一条,便足够让她受罚。思及此,他对阿宁说:“阿宁,收拾一下,和我去见驷王殿下。”
阿宁本能的想拒绝,可见师父神色坚定,也不好反抗。只是嘟囔了一句:“为何您怕我淌浑水,却又叫我去见他……”
“你这孩子!不做错事,可避祸端;做了错事,就该承担!”说着,拉起阿宁去找武驷。
昌秀殿中,常娘娘正心疼地抚摸着武驷的伤口。
“母妃,您轻点!”武驷忍不住皱了皱眉。
“驷儿,这伤是哪里来的?”武夷今日住常娘娘这里,看到武驷这样,不免多问了一句。
“这……”武驷眼睛转了一圈,便将其中的利害分析了个透:若说是自己嬉闹所致,父王一定会责罚他;若说是那个进宫不久的丫头所致,只怕阿宁会被拖去杖责几十。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说:“回父王,是那个新来的丫头推了儿臣一把……”声音中带着委屈,只差几滴眼泪便要惟妙惟肖。
武夷听了,那里会舒服,当即宣了画师前来。这时画师已带着阿宁来到了昌秀殿门口,听到传召,他神色一凛,拉着阿宁快步走了进去。
“参加大王,参见……”
“废话少说!”武夷有些厌倦地打断了画师的话,“阿宁,孤且问你,有没有伤了驷儿?”
阿宁先是一愣,看见武驷在一旁偷笑,才明白武驷告了她的状。她低下头去思考,这在旁人眼里却成了逃避。
武夷看这情形,正要发号施令,却听阿宁张口辩解。
“臣女本一介布衣,驷殿下在上,自只能居下。不过是见殿下落下石头,却成了让他受伤的把柄,这是何道理?”阿宁说这话的时候,瞪着武驷,像极了咬人的兔子。
武驷本就不怕责罚,不过是抄几页经文功课。之前说的一番,也只为了讨个乐子。这会见这丫头着了急,竟神使鬼差地道出了真相:“父王,孩儿刚才说的有所隐瞒,不过是为了逃过责罚,却不想这女娃如此较真,只怕连累了她,恳请父王问我之责,放了这小丫头吧。”
武夷听到阿宁所言,有些佩服她的胆识,武驷又主动担了责罚,于是干脆放弃了罚他们,改为吓唬:“阿宁,就算驷儿不是你所伤,你置之不理,也该罚,就罚你……罚你十大板。驷儿,你来打,若是打轻了,这十板就归你了!”
“啊!父王,这……”武驷哭丧着脸,看看瘦小的阿宁,心里一时没了决断。
板子很快呈了上来,武驷接过去,下了半天决心,最后也只是闭上眼睛,轻轻地敲了两下。
“你没吃饭吗?”武夷忍住笑意,假装责备,“依孤看,这十板还是给了你吧?”
看着常娘娘欲言又止,武夷连忙补充了一句:“谁都不许求情!”
“罢了!”武驷扔了板子,心一横,说:“打我好了!省得日后传出去,别人说我丰禾国的殿下,竟然欺负一个弱女子!”
武夷招呼了身边的侍卫,很快聚集在了武驷身边。板子一下一下打在武驷身上,他却咬着牙,一声也不吭。
阿宁在旁边悄悄地数,到了最后,侍卫们其实多打了两下。阿宁看着武驷渗了血的屁股,心里有些难过。
“别看了。”画师轻轻盖住了阿宁的眼睛,悄声嘱咐她。
“师父。他会死吗?”
阿宁说这话的时候,画师感受到她的颤抖。画师想到阿宁的父母,也曾这样出现在阿宁的面前,阿宁虽没有他们的记忆,却记得死亡的含意。
“当然不会,如果你每天都会去看他。”画师安慰地说。
武夷看着画师和阿宁的小动作,说道:“画师请先回吧,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是!”画师几乎是逃得想要离开,“臣告退。”
下午刚吃完饭,阿宁扔了碗筷就要出去。
“你干什么去?”画师跟在后面喊到。
“师父,您先歇着,我要去承担责任了!”
阿宁记得画师所言,画师欣慰地笑了笑,转身进了屋。
“哎呦……哎呦……”武驷正躺在床上呻吟,屁股上的疼痛让他连饭也没顾得上吃。
武夷满脸笑意,伸手去拍武驷的屁股。
“啊!”武驷疼地跳了起来,没一会又虚弱地趴下了。
“驷儿,今日你没有为难那个女娃,我很高兴。”武夷示意太医擦药,“男儿志在四方,却以德行存名。若今日你真的打了阿宁,这十板还是会落在你身上。”
“这又有什么分别呢?”武驷不解。
“若都罚,是因你无担当,无气量。若罚你,只不过因你贪玩任性,栽赃嫁祸。”
“父王,”武驷突然把头转了个方向,“这么说,我将来会是个好人吗?”
这个问题,武夷却没有回答他。
父子两人陷入了沉默,却听窗外有悉悉索索的声音。不一会儿,窗子竟被人从外面打开了,没有人闯进来,只有一小手轻轻地放了一瓶药膏在窗台。紧接着,窗子又被关了回去,武夷还听到了落锁的声音,上前察看,窗子已经上了栓。
“这窗子怎么会从外面打开?”武夷惊奇地问。
“一定是那个小丫头!”武驷用手臂支撑着,抬起了头,“我悄悄告诉她殿内的窗子上有孔的。”
武夷伸手拿过药膏,另一手摸摸那窗台上留下的木屑,觉得自己找到了什么。
接连几天,阿宁都会悄悄送药来,药效奇佳,武驷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今天,武驷算算时间,阿宁快要来了,于是扶着屁股一走一颠地挪到了窗台。没等一会,阿宁开始开窗子了,武驷一下来了精神,抓准时机,在阿宁伸手进来时,抓住了她的手。
窗户比阿宁略高一些,所以每次送药都看不见她的脸,此时武驷拽着她,她便踮脚去看,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对上那双狭长的眼。药瓶翻倒在地上,两人却丝毫没有察觉。
八岁,他遇见她,一见面就是不断的纷争,可现在,此时此刻,武驷无比希望日后,她能留在宫中。
武驷一贯有了想法便要付诸行动,找了个机会,他就去太和殿找武夷。推门进去,武夷正在和一个老僧聊天。
老僧看了武驷一眼,目光一凌,准备起身向武夷告辞。
“她就是那个人。老衲就不久留了。”说着就离开了大殿。
经过武驷时,时间好像变慢了,武驷清楚地听到他说:“是老衲看走眼了……”
转身还要询问,那老僧已经走出很远了。
“驷儿?你来的正好,孤问你,给你添一个妹妹如何?”武夷笑着说。
“妹妹?阿宁吗?”武驷本能地问。
“你希望是这样?”
“对,我希望。而且,”武驷声音坚定了些,“好像只能是她。”
诏书很快被送到阿宁师父素弥手中,册封等诸多事宜推上日程――
“兹有女阿宁,素恭谦,知礼节,通大体,封纯文公主,赐沁竹殿。”
此时武盈和武兰已经年有十四,不出半月就要进行长公子、长公主的册封大典。可静安殿中,却不见半分喜色。
“母后,我不要这虚位,我只要张铎端!”武兰向王后哭诉到。
王后紧皱眉头,厉声说:“武兰,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的婚约定在张家最昌盛的时候,可此时他家道中落,你日后嫁过去,不仅是自降身份,更是拖了你哥哥的后腿!”
“当初说好等我年有十七,就可以嫁给张铎端,现在他家都没了,我们就要背信弃义吗?”武兰恼了,语气急躁。
王后倒是一贯的平静:“兰儿,你要学会审时度势。你父王很少来看我们,如果你无法嫁给权臣,就不会有长公主的封号,你明白吗?”
“是为了这个封号,还是为了那个人!”武兰指着在一旁嗑瓜子看热闹的武盈,“为了他,我从小就谨言慎行,他四处闯祸,我去道歉;有人对他不利,我是他的挡箭牌。你看见过我吗母后?今日,我便去求父王,定要如一次自己的意!”
说完,武兰一路小跑着去了养心殿,一进门,武夷正在批文。
“父王!儿臣请您赐婚!”武兰倔强着跪倒在地,大声说到。
王公公此时才反应过来,对武夷说:“大王,臣实在拦不住,这……”
武夷摆手让王公公退下,冲武兰说:“你要嫁给谁?”
“父王不是应过顺远候张家吗?儿臣正是来要欠了多年的婚约。”
武夷的脸色阴暗,说:“你再说一遍,你要嫁给谁?”
此时王后的凤辇姗姗来迟,王后在武兰开口之前跪在殿上,说:“大王,武兰还小,不懂儿女之事,如今有此狂言,皆是臣妾管教不周,您全当没有听到,我这就带她回去!”
说着,王后伸手去拉武兰,后者却说:“我不走!我与驸马自小一起长大,既然应了这门婚事,就绝不会有悔意!”
武夷气血涌上心头,咆哮都带上了颤音:“你若要嫁他,便不再是众人敬仰的长公主!”
武兰见状,只当是武夷送了口,她连磕三下响头,大声说:“儿臣请命年满十七就嫁出宫去,不要长公主的虚名。为此一愿,儿臣愿从朝华殿跪到养心殿,生死不论,求父王恩准!”
“好一个生死不论,既然如此,册封大典不变,你却不准前去,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留你胞弟一人,面对天下百姓!”武夷说罢,气的瘫倒在座椅上,王后见状,上前去安抚。
正巧为素弥传诏的宫人回来了,细声说道:“回大王,素弥已接旨,何时为纯文公主行册封礼?”
闻此一言,跪在殿内的武兰心生一计,她说:“父王,这纯文公主与儿臣比,如何?”
武夷看了看武兰,后者脸上是期待和紧张。武兰是他第一个女儿,不论旁人如何评说,在他眼中,她乖巧懂事。身在宫中,十有八九事不如人意,说不定远离朝堂,对她是好事。
思虑良久,终是感情大过理智,武夷说:“就封纯文公主为长公主,等她年满十五,行册封大典。至于之前定夺,无非取了武兰那部分。让宫人们早做安排吧。”
武夷站起来,走到武兰身边,看着跪到在地的武兰,说:“你要的婚书,拿去便是,是福是祸,回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