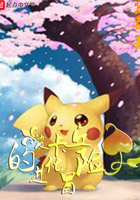当夜孙隐晚饭也不能下咽,那心里不知乱的怎么个样子。一夜翻来覆去,何曾合眼!天还没亮就起来了,呆呆的坐到天明。走到签押房,见继之也起来了,正在那里写信,见了他道:“好早呀!”
孙隐道:“一夜不曾睡着,早就起来了。大哥为什么也这么早?”
继之道:“我也替你打算一夜。你这回只剩了这一百两银子,一路做盘缠回去,总要用了点。到了家,老伯母的病,又不知怎样,一切医药之费,恐怕不够,我正在代你踌躇呢。”
孙隐道:“费心得很!这个只好等回去了再说罢。”
继之道:“这可不能。万一回去真是不够用,那可怎么样呢?我这里写着一封信,你带在身边。用不着最好,倘是要用钱时,你就拿这封信到我家去。我接我家母出来的时候,写了信托我一位同族家叔,号叫伯衡的,代我经管着一切租米。你把这信给了他,你要用多少,就向他取多少,不必客气。到你动身出来的时候,带着给我汇五千银子出来。”
孙隐道:“万一我不出来呢?”
继之道:“你怎么会不出来!你当真听令伯的话,要在家用功么?他何尝想你在家用功,他这话是另外有个道理,你自己不懂,我们旁观的是很明白的。”说罢,写完了那封信,又打上一颗小小的图书,交给孙隐。又取过一个纸包道:“这里面是三枝土参,一枝肉桂,也是人家送我的,你也带在身边,恐怕老人家要用得着。”
孙隐一一领了,收拾起来,此时他感激多谢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不知怎样才好。一会梳洗过了,吃了点心。
继之道:“我们也不用客气。此时江水浅,汉口的下水船开得早,恐怕也到得早,你先走罢。我昨夜已交代留下一只巡船送你回去,情愿摇到那里,我们等他。”于是指挥底下人,将行李搬到巡船上去。
述农也过来送行。他同继之两人,同送孙隐到巡船上面,还要送到洋船,孙隐再三辞谢。
继之道:“述农恐怕有事,请先上岸罢。我送他一程,还要谈谈。”述农所说就别去了。
继之一直送孙隐到了下关。等了半天,下水洋船到了,停了轮,巡船摇过去。孙隐上了洋船,安置好行李。这洋船一会儿就要开的,继之匆匆别去。
孙隐经过一次,知道长江船上人是最杂的,这回偏又寻不出房舱,坐在散舱里面,守着行李,寸步不敢离开。幸得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早就到了上海了,由客栈的伙伴,招呼孙隐到洋泾浜谦益栈住下。这客栈是广东人开的,栈主人叫做胡乙庚,招呼甚好。孙隐托他打听几时有船。他查了一查,说道:“要等三四天呢。”
孙隐越发心急如焚,然而也是没法的事,成日里犹如坐在针毡上一般,只得走到外面去散步消遣。
这洋泾浜各家客栈,差不多都是开在沿河一带,只有这谦益栈是开在一个巷子里面。这巷子叫做嘉记道。这嘉记道,前面对着洋泾浜,后面通到五马路的。
孙隐出得门时,便望后面踱去。刚转了个弯,忽见路旁站着一个年轻男子,手里抱一个铺盖,地下还放着一个鞋篮。旁边一个50多岁的妇人,在那里哭。孙隐不禁站住了脚,见那男子只管恶狠狠的望着那妇人,一言不发。孙隐忍不住,便问什么事。
那男子道:“我是苏州航船上的人。这个老太婆来趁船,没有船钱。他说到上海来寻她的儿子,寻着她儿子,就可以照付。我们船主人就趁了她来,叫我拿着行李,同去寻她儿子收船钱。谁知她一会又说在什么自来水厂,一会又说在什么高昌庙南铁厂,害我跟着她跑了二三十里的冤枉路,哪里有她儿子的影儿!这会又说在什么客栈,我又陪着她到这里,家家客栈都问过了,还是没有。我哪还有工夫去跟她瞎跑!此刻只要她还了我的船钱,我就还她的行李。不然,我只有拿了她的行李,到船上去交代的了。你看此刻已经两点多钟了,我中饭还没吃呢。”
孙隐听了,又触动母子之情,暗想:这妇人此刻寻儿子不着,心中不知怎样着急,我母亲此刻病在床上,盼我回去,只怕比她还急呢。便问那男子道:“船钱要多少?”
那男子道:“只要四百文就够了。”
孙隐就在身边取出四角小洋钱,交给他道:“我代他还了船钱,你还他铺盖罢。”
那男子接了小洋钱,放下铺盖。孙隐又取六角小洋钱,给那妇人道:“你也去吃顿饭。要是寻你儿子不着,还是回苏州去罢,等打听着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再来寻他不迟。”那妇人千恩万谢的受了。孙隐便不顾而去。
走到马路上逛逛,绕了个圈子,方才回栈。胡乙庚迎着道:“方才到你房里去,谁知你出去了。明晚有船呢。”
孙隐听了不胜之喜,便道:“那么费心代我写张船票罢。”
乙庚道:“可以。”说罢,让孙隐到账房里去坐。
只见他两个小儿子,在那里念书呢,孙隐随意考问了他几个字,甚觉聪明。便闲坐和乙庚谈天,说起方才那妇人的事。
乙庚道:“你给了她钱么?”
孙隐道:“只代她给了船钱。”
乙庚道:“你上当了!他那两人便是母子,故意串出这个样儿来骗钱的。下次万不要她!”
孙隐不觉呆了一呆,道:“还不要紧,他骗了去,也是拿来吃饭,我只当给了化子就是了。但是怎知他们是母子呢?”
乙庚道:“他时常在这些客栈相近的地方做这把戏,我也碰见好几次了。你们过路的人,虽懂得她的话,却辨不出她的口音。像我们在这久了,都听得出来的。若说这妇人是从苏州来寻儿子的,自然是苏州人,该是苏州口音,航船的人也是本帮、苏帮居多。他那两个人,可是一样的宁波口音,还是宁波奉化县的口音。你试去细看他,面目还有点相像呢,不是母子是什么?你说只当给了化子,他总是拿去吃饭的,可知那妇人并未十分衰颓,那男子更是强壮的时候,为什么那妇人不出来帮佣,那男子不做个小买卖,却串了出来,做这勾当!还好可怜她么?”
此时天气甚短,客栈里的饭,又格外早些,说话之间,茶房已经招呼吃饭。孙隐便到自己房里,吃过晚饭,仍然到账房里,与乙庚谈天,谈至更深,方才就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