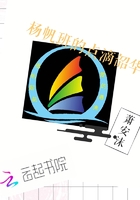当下继之对孙隐说道:“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蛋穷的吃尽当光,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却不能不将他们那旗人的历史对你讲明,你好知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各人要摆各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旗人,穷到那个样子,还要摆架子,说大话,你想这个做道台的,那家人、衣服,肯不摆出来么?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时便是家人,没客的时候,他们还同着桌儿吃饭呢。”
孙隐问道:“这又是什么缘故?”
继之道:“这有什么缘故,都是他那些什么外甥、表侄,听闻他做了官,都投奔他去做官亲;谁知他穷下来,就拿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我还听说有几家穷候补的旗人,上房里的老妈子、丫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你明白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你就都明白了。这位大帅,军功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天下太平,那些亲兵,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副将的副将,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你道为什么呢?只因这位大帅,念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好仗着这个势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还有一层:这位大帅因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喜动不喜静,到了晚上,往往悄地里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什么话,他总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他这脾气,叫人家摸着了,就借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使,只要认识了几个兵丁,嘱托他到晚上,觑着他老人家出来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江某人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使的了。你想求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李观察礼贤下士,就是为的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又是那里的什长之类的了。”孙隐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
继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下人,见继之话说的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回道:“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驾了。”
继之问道:“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
下人道:“是衣帽坐轿子来的。”
继之“哼”了一声道:“功名快丢了,他还要来晾他的红顶子!你挡驾怎么说的?”
下人道:“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回来。”
继之道:“明日到关上去,知照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驾。”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
孙隐因问道:“这又是什么故事,可好告诉我听听?”
继之笑道:“你见了我,总要我说什么故事,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
孙隐也笑道:“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人了。”
继之道:“你不要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
孙隐笑道:“你才说他的功名要快丢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可不是势利吗?”
继之道:“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这个人姓钟,叫做钟雷溪……”
孙隐抢着说道:“怎么不‘钟灵气’,要‘钟戾气’呢?”
继之道:“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孙隐央求不迭。
继之道:“他是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栈,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到了年下,他却结清帐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2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这一年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帐,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栈,是发财得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济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了,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二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把肯通融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他却‘少陪’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土栈里面,丢下了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儿都没有。银庄上的人吃一大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捉得他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地就捐上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一个二品顶戴,引见指省,来到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那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哪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合十八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
孙隐说道:“这又奇了,怎么有这半个缺起来?”
继之道:“大约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什么用处?谁还去捐他?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从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迭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那钟雷溪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使,只靠着骗拐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得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里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同他要帐。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帐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他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有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帐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并未见着他一面。没有法想,只得回到上海,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他告的是个道台,又且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说是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力,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系被骗,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面的事,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二十多万的倒帐,不消说的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同他递进去。闹的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也不曾干上,白白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得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一万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呈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藩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藩台依言问他,他却赖得个一乾二净。藩台回了制军,制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溪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督署的巡捕,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是甚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给各衙门的刑名师爷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那里请出一位给这督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钟雷溪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帐卷逃,并将两年多的往来帐目,抄了一张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信封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督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的他昨日去求藩台设法。这位藩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藩台还说得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藩台去代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么?所以不要会他。兄弟,你如何说我势利呢?”
孙隐笑道:“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着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个怎么样结果呢?”
继之道:“官场中的事,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罢。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