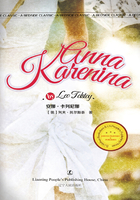卫韫先让她在自己屋里睡了,而她自己却彻底失眠了,她看着睡在自己身旁的女子,轻眉淡唇,恰是正好的年华,和她的成十九一样,又傻又呆的……
因为习剑的原因,她自小就没有脱衣睡觉的习惯,看着她睡熟了就起身想到外面去坐坐,可刚打开门就看到正要敲门的棠棣。
卫韫问:“怎么了吗?”
棠棣有些尴尬:“没没没,阿娘就是…想来看看你……”
“看我?”卫韫疑问道,这大半夜的?
她手忙脚乱的想要解释什么,卫韫可能也是刚才的事情,见她莫名其妙的就有些烦躁了。
棠棣看了一眼屋里还正在睡梦中的望舒,说道:“阿…诏,我们出来说吧……”
她对卫韫总是有种讨好的意味在里面,想来也是因为对卫韫的自小生而未养的内疚,满心愧疚就变成了极力“讨好”,其实她大可不必如此。
她们坐于亭苑里,棠棣先开了口:“我刚才起身,听到望舒说……,她知道了你不是男儿身?”
“你听到了?”卫韫启声,刚才望舒说话时确实是有点大声,所以她也忙是把人拉进屋里,没想到还是被人听到了。
棠棣有些为难地说道:“你阿爹哪里是怎么跟你说的?我本来是想,她若是不知道就随她在这鄯阐城里待着,不想却……”
“如果她不知道我是女儿身,就可以留她一命……”
她和望舒一路上走来,时间不长不短,淡不上什么难分难舍的,但是突然就要那样,她确实是有些不舍。
“那你呢?”棠棣问道。
过了许久她才说道:“我不知道……”
夜色冷落,桌台上的灯火忽明忽暗。
棠棣开口道:“你的身份是必须要保密的,宁古!”
卫韫从自己女儿“变成”儿子,身份替换她总归是有些膈应着,她也不知道怎么叫卫韫才好,想这夜里也无人才叫了“宁古”,而且看卫韫从书房出来时的表情,棠棣就知道卫韫心里肯定是有些不开心。
卫韫也看出她的顾虑,言语里带着宽慰说:“叫阿诏吧,叫多了以后自然就习惯了,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望舒的事情不是小事儿,你要好好考虑清楚,这鄯阐城里处处都要小心。”
“……”
卫韫也不是傻子,望舒的身份不明,日后会不会对她有所影响也是未知的,她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每件事都对她很重要,她不能冒一点任何形式的险。
第二日,棠棣让阿蛮送了好几件衣物到卫韫哪里去,她要在这里待着就不能再穿自己的那些中原式的衣服了,望舒也换了一身,看着样子还算不错,她看上去很是开心,还给卫韫转了转裙子。
不一会儿就有人闯了进来,卫韫听到声音连忙出去查看,是个年纪尚轻的男子,看着比卫韫还小一些,面目丑陋,身形清瘦,手里只有一把弯刀,狂傲又气势汹汹的像一群野兽。
身后还跟着几个带刀的兵吏,走到她们前面,阴阴地道:“诏小殿下?来人,把这两个人抓了!”
他要抓的自然是指卫韫和望舒,卫韫心下觉得情势不妙,抽出了背后的剑,沉静却不语的与他们对质着。
卫韫拿着剑却一脸的不屑,不以为意的冷笑了一声,一旁的阿蛮看形势不好便匆忙跑去叫棠棣。
棠棣匆匆赶来,刀剑相向,厉声吼道:“曲部,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叫曲部的见到棠棣也没有要收敛的意思,假意为臣,出言不逊,一言一语都是嘲讽:“诏后在紧张什么?莫不是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呵!我听人说宫府中来了两位贵客,其中还有诏殿下,曲部见识浅薄,倒是想见识见识这死人,又是怎么生还过来了的!”
“来人,直接抓了!”
棠棣怒不可遏,阻到卫韫身前:“你敢!不过一个小小的宫府副使,谁给你的权利?”
曲部轻蔑的说道:“曲部自小就跟着祭司,我要带人来,祭司难道还会不知道吗?诏后是想干什么!!”
“况且,这两个人来历不明,靠着一张与诏殿下形似类同的脸皮,就进到宫府里来,诏后可不要轻易就被人给蒙蔽了,还是擦亮些眼睛比较好!”
卫韫蔑视笑傲道:“你说什么屁话呢!爷爷我是谁自己还不知道吗?倒是你这个自持了不起的宫城副使,你莫非觉得你这区区几个兵吏就能与我相抗了?狗仗人势、欺人妄上的后果,你死前是不是得想一想!”
曲部不堪受其侮辱,震怒道:“少废话!给我抓起来!”
兵吏齐拔刀,卫韫两步并一步,脚履轻匆,刀光剑影,兵韧相交,寡一敌众,卫韫丝毫不以为意,微弱几剑,几人便是躺地呻吟。
曲部老羞成怒,脸面上已经挂不住了,放了话道:“这是我培养多年的亲信死士,你竟胆大伤了他们?”
卫韫只轻轻一笑,眼里尽是对眼前这人的不屑,开口说道:“伤?抱歉啊,我不仅伤了,而且过不了多久,他们都会受我剑上之毒,个个暴毙而死!”
他一惊:“你剑韧上藏有毒?”
“你觉得呢?”
“……”
“什么事儿惹得这么多人都杵在这里啊?”是身后传来的声音,众人齐齐看过去。
诏王卫景韬在曲部几人后面缓缓走来,棠棣带着卫韫一行人皆是忙问了礼,除了曲部那几人无所畏惧的依旧挺直腰板着。
卫景韬身边还有一个年岁稍高的人,看着有些女男不分,满头银发都凌乱的披散着,看不清隐藏着的脸,勾腰驼背,手里还拿杵着一根手杖。
他们的身后也是一群配刀的兵吏。
“主上,您怎么看?”她慢慢地开口道,言语里平淡漠然。
听声音原来是个女的!
卫景韬侧目一视,未语。
曲部跑了上去,也没有先向卫景韬问礼,而是带着刚才从卫韫那里受的气,委屈满满地对那个女人说道:“祭司大人,这女子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竟敢冒充诏殿下,奴将叫人将其捉拿,可诏后却百般阻挠,她还被奴将多年来培养着的几名死士通通下了毒,怕是救不活我这些兄弟了!”
祭司看了一眼前面的卫韫,眼神里看不出任何一种情绪,道:“他是南诏的诏小殿下,你区区几个死士算得了什么,死了就死了!诏小殿下如若要你死,你也必须尊从,不是吗?主上您说呢?”
她没有看卫景韬,只是自顾自的说了一番,卫景韬缓缓开口道:“祭司说的没错,曲部是祭司多年来的爱奴,受了委屈自然不能就此作罢,何况是我们阿诏先伤了人,让曲部丧失了奋命的人士……”
祭司又言:“主上多虑了,这南诏是主上的南诏,主上才是南诏真正的主人,没有人能违背。”
“这南诏是本王的南诏,也是祭司的南诏。”
“鄙臣为主之臣,主上这话可就是抬举奴才了。”
“祭司可是谦逊了。”
两个人针锋相对,表面上却又平静无事,无人敢言语。
空气中弥漫着不死不休的战火气,卫景韬突然开口说道:“卫诏!狂傲气慢,不服礼道,乱伤慌害……”
“主上,未免对诏小殿下苛刻了一些!”她这话明显没有希望卫景韬轻惩卫韫的意思,随口而出,其中何意不难知道。
卫景韬没有对她多说什么,而是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说道:
“……将其禁囚于羁押所,面壁思其过,未得我令,不得放出!”
卫韫从卫景韬脸上没有看到一丝他对自己的袒护,像是一个毫无关系的人正事不关己的对自己进行无情的宣判,她却不能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