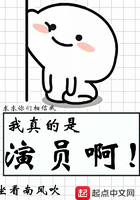我的哥哥们
奶奶被叔父接去后,我们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小家更加困难、动荡了。父亲多在外,少在家,为了一家人糊口跑脚不停,大哥这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家的主男兼主妇。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挑起这样的家庭重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是,生活的磨难使得大哥成熟了,懂事了,他很操心,也很疼爱弟弟妹妹。家里的活儿他几乎全包揽了,拾柴捞草、把灰煨炕、烧火做饭等等,都是他一人干。他从不厌烦,也从不打骂我和妹妹。我们的家境基本上是有一天吃一天,有一顿吃一顿,所以大哥做饭也很简单,一般都是炒麦子吃——灶火内抓一把草一烧,铁锅烧热了,往里倒一碗麦子,噼里啪啦响一会儿就熟了,然后每人分一些,当然每次都会给我多分一两把,特意照顾。这就是我们的家常饭。晚上,我们兄妹三人一同蜷缩在一个炕上,眼看着天上的星星,耳听着窗外的风声,盼望着早些天明。尽管大哥每天都操心把炕煨得很热,但由于破屋四面通风,还是很冻人的。我记得我们好像没有被子,我常常被大哥搂在怀里,两人合盖一件破山羊皮褂,小妹一个人盖一件破棉袄。我经常感觉到,大哥的手在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身子,生怕我着了凉。大哥一边从头至脚地抚摸着我,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尕兄弟呦,我们啥时才能活出个人样儿呢?”这件事、这句话,一直令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是我每每遇苦却从不放松的原因。
大哥除操劳家务、照顾我和妹妹外,还要料理我们旱沙地里的庄稼,一是要除草,二是怕被别人家的牲口糟蹋。就这样,他既忙里,又忙外,还要忙里抽闲给亲戚邻居家帮忙。他常常帮别人家推磨、碾米,顺便也捎带给我们磨点面、碾点米。由于大哥懂道理,干活有眼色、麻利,而且肯卖力,街坊友邻们也都喜欢他帮忙,有时有些好心人也会给他一些微薄的报酬。由此,大哥赢得了好名声,大家都夸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前面说了,奶奶去了叔父家,按说是应该享些清福了,可是她老人家积劳成疾、积虑成患,自身的疾病疼痛,儿孙们无法代替。后来,她疾病缠身已是卧床不起了,水火也已难送。大哥见状,就主动去扶抬,每天都背新沙换旧沙给她铺垫,让奶奶尽量干净些,好闻一些,这样一直坚持把奶奶送终。大哥是我们兄弟几个中唯一给奶奶尽了孝道的人,所以,我们永远敬重大哥。
就这样,大哥忙里忙外,成了我们家的大忙人。他多的时间不在家,我和妹妹也就成了无人管教的自由人了。有个好心的邻居李三婶,她很喜欢妹妹,经常给妹妹洗脸、捉虱子,还给吃给喝。后来,她干脆就让妹妹住在了她家,实际上她是看妹妹可怜,想好心善意地收养妹妹。她曾向我父亲当面提出把妹妹给她收养,父亲婉言拒绝了:“我已经把一个小女儿给别人了,如果再把这个女儿送了人,死后没法向老伴交代。就请帮帮忙吧,再苦再累我也得把这个女儿养大成人。”
父亲常年在外,大哥又忙忙碌碌,没空看管我,我就成了天不管地不收的流浪儿了。我整天和邻居家的郝蒙头、石三娃、王三娃、吴六三、张六娃等一大帮娃娃淘气玩耍,掏麻雀儿、挖蜂窝儿、打沙蛇鼠等等,整天玩着不回家。肚子玩饿了,走在谁家都看着可怜,好心的人们常常给上半碗剩饭,或者抓给一两把炒面。他们不仅给我吃喝,有时晚上也收留我住下。饥是一顿,饱也是一顿。有时受人欺辱,相互打架,脸肿鼻青的事也常有发生。就这样,我玩疯了、耍累了,住在别人家,晚上不回家,常常害得大哥满村子找我。大哥找着我,也从不打骂我,只是兄弟两人贴胸相抱,碰头相哭。这样的情景,犹如电影里的镜头一样,常常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后来,看到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时,我不禁泪流满面——这不就是我过去的生活吗!就这样,玩着、耍着、挣扎着,吃着百家饭,我的小命算是活下来了。在我的记忆中,罗家尕表婶、付家三舅母、张家大叔大婶、李家婶婶,还有好多不能道出姓名的大叔大妈、婶婶们,他们都乐善好施,常常给我吃喝,他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
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几个哥哥就是最好的验证。也许,这也是得了父母祖上的遗传。大哥在我们家里已是顶天立地,领给别人家的二哥和三哥又是怎么样呢?
二哥被领到尕爷家后,先是放驴打杂,长到十一二岁以后,就真正是男儿不吃十年闲饭了,他赶着3个小毛驴开始跑脚出远门了。每次临出门前,尕爷都会给联帮跑脚的可靠人叮咛嘱咐,甚至诚心地拜托,让他们一路上费些心思担待照料些。二哥太小,实在让他不忍心,也不放心。可是二哥在联帮合伙的跑脚队伍中却是人人喜欢,因为二哥精明、勤快,从不拖大家的后腿,也不给大家增添麻烦。大伙儿不但不觉得他是累赘,而且觉得联帮伙里还少不了这么个勤快好强的娃娃。在他们跑脚的路上,二哥除了在给牲口搭驮子、卸驮子时力量不足,不能独自完成而外,其余活儿如喂牲口、饮水、烧火做饭等等,样样他都跑在前面。凡是他能干的活儿,他就抢在前面不让大人们干。同帮合伙的人们都同声赞扬二哥:“娃娃勤,爱死人。朱尕尕(二哥的小名)确实是个精灵虫。”二哥出远门跑了一趟后,联帮的人们谁出门都喜欢联络二哥一道去。小小年纪的二哥不仅给联帮跑脚的人们留下了好印象,而且给尕爷家庭经济的改变也撑起了半边天。他每一趟跑脚回来,都能给尕爷把账目交代得清清楚楚,由此尕爷也特别器重二哥了。
三哥的性格更倔强,也更有志气。三哥到李家后,也是勤快有余,更像个男子汉。他十一二岁就开始驾着大牲口——骡子给李家犁地了,不论是犁水地、漫水地,或者是耖沙地,虽然常常是人小牲口高、犁把高,但他够不着犁把和耧柄时,就从半截腰扶着去犁。狡猾的骡子欺负他是小孩,往往不上趟,东拐西拉,不听吆喝和使唤。遇见这种情况,三哥就会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犁压得深深地入进土里,然后牵着骡子头用鞭杆子猛打,直到把牲口驯服了才停。如此这般,狡猾的骡子才成为他驯服的工具,他也才得以顺利地干好农活。三哥是个有心计、有志气的娃娃,干啥农活都要干好。他人虽小,但干活时却总是不服气大人,大人干多少,他也要干多少,从不服输。由此,李爸一家人都非常喜欢三哥,尽量给他吃好、穿好,而且劳动报酬也在逐年增加。据说,李爸还曾有意把三哥招为女婿,可是,年轻气盛又好强的三哥觉得自己能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了,就婉言谢绝了李爸的好意,辞退了李家的活儿。他听说背煤这个活计挣的钱能养家,就跑到煤山上跟着罗家表叔背煤去了。罗家表叔是挖煤的能手,三哥吃苦又利索,他们搭成一对,表叔挖,三哥背,他们这个班子出的煤最多。好心的表叔也没有把三哥当娃娃看待,而是公平地分给三哥应拿的份子。三哥的背煤,使我们的家境渐渐有所改变,家里开始能常常吃到黄米,也可以吃到一点白面了,有时还能吃到清油和黄豆以及山药蛋之类的奢侈品,甚至买来或者用煤换来一些土布匹等等,我和妹妹也能做件新衣服穿了。可以说,三哥的艰辛背煤,使我们这个穷困潦倒之家又有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