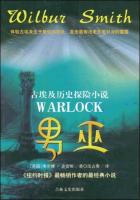吃完馄饨他殷勤地要去走廊水龙头下涮盆子,她说不必了,晚上一道涮。她把盆子收拾好,又补了一句话:“若让别人看见,又不知会说些什么。”
他欲言又止,心情有些复杂。但他理解她的顾忌和谨慎。她倒了一瓶开水,拧了一把毛巾让他揩脸。毛巾的温香让他陶醉,一股热热的东西从心中淌了出来。他揩过脸后,她又用同一条毛巾洗脸,这使他心里格外舒服,这仿佛是一种象征,一种暗示,一种接纳。她接着细心地往脸上抹雅霜。那种清雅的香气仿佛为她所独有,仿佛是她本身的气息调制而成,它笼罩了他,充实了他,渗透了他,使他有腾云驾雾之感。而当她揉抹完面颊,双手将头发慢慢往后拢,捂住了耳朵,只露一张脸在外的时候,他心里电光一闪,立即认出了她。
“我知道在哪里见过你了!”他惊喜地叫道。
“哪里?”她问。
“青山铺!那天我坐在石拱桥上,你挑着一担红薯从我身边过!你还用蓝印花头巾包着头!”他说。
“你看错了。”她急剧地眨眨眼,否认道,“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什么青山铺也没有什么蓝头巾!”
说完,她就不理睬他了,使劲地掸着床单。她的眉头微微蹙起,洁白的细牙咬住了下唇,眼波里有一缕忧伤在流动。他想,也许触着了她心里的隐疼。她显得心烦意乱,东看看,西动动,半天才回到他对面坐下,垂着头,看也不看他。
她烦他了吗?他心里很不安,不知所措地操起火钳,拨了拨烘笼里的木炭。红红的火光立即映上了她的脸,如同擦了一层胭脂。他不敢打破这深厚的沉默,只是悄悄地呼吸她身上的温馨气息。她瞥了他一眼,头垂得更低了,他只能看到她乌黑的头发和半个圆润的额头。她惶悚的眼神久久地留在他脑子里。她显得那么无助。她在期待什么。他该怎么办?他的头皮绷紧了,口腔里分泌出一些苦涩的液体。
沉默太长了。很多东西都在沉默中酝酿着。沉默中,一种渴念春笋破土般钻出了他的心,在他体内迅速生长,他快抵挡不住了。与此同时,皮肤表面冷嗖嗖的,畏惧的壳正在形成。是时候了,他鼓励自己把那几个琢磨过好多遍的字眼吐出去。然而干涩的嘴巴刚张开,喉头一阵痉挛,封锁了语言的道路。他因为冲动,也因为压抑而喘息不止。喘息声惊扰了她,她抬头用眼神问他,你怎么了?他狂妄地直视她的脸,恨不得将一腔激情全倾泻在这张脸上。他浑身微颤,手指鸡爪般僵硬地张开又收拢,欲望在体内沸腾,冲撞着他的青春之躯,而那层羞怯的壳却拼命箍紧他的身体,抑制他的冲动。
“你冷吧?”她问他。
他不作答,苍白的脸浮出痛苦挣扎的神情,眼睛里布上了血丝。他好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气息奄奄了。这时他看见桌上有本稿纸,还有一支铅笔。他气喘吁吁地抓住了那支笔,再向稿纸伸过去——他听见笔尖喀嚓一声戳破了一层壳——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一行字:我喜欢你,希望和你交朋友。
他胀红着脸把纸推到她面前。
她看了那行字,眼睫毛忽闪了两下,一抹红晕从两颊洇出。过了好一会,她才说:
“我……谢谢你的好意。”
“……我是真心诚意的。”他从嗓子里挤出一句话。
她点点头:“我相信。”
“那,你答应了?”他急切地问。
“我们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她说。
“我说的不是一般意义的朋友。”他说。
她不言语。风从窗口漫过来,顺着他的背流泻,他不由打个寒噤。这时他清楚地看见了她拒绝的表示。她的头轻轻地摇了摇。
他感到毛骨悚然,缩紧了心,不无怨忿地道:“当然,我只是个工人,而且是个倒班的操作工,毫无社会地位可言;每天跟机器打交道,一身油污,两手老茧……”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小声地说。
“自然,我的相貌也配不上你,我长得丑,只能给你当陪衬人。”说着他一扭头,从桌上的圆镜里看见一张半是绝望半是愤懑的脸,单眼皮下的眼眸射出刺人的光芒。这叫他吃了一惊,这个人是谁?
“不,你并不丑,真的。”似乎为了证实她说的真心话,她凝视着他。
“那你为什么摇头?”他问。
“你了解我吗?”她说,“你一点不了解我,就想和我交朋友……”
他冲动地打断她:“我晓得你在个人问题上有过挫折,但那又算得了什么?我非常同情你。”
“我不需要同情!”她断然说。
“我、我不止是同情呵!”他结结巴巴,颈子上的青筋都凸了起来。
她想着什么,须臾,问:“你听别人说过我什么吧?”
“我其实也没听说过更多的什么。”
“告诉你吧,在爱情问题上,我跌过跤,不然也不会调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来,”她语调平缓,透着一股哀伤,“我的心受到很大创伤,现在,伤口总算结疤了,我不想再去触动它。”
“庄姝!”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她的名字,“我保证永远不去触动它!我愿意平复你的创疼,和和一起创造新的生活!”
她苦笑道:“我现在只想遗忘,再也不奢望什么新生活。我的心已经死了。”
“我要让它复活!”他激情难抑。
她又摇了摇头。
“不,我要,我要!”他露出了孩子气。
“危思,你何必要找我呢?你虽然只是个工人,但你勤奋,有才华,以后会有出息的。天下的好姑娘有的是!让我独自走自己的路吧,我已经孤独惯了。”
她凄婉的神情使他的心阵阵隐疼,特别是泪光闪闪的黑眸,令他不忍目睹,他尽力克制着抚慰她的渴望,信誓旦旦地:“不,我一定要让你摆脱孤独,一定让你终身幸福!”
“我请你离开我!总有一天,你会嫌弃我的,我的感情早被别人玷污了,我不想再一次绝望……”
“我的心是真诚的,我的感情是纯洁的!我爱你都来不及呢,怎么会嫌弃你呢?庄姝,我……”他向她伸出两只手去。
“不!”她叫一声,连退两步,坐到床上。
他的手凝固在空中,半晌才木木地落下。他的视线模糊了,她那穿桔红色平绒棉袄的身子变成一团捉摸不透的云。一阵耳鸣过后,他听见了二十公里外传来的机器轰鸣声,那些熟悉的噪音似在传达一种嘲笑。他想看看她的神态,是一种决绝,还是蕴含一线希望,但那被热情烧灼过度的眼睛,已举不起他的目光了。他颓丧地垂下眼帘。烘笼里的炭火奄奄一息,余下一缕袅绕的热气在和冷风作最后的周旋。屋子里光线黯淡下来,他该去赶最后一趟回厂的公共汽车了。
他白着脸艰难地站起来。他听见自己的脊椎如同没上润滑油的齿轮喀喀作响。她垂着头,脸上闪着神秘莫测的幽光。他撕下那一页他的表白,揉成团扔进烘笼里。纸团立即冒出一股黑烟。他想,这就是命运,他想,这就是结果,他想,这就是一首诗的最后一行,他想,这也就是一次情感的葬礼。他嘴角微微一翘,绽出一抹自嘲的浅笑。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呆在这里,这是别人的房间,别人的壳。他像挪动一座山一样将自己向门边移去。
“危思!”
这呼唤犹如一朵蓝色焊花突然爆绽在夜空,璀灿无比。他停住脚步,心惊肉跳地转过身来。
她坐在那里,目光灼灼,神情哀哀:“你真像你说的那样吗?”
他沉重地点点头。
“如果你真像你说的那样,而且能够暂时保密,那么我答应你……这事公开早了不好。”她说。
他恍若被人击了一掌:“真的?”
“嗯。”她慎重地点点头。
他傻了,鹄立良久。
“来呀。”她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黑暗的脑际忽然裂开一条缝,缝里金光四射,映得他眼前一片辉煌。他踉跄着跨过去,双手紧握住她的的那只右手。她的手芳香四溢,温热柔软,像一只小鸽子安静地栖息在他的掌心。握了一会,他将它贴在自己面颊上,然后又让它捂住自己的口鼻,他贪婪地呼吸它的气息。再下来他无比珍爱而又小心翼翼地抚摸它,从小指到拇指,从手心到手背,从指甲到指关节处的肉窝窝,不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后来他再次握紧它时,它那一端忽然传来一股力,于是他的手积极响应,猛地一拉,她那桔红色的身子便朝他的怀抱飞来。他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她。她的棉袄松软之极,他全身心地陷了进去。他心醉神迷,把头埋在她的脖子里,如同一匹跋涉沙漠的骆驼渴饮甘泉,吮吸着她身体的气息。他的每一个呼吸里都饱含着她,她一缕一缕地吸入了他的内脏和血脉,他和她完全溶化在了一起……
从眩晕中清醒时光线更暗了,暮色在窗帘上飘动。他走到窗口,只见最后一班车正向站牌徐徐驶来。“我必须走了。”他无限遗憾地说。她则通情达理地点点头。“属于我们的岁月还很多!”他诗意地说,诗意地道别,悄悄而迅速地离开了她的房子。
他跳上公共汽车,从车窗里伸出头去。她红红的笑脸镶在三楼的窗口,被果绿色窗帘拥簇着,恰似一朵迎风摇曳的玫瑰。玫瑰在向他招手,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在玫瑰的上方,铺展着有生以来最广袤最纯净的天空。
危思做巡回检查时,看见分析室的冯彤彤站在低压泵房门口,一手拿个取样瓶,一手捂着口鼻,畏缩不前的样子。这两天低压泵房泄漏严重,氨味很浓,刺激得人眼泪双流。特别是脖颈、腋窝和大腿根这些隐秘潮润处,氨分子和水分子发生化学反应,针刺一般疼。分析室每个小时都要来取一次样,真够为难她们的了。
危思过去说:“冯彤彤,不敢冲锋陷阵了?”
冯彤彤说:“危师傅你还笑我,怎么一点骑士风度都没有呵?”
“行,我就当一回骑士吧!”
危思到值班室拿来防毒面具戴上,接过取样瓶,像个水鬼似的,冲入低压泵房。由于氨气浓度很高,防毒面具上的过滤罐起不了大的作用,吸入的空气仍很呛人。他只好憋着气,忍受着裆部的点点刺疼,取了样,赶紧冲出来。
冯彤彤接过瓶子,感谢不迭地走了,边走边回头看他。
危思取下防毒面具,到露天走道上去透气。班长黄秉良过来,与他聊起了天。
“危思,你看冯彤彤这人怎么样?”
“嗯,这姑娘身体挺结实,挺棒的。”
“特别是两条腿,还有胸脯,都挺那个。”
“嘿,外国人有个词那个。”
“什么词?”黄秉良问。
“叫作性感。”他说。
“对,就这么回事。”
“外国女人你说她性感她会很高兴。”
“你敢对冯彤彤说吗?”
“我可不想挨一扳手。不过冯彤彤这人不错,蛮爽快蛮直率的,穿上条西装裙好象还有点风度。”危思说。
“你对她有好感?”
“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