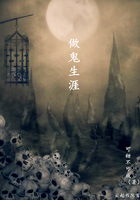思源怒不可遏,扬手就是一耳光,直把玉茜打愣了,思源也愣了一下,玉茜咬牙道:“好,何思源,你真做的出来。咱们两个离婚吧。”
思源也怒道:“离婚就离婚,像你这样恶毒的女人,随时会捅丈夫一刀,我也不敢跟你过下去了。”说罢扬长而去。
玉茜本有肝郁之症,这时更觉胸腋间胀痛难忍,伏在床上细想近来种种,又悲又怒,又痛又恨,一时气血翻涌,觉得万不能让那一对狗男女就此畅心快意,一时心灰志冷,又觉得这样薄情寡义的丈夫,何必希罕于他。阿盈煎好了药端来,玉茜一见,就想起思源那日掀翻药碗的情景,哪里吃得下。既不吃药,又难消气,病情便一日日加重起来。
思源住在晓莺处,只尽着手头的钱花,一心等着交易所分红,这天正陪着晓莺买东西,却见何大贵寻来了。
他擦着汗道:“三少爷,叫人好找。”
思源哼一声道:“找我做什么?”
何大贵道:“三少奶奶病了,太太叫您赶快回去。”
思源怔了怔道;“叫我回去做什么,我又不是大夫。”
何大贵道:“太太吩咐的,小的怎么知道?”
思源看了晓莺一眼,晓莺低了头,不与他眼光相对。思源咳了一声,将晓莺拉在一边,低声道:“我不是为了她回去,只是母亲发了话,不能不走这一趟。”
晓莺低声道:“我还能拦着你不让你回家么,只是怕你这一去,就不回来了。”
思源急道:“怎么可能呢,我就算不顾你,还能不顾孩子么?”晓莺这才不说话了。
思源回到家后,挨了何太太一顿责骂,垂着头出来,也不回房,径自去找思澜借钱,思澜拿了个折子出来,也不过几百块钱,思源笑了笑道:“你也够穷的了,总算聊胜于无。”
思澜道:“魏七哥找你,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只怕有急事。”
思源急忙去回电话,原来是交易所出了问题,有买方不缴证据金,并且用空头支票来代替现金,对方是很有背景的人,魏占峰自觉独力难支,让思源尽快过去帮他。思源不肯耽搁,匆匆去跟晓莺交代了几句,便赶去下关车站。
在上海呆了二十多天,才处理妥贴,回来时手头已有了余款,兴冲冲赶到花雨楼,不料人去楼空,哪里还有晓莺的踪影?不止晓莺,竟连杨四姐都不知去向了。思源惊骇之下,如堕雾中,阿宝出局尚未回来,娘姨大姐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只得折回家中去问思澜,偏偏思澜这日些子有时间就在家逗女儿,好久没同朋友一处喝酒打牌,也不知道原委。他见思源神色有异,怕他冲动出事,便陪着他一起来找施可久。
施可久看了思源一眼,缓缓道:“大凡客人热了一个姑娘,总想着要讨,其实讨到手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思源发急道:“你跟我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我是问你晓莺,不,云枝到哪里去了?”
施可久道:“听说是嫁了人,前几天摆的酒。杨四姐赚足了,也回乡下养老了。”
思源顿足道:“胡说,她怀着我的孩子,还会去嫁谁?”
施可久笑叹道:“傻哥儿,你怎么还不明白,像她们那种人,有那么容易怀孕么?”
思源顿时呆了,盯着施可久道:“你,你是说她骗我。”
施可久拍拍他的肩膀道:“老三,想开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思源退了两步,欲待不信,又不能不信,接连几天细细打听,才知道晓莺有个安徽客人,家住北京,是从前在八大胡同群艳班认识的,上次自己去常州时,正值那人到南边来做生意,两人重又遇上了,那人自从妻子殁后,便有讨晓莺的意思。思源只想不通她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好手段,把自己完全蒙在鼓里。
思源、思澜和施可久在酒馆喝酒,说起这件事,越想越怒,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经过钓鱼巷时,脚下一顿,又折向花雨楼,思澜和施可久拦不住,眼见着他冲了进去。思源借着酒意,大呼晓莺的名字,拿起东西就砸,外场相帮也有素日相识的,或拦或抱,都被他踢打开。忽听一个声音清脆脆道:“三少爷,这是何必呢。”
思源住了手,见一个女郎俏生生站在面前,正是阿宝,点头道:“好,你们都是一路的,拿我当寿头码子。”阿宝挥手让人都退出去,亲自给思源三人斟茶。
思源冷笑道:“少来这假惺惺的。”
思澜道:“三哥,不干六千金的事。”
施可久也道:“是啊,老三,你可别乱迁怒。”
阿宝微笑道:“我明白三少爷是气五阿姐嫁了别人,可你知道,她为什么嫁别人吗?”
思源冷笑道:“我哪知道,大概是我服侍得不周到吧。”
阿宝道:“令尊那日派了贵管家来——”
思源惊道:“你说什么?”说着看了思澜一眼。
思澜忙道:“我不知道。”
阿宝笑道:“我想也是瞒着四少爷的。贵管家说,何家是不会让五阿姐进门的,就是有孕,也是去母留子。又说有她在一日,令尊一日不会让三少爷管事。五阿姐哭了一晚上,逼于无奈,才允了别人的婚事。”
思源将信相疑,半晌道:“那骗我有孕又是怎么说?”
阿宝微微笑道:“不骗三少爷有孕,三少爷还在太太跟前做好丈夫呢。我说前面的话,是不愿没了五阿姐的心意,若依我看,她可没有什么对不起三少爷你的。”
思源嘿嘿一笑,“她没有对不起我,我现在人财两空,倒成了对不起她了。”
阿宝笑道:“我们掉进火坑,都是娘老子卖的。可五阿姐是为了什么,三少爷心里最清楚,始乱终弃,说句不好听的,有今天是你三少爷的报应,你害了她一辈子,只花了万把块钱,难道还很冤枉吗?”
思澜想不到阿宝娇娇柔柔的模样,言辞竟这样锋利,却听思源啜嚅道:“就是因为我从前错了,才想补偿……”
阿宝笑道:“难道三少爷的补偿,就是让五阿姐当你一辈子的外室,待到人老珠黄,再被抛弃一次。”
思源怒道:“胡说八道,我怎么会抛弃她呢。”
阿宝脸色不变,依然从容含笑道:“我哪里知道会不会,只是吃过亏的人,总要记着点教训。”
思源恨声道:“难道那个人,就会守着她一生不贰么?”
阿宝微笑道:“三少爷,世上事要都这样穷究起来,可就没法活了。南京这个地方,伤她太过,她想离开,也无可厚非吧。”
施可久劝道:“你负她,她负你,两下里就算扯平,今生有缘无份,老三,你也就别再钻牛角尖了。”思澜暗叹一口气,想当初晓莺千方百计地要回南京,现在却毫不留恋地离开,足见人生的讽刺。只盼她此后平平顺顺,安度一生,再不要受那些磨难了。
思源望着花雨楼的一桌一椅,一廊一柱,想着那日与思澜同来,听晓莺与阿宝对唱“秋江”,我怎肯转眼负盟言,我怎肯忘却些灯边枕边?那是何等的温柔旖旎,妙常与潘生秋江唱别,尚有重聚之时,自己和晓莺,大概此生再无相见之期了。少年相恋,街头巧逢,回想起往昔的柔情蜜意,真如做了一场梦,如今却是该醒的时候了。
思源一言不发,只坐在椅上发呆,思澜想唤他,阿宝轻轻扯了他袖子一下,思澜望向她,阿宝低声道:“四少爷,请移步。”
思澜跟阿宝上了楼,见她进了房间,摆弄着妆台上的香水瓶道:“五阿姐还留下几样东西,你说我要不要交给三少爷?”
思澜不料她引自己上楼,就是为了问这件事,心想若是伊人香消玉殒,留一两件遗物倒也可寄哀思,只是现在蝉过别枝,留着人家妻子的东西,算是怎么回事呢。阿宝是个聪明人,何以问出这样不通的话来,笑了笑道:“三哥想是愿意的,只是物是人非,让他情何以堪呢。”
阿宝点头道:“说的也是。”起身斟了一盏茶,双手递给思澜道:“刚才太无礼了,还请四少爷不要见怪。”
她这样说,思澜若不接这杯茶,倒像真的见怪似的,只好伸手去接,葱管似的十指,软缎拂香的衣袖,一弯流水青丝,盈盈欲语双眸,思澜敛住心神,啜一口茶,口鼻间却不似茶香似脂香,他一口饮尽,起身笑道:“我要下去了,否则老施非闯进来不可。”阿宝笑而不言,只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觑着思澜,思澜也是一笑,推门而出。
阿宝随着思澜一起下楼,这时思源伏在椅上半睡半醒,施可久却对着他们眨了眨眼,思澜心知他想多了,但也不便解释,同施可久一起扶思源到街上,雇了车回家。他本打算将思源掺回卧房睡,无奈玉茜已睡了,只好安顿在书房。
思澜回房后,跟迎春说起思源晓莺之事,迎春也唏嘘。
思澜感慨道:“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两个那次去晓莺家,晓莺说起三哥的样子,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一回竟然是晓莺先抛下三哥。”
迎春道:“也许她怕自己再被抛下,所以这一回,她先抛下他。”
思澜拥住迎春道:“还好我们是在一起的,谁也不会抛下谁。”迎春埋首在他的怀里,点了点头。
思澜一觉天明,床上已不见迎春,因玉茜生病,家中诸事暂且交给秀贞和迎春。其时江苏各处都在赈灾,何家也不甘后人,开了几处粥棚施粥,迎春不免要帮着秀贞提点诸事。
这天从早至晚方散,经过花园时,正见珠儿和一个妇人拉拉扯扯,秀贞问道:“珠儿,怎么回事?”
珠儿看了一眼迎春,向秀贞道:“大少奶奶,你替我做主,我不出去。”
秀贞笑道:“你闹什么脾气?”转脸向那妇人道:“是不是聘礼不合意?”
那妇人正是珠儿的母亲,陪笑道:“都是自己家人,哪有那么多可挑剔的,也不知她别扭什么。”
珠儿高声道:“我嫌他没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