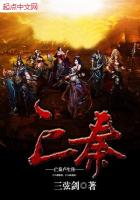当夜,宋军四壁各自清点伤亡人数,辛亢宗醉醺醺走上城墙,又哭又笑,疯疯癫癫道:“完了,都完了,五帝以来华夏,汉唐以来中原,都完了,没救了……”
守城军民见辛亢宗不仅不敢守城,反散布灭国消息,群情激愤,立时涌上,竟将辛亢宗殴死。
李若水听说辛亢宗死前念叨“五帝以来华夏,汉唐以来中原”,也忍不住痛哭流涕。他虽不是武将,亦看出城中军民绝难抵挡金军。当夜,李若水求见郭京,哭道:“今势急矣,求仙人大展神威,救黎民于水火!”
郭京心下惊惶,半天说不出话。
李若水悲恸至极,已辨不出郭京心意,乃长跪叩首,苦苦哀求郭京率神兵出击金军。
郭京瞪眼半晌,道:“要我神兵出战,那,那也不妨,只是,只是这粮饷……”
李若水道:“仙人想要多少,只管说来,若水便是粉身碎骨,必为仙人筹齐。”
于是朝廷紧急清点府库内帑,将众多财宝搬到郭京府上。
张叔夜听闻自己拼死护主的几十名勇士,竟被一个术士抢了赏赐,立时就来找郭京算账。
郭京初时惊惶已退,此时又做大起来,命人将大门紧闭,传话道:“你才杀了几个金兵,敢来找我的麻烦!若坏了我的法事,便将你凌迟车裂,也赎不得罪过。”
张叔夜大怒,抡起狼牙棒就要砸门。
李若水止他道:“将军息怒,当此之时,只有仙人才可逆天改命啊!”
张叔夜愕然,呆望李若水半天,突然“嘿嘿”挤出两声怪笑,哭道:“天意,天意啊!”说罢豪泣而去。
张俊亦无他法,只好向郭京传话道:“既如此,明日便要见识仙人手段,若果如其言,我等皆向仙人下跪认错,任凭处置,若有半分差池,哼哼……”
郭京亦传话道:“明日只须神兵三百,定能生擒金军左右二帅!若我高了兴,莫说燕云十六州,便打到阴山,又有何难处!”
当夜,郭京吓的睡不着觉,待要逃跑,又无处可去,事已至此,又有何办法。
金军方面,宗翰深知金军伤亡颇大,他见雪尤未停,命人趁夜掩埋收敛金军遗体器械,只将宋军遗体暴露在显眼位置。
当夜,宗弼不顾疲惫来寻阿合。他早知道宗辅将阿合安置在战场外,恨不得空来见。
阿合见宗弼赶来,大为吃惊,道:“你受伤了!”
宗弼笑道:“不曾伤到,只染了一身血污,我们去泡温泉吧?”
阿合打发宗弼洗澡,见他头发都被血块粘住,道:“这些日子杀的惨烈吗?”
宗弼笑道:“早习惯了,也不只是这些日子惨烈。若不是为了见你,哪顾得上洗澡。”
阿合不言语。
宗弼道:“萨萨,你不高兴吗?我虽今日才来,却时时想着你,只是军中多事,又怕那些臭男人吓着你。你不知打起仗来,军营里男人多坏呢。”
阿合随口道:“怎么坏?”
宗弼道:“抢财物、杀俘虏那都是小事,玩男女俘虏才最恶心呢,我见他们故意把人肠子拉出来,看谁存的屎尿多。”
阿合道:“那不是疯了吗?”
宗弼道:“平日里刀尖舔血讨生计,凡打赢了,必定狂欢无度,若有女人还好,没有女人的时候,只好做些抠**、挠脚心的恶心事,或者把火气泄在俘虏身上。前几日攻城不顺,宗翰哥哥他们每日都要杀几个不肯拼命的士卒,又逼俘虏们冲到阵前送死,一时死不掉的,都被玩的生不如死。”
阿合不言语。
宗弼拉着阿合手道:“此处不好,待打完了,咱们一起回燕山,我找了一处很大很好的宅子,后院还有两棵几百岁的大树,以后我们常在一处看星星,好不好?”
阿合道:“能别打了吗?”
宗弼道:“边打边谈啊,我也说不好。”
阿合道:“宗翰郎君和宗望郎君,到底怎么想的?”
宗弼道:“最次划河而治,其次降伏赵氏,再或者,我们一举南下,问鼎中原。”
阿合道:“那得到什么时候啊?”
宗弼叹气道:“我也不想打了,若说土地财帛,咱们这辈子早尽够了,和我姐姐姐夫那样,不也很好吗?”
宗弼烤干头发,见外面雪终于停了,道:“明天会杀的更惨,总要杀个5~6天才见分晓——我今日又死了一个护卫,才刚满16岁,脸嘟嘟的还没长开。我原想送些金簪子、金镯子、金戒指给他那眼花的姥姥,没想到他一大早被砲石砸碎了脑袋,估计他姥姥也不认得了。”
阿合望着宗弼,总难想象这样孩子气的少年,竟可以这样平淡的谈论这些,或者,做出这些。
宗弼因之前几次总不能成事,猜想阿合不喜用强,此次便改变策略,一味搂着讨好。
阿合本想重提“美玉无瑕”的事,却根本无法开口。事已至此,那个借口还值什么?
宗弼见阿合不似先前一味抗拒,兴奋的不能自已,稍一用力便把她压在身下。
阿合努力想要接受现实,却发现长久以来她在意的并不是什么“美玉无瑕”,而是委身宗弼。是的,这个多年以来令她困惑的问题,终于在她决定认命的时候清晰了起来。
她如此熟悉宗弼,如此喜欢宗弼,却并不想嫁他——这多么可笑,其实她从小,就厌恶宗弼的强势和善妒吧。她不止害怕威严不可攀的阿骨打,也害怕偏执不罢休的宗弼。
宗弼感觉到阿合的异样,小心道:“你又哭了?是怕我欺负你吗?可我们成了婚,总要那样的。你就稍微忍一次,以后肯定会喜欢的,我可厉害了。”
阿合坐起身子,啜泣不已。
宗弼默默看着阿合,慢慢明白了她的意思,道:“你其实,只是不想我碰你吧?什么‘20周岁前保住处女之身’,什么放不下染坊,什么再等四年,一年一年又一年!”
阿合心里愧疚,突然不敢面对这个一直对她言听计从的男人——他只是选择听萨萨的话,而她却不能选择不做他的萨萨。
宗弼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你为什么不能喜欢我一点?一点点就够了。”
阿合道:“我喜欢你,但我害怕你,不想嫁你。”
宗弼道:“我并不会欺负你。你不想回会宁,我们就不回会宁;你想开什么染坊磨坊,开多少都随你;你不喜欢我从军,待这里打完,我只跟你待着,哪都不再去!”
阿合无言以对,有些事情,其实真的没什么理由,也没必要强调借口。
宗弼抱着阿合,道:“萨萨,我想你……”
阿合不敢看他,低头道:“还是,等明年吧?”
宗弼大怒,跳起来就乱摔东西,阿合也不敢劝他,只是坐着发呆。
宗弼道:“你到底有什么话,倒不肯说?只一味哭什么!我从出生到现在,何曾对不住你?你纵要打要骂,我还能跟你动气?你说也不说,打也不打,哭的我烦死了!”
阿合哭道:“谁要你来?谁愿烦你?难道是我想待在这里?”
宗弼道:“要不是我三哥,你早被那个什么‘哭丧王’坑死了!我恨不能把心剖给你,你却情愿跟了他去!”
阿合道:“我谁都不愿跟,更不愿跟你!”
宗弼待要还口,当场气哭,流泪道:“我何尝得罪你?这样说我……我出生入死这些日子,你竟无一句好话对我……”
孙和尚等人听见宗弼哭,凑在一块商议对策。
孙和尚叹气道:“因这妇人,白挨多少打骂,究竟如何是好?”
渤海护卫大草里道:“阿撒和韩奴托故不来,他俩都怕,咱们更不济。”
阿合见宗弼哭的厉害,道:“你回吧,明日你二哥找不到你,又要怪你。”
宗弼道:“我不回去,我就在这待着,哪也不去。”
阿合无奈,自穿衣服出门,让护卫们领宗弼回军。
护卫们都不敢吭声,大眼瞪小眼看着。
阿合道:“你们此时不领他回去,待明天宗望郎君一样饶不了你们。”
护卫们无奈,孙和尚和大草里打头,进去劝宗弼道:“郎君,有什么话,待打完再说,也是一样的……”
宗弼半天不吭声,突然站起来道:“待灭了赵氏,我非教‘哭丧王’死在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