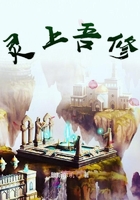栖暮这几日实在是提不上劲儿,想着自己恐怕是病了,但也不是头一回生病,自己便也没有太过在意,这样撑了几日,却觉得越发力不从心了。
等到了今日晨起,他才觉得实在是身子沉,想着便躲懒一日罢,才复躺下又想起后山新种下去的荼蘼花还未去浇水,叹了一口气,便强撑着又坐起来,穿上外衫去到院里提了水桶往后山去了。
因为没什么力气,做起事来栖暮便显得有些慵懒,等施了法,将掺了灵力的泉水尽数撒到了植被上他便倚在树下望向那片荼蘼,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养成,到时候便是一片花海,正好给枝枝做生辰礼。
栖暮站起来的时候还微微踉跄了几步,伸手揉了揉太阳穴又休息了一会儿才拿起东西回去。
他才回了院子,准备去房里躺一躺的,便有客来访,只好坐在院子里,奉上了两杯热茶等客人至。
等瞧见来的是敖望的时候,栖暮再怎么不动声色心里也还是微微叹了一口气,伸手招呼了一声便问道:“殿下这是又有什么疑问了?”
敖望坦然行了礼便落座,伸手拿起热茶浅尝了一口便放下来,答道:“近日接了公务,有些事情不大清楚,便想着来问一下山君。”
栖暮却不大给面子,说道:“殿下也晓得我只是山君,这事务上我怕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殿下的兄长最是晓得的,何必来我这里,倒是有些舍近求远了。”
敖望却自有说辞的道:“山君师承自清妙真人,只是更善育万物罢了,能得山君指教是我之幸。”
栖暮看他是铁了心的要在这里耗着了,也不再赶客,但也晓得他并不是真心来求教的,便随便说了两句带过这事便罢了。
两个人这样各有心思的说了半晌话,栖暮看他的模样,心里想着他年纪虽小,却倒也坐的住,还是暗叹了一把,但他今日身子并不舒坦,这样闲坐了半晌有些撑不住,衣袖掩面干咳了两下,便想着送客了。
敖望看栖暮素来清瘦,今日来看又更显得单薄,此时面上因为咳了两声染了些许薄红,便晓得他今日身体并不舒服,也不再多言,只嘱咐了几句保重身体便离开了。
栖暮这边送了敖望离开便也歇下来,不料隔了几日他又来了,一见面便问道:“山君看着怎么比前日更瘦了?”
栖暮摆摆手,不欲谈这个话题,正要问他这次来是又做什么的,敖望便已经先一步开口道:“山君身体不适这么几日了,我瞧着是有些严重,我家里有位医师,不如叫他来为山君看看?”
栖暮闻言便连忙摆手道:“快别,我自己会用药的,就不劳烦殿下了,好意我便心领了。”
敖望却不是很赞同,劝道:“山君该保重身体才是,枝枝在外游历,知道你身体不适想来也正烦忧。”
栖暮闻言便笑道:“殿下未免对我家枝枝太过关注了。”
敖望这才显出几分少年的羞涩来,没有接话,等栖暮好不容易打发了他,并推说自己往后一段时日需要养病,不再接访客后才又安心回了内室躺下。
躺在了床上栖暮却并不闭眼,这几日许是身体不适,便有些孤寂之感,入睡后又总是梦到些往事来。
栖暮并不想梦到这些,但入了梦却又总是难舍难离,他最后还是微微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
思君入梦,他自己心里明白。
又是那座小院,却并不如之前梦到的那般浮着温馨,他似是有知觉,晓得之后要梦到什么,挣扎了想醒,却还是困在了梦里。
他本是待在小院里,研究上次回山里输给他那师弟的一盘棋,前院却热热闹闹的,平白吵闹惹得他有些恼。
府里向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今日这般倒是有些不寻常,他不由得心下有了好奇。
栖暮出了院门,见到处都挂上了红绸,看起来很是喜庆,不由的心下却是有些不安,看见路过的小厮,便上前拦了下来,问道:“府中这是怎么了,要办什么喜事吗?”
小厮见是栖暮,知道他是将军好友,忙笑着答话道:“公子没听将军说起?下月初五,将军便要同尚书姚大人家的大小姐成亲了,今日是定亲宴,来的都是将军的军中友人,想来是晓得公子爱清静,便没有来喊公子去喝酒的。”
闻言,栖暮手里的扇子没有抓稳,“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正面朝上的还是那人亲手提的字,写着“人面桃花”。
他强忍着又扯出笑来,说道:“许是将军他,事务繁忙,忘了知会我一声。”
说罢,那小厮只见他身影跌跌撞撞走了,连扇子都忘了捡起,再唤他似是没听见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