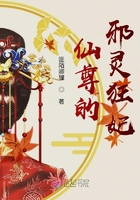潘凉问道:“李肥,你没事吧?”
李肥不觉三魂六魄已然回窍,灵思瞬间清明起来,思维陡然活络,眼前一片清晰,看到的终于不再是一重重流动的世界。
李肥看着双手滴答的茶水,地上散落的残片,恍若隔世,手有点疼,已经泛红了。
李肥眼光瞥了一眼吕先生,二人眼神一触,各自收敛,李肥摇摇头,对潘凉说道:“没事,就是被茶水烫了一下。”
潘凉感觉自己身旁的李肥忽然变得有些怪怪的,不就摔碎一个茶杯吗,至于这副表情?虽然只有一瞬,但李肥的错愕与震惊还是被潘凉看在眼里。
我真的回来了吗?李肥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境的内容很真实,历历在目,身临其境般,以至于在他醒来后一时都分不清楚虚实真假,但这种真实却是在极为短暂的滞留后,开始迅速消退,仿佛在告诉李肥,这只是一个梦而已,再真实的梦醒来后,也不过是剩下虚幻与不真切。
吕长吉微微一笑,虽然李肥回来时还在此刻此间,却已经不记清自己到底溯回了多远多久,悄然间一切都好似没有发生过的样子,那些见闻已然化作久远记忆中的补充与修正,并无突兀撕裂之处。如不是李肥人心不足,试图去做逆势的事情,此刻还依旧沉浸在光阴流水中呢。
李肥忽然张口结舌,赶忙捂住嘴巴,那个记忆中本来有些模糊的小老头样貌,此刻竟然跃然脑中,无比清晰,包括他脸上的皱纹,头顶稀疏杂乱的头发,以及那夜里省油只点一盏灯时,烛火照映在脸上照印不到的深壑,和那夏日比夏日蝉鸣还有聒耳的鼾声。
甚至于,那个头戴幂篱的妇人,脸色苍白,看着自己的眼神中极度疲累,带着慈祥和不舍的目光,再没力气说出一句话,就撒手了。
李肥从不敢奢望自己脑中能有个娘的模样,从小就懂事的他也不会缠着老爹问娘的事情,只是听大哥说,娘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大哥的样子随爹,而自己的样子,更像娘些。
“真没事?”潘凉神色狐疑。
“真没事。”李肥胡乱抹了一把脸,看着一地碎片水渍茶叶,笑着转移话题:“吕先生,不用赔吧?”
吕长吉笑道:“不用,本就是这乡学馆中之物,你没伤到就好,我来收拾吧。”
吕长吉拿过笤帚畚箕,将地上的碎物打扫归拢,说道:“我再去沏一杯。”
这次李肥没有推辞,实在是需要一杯茶镇镇神。
第二盏茶入手,李肥感受到手心温热的坠感,自然而然的口渴起来,啜饮。
炎热之季,茶凉也慢,潘凉坐在高凳之上,双脚还有些不能完全踏足地面,真就是个孩子,一脸愁色,神情与姿态实属不搭。
三人都不再说话。
待到盏中茶水见底,李肥轻轻将茶托放在茶案之上,瓷木相击扣响一声,仿佛是打在心上。
吕长吉说道,“走吧,咱们出去走走,也要寻个法子将小泥鳅塑出来。”
潘凉闻言,顿时全部心神都被小泥鳅所牵引,自然是无暇思虑其它。
吕长吉拔腿向外走去,李肥拍了拍潘凉的肩膀,示意跟上。
只一出门就倍感暑热,吕长吉身着泛白的长衫,神色自然,徐步缓行,潘凉攥着衣角,紧跟其后。
李肥缀在后头,头顶白日,恍惚抬头,刺目,流泪。
吕长吉突然问道:“潘凉,这清风拂面、雨水浇头都有所感,那么沐浴阳光是何感受呢?”
潘凉垂着头,小声道:“热。”
吕长吉莞尔一笑:“倒也直观,的确是光附带的一种内弦感受。是我问题问的不好,与其说是沐浴阳光,不过说若是没有阳光,我们该作何?岂不是一直都处在阴暗里?万古如长夜。”
潘凉虽然还小,却是敏感的体会到了吕长吉的言指之处,反驳道:“还有月亮。”
吕长吉摇摇头,“太阳在,月亮才在,太阳不在,月亮也会失色,可能有一些星星还会闪烁,但是距离我们太远了。太阳运行到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便身处黑暗;明日高悬,光照在身,脚下自然留下影子,这些都只是色蕴所限,质碍所阻,算不得真。当你以为阴阳对立的时候,弦外之物依旧是奔走不息,穿行而去,而我们一直在阳之内。”
李肥灵光炸响,脑中泛起一些不属于他认知中的涟漪,走过一趟光阴长河的他,不知在其中流连了多久,对其本质至少是有些粗浅的认识,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李肥忽然觉得光阴长河不是什么太过玄奥的存在,甚至有些合理。
其中道理便在于跳出质碍,以足够的距离去看待事物,常人所能感受到的五弦:视、声、味、触、嗅,再加上练气士的灵觉,再无他样,每一种弦的波动长度都是不同,且每种弦的速度都快过人的感官,近距离感受这几种弦的波动,因为肉身栈的桎梏,却是无法精确分离,重重交织之下,才形成了人所生存的世界,若是能解脱了肉身栈的桎梏,神思清灵,又是不在局中,所感这种种弦之波动,其实有快有慢、有长有短,千差万别,其中最迅捷的当属视弦,遥遥领先,快逾闪电,即便如此,在广袤的宇宙之中,视弦的传播也不过是鹅行鸭步,遑论被其甩在身后的其它弦,若是能通晓各种弦的传播速度,将被动的接受能力统一调度,在辅以各弦不同的分析整合,便能看到最真实的世界,而光阴长河,是弦尚未波及之处,站在长河之中,顺着自己的旧识溯回,静待弦至,便能看到过去,站得越远,看得越前,甚至是一眼千年,至于能不能看向未来,李肥暂时还没有头绪,只是打心里更倾向于是不能的。
潘凉双手绞在一起,“吕先生,我只想要我的小泥鳅。”
吕长吉摇摇头,言下之意很明白了,就是听不进去道理。也对,“阴在阳之内非在阳之对”这个道理,对一个孩子来说还太难懂了,何况还是一个被仙人手段枉曲过的可怜孩子。
吕长吉说道:“事先声明,你那小泥鳅的来路你自己最清楚,无非是恶念所化,有形无质,鬼蜮之物最难管束,一般来说是被牢牢关在心湖之中的,它作囚徒,你为狱守,换句话说,只有你应允,才能放它出来,至于你境界攀登太过顺遂,筑基练气又不正统,一上来就是心动境界,所以才显得有些乱了套。”
“你现在是因为使唤不出来小泥鳅,所以认定是我做了手脚,其实不然,练气士的心动境界笼统来说便是在心湖上开一扇窗,才使后续能习得心神传音的秘术,你在心动境界时,心牖不闭,小泥鳅自然能在不得到你应允的情况下在你眼皮底下进进出出,其实是主客颠倒的情形,只是这种情况久了,你又习以为常了,等你突破到了结丹境界,顺理成章,一身灵体抟成一颗金丹,这小泥鳅乃是受你体内灵气血食奉养多的,其形自然是被杂糅抟在丹内,如今只剩纯粹念头还在心湖,成了无形无质之物,所以即便是你现在有意召唤,它也没有假身可以凭借,不是它不停使唤,而是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
吕长吉颇有些无奈道:“不过这事你要是全赖我,我也只得捏着鼻子认账了,毕竟没我那一弹指,你也不会误打误撞的结丹了。”
潘凉似懂非懂,不敢说话,只敢看着吕长吉,眼神有些委屈可怜。
吕长吉心一软,说道:“就当是伯仁因我而死吧,我想与你说的便是阴阳智慧包含万事万物,阴阳的对立斗争、依存互根、消长转化亘古鲜有变化,我不求你通晓阴阳易理,只是想你不要固执己见,觉得这世界非黑即白,善恶既定,自己注定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的。”
“就像人看到肉畜挨宰时,也会不忍它死;听闻它的哀鸣,一样会不忍食肉,不见之时却又说着食色性也,心安理得。人就是在天理与人欲之间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位,循环往复的自相矛盾,不断平衡,阴阳相济,才能在万灵之中,侥幸领先一个身位,是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你怎么能独独例外呢?”
潘凉一言不发,兀的想起了黑毛,两手指节捏的发白。
吕长吉知道潘凉的心结,轻声道:“那事情怪不得你,罔顾性命定然是错的,若因惜己命而不得已,也不算不顾自己惜命,两害相权,摆平心间那杆秤,最终结果又能不堕心志,心知自己做了不算对的事情,至少错得不离谱。”
见潘凉不语,吕长吉倒也没有强行开导,轻声道:“即便我今日将话与你细细明说了,你也还是可以说不懂,你这岁数,真就是百无禁忌的时候,食色喜怒,人之天性,有的是时间慢慢学、慢慢悟,早晚都会懂的。”
吕长吉伸手点了点潘凉的额头,潘凉下意识想要躲闪,前者指间却已轻触而返,潘凉额上尚有触感,不明其意,如同以莛叩钟。
吕长吉脸色微变,轻叹道:“这外道仙人的手段当真难解。”
与此同时,万里之遥的一洲之地,正与弟子弈棋的徐奉戏双眼渗血,自眼角挂下浓稠血液,犹如两条细蛇,犹自挣扎一番。
“当初袖手旁观的是你,现在亡羊歧路了,你还寻得回来?”
徐奉戏一抹眼,一挥手,进车压马,恍若无事,与其对垒的弟子战战兢兢,不敢抬头。
吕长吉不再言语,负手沿着乡间小路而行,路的两边不时伴着溪涧,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潘凉与李肥家门口,行至半山腰的山塘之上,山塘蓄满了整个黄梅天的雨水,雨停日炎,没几日已经用去小半,那条官府挖掘的山塘溢洪道也是完全裸露出来,溢洪道中遍是沉积多年流水带不走的砾石,以及间隙之间夹杂的浅色沙土。
吕长吉问道:“会打水漂吗?”
潘凉默默点头,李肥回答不会。
“我以前在外求学,路过一处山塘,见到有许多小孩在水边打水漂,我刚好累了歇脚,大概过了半个时辰,等我歇够了,他们还在捡着石头不停的打水漂,后来有妇人寻来,领了一个孩子回家吃饭,是拽着孩子的袖子骂骂咧咧走的,原来那里的乡俗说,把石头扔进水里是不道德的,石头陷在水底的淤泥里,见不到太阳,就像是被打入了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可我见到,即便是那妇人驱赶一番,其余的孩子也没有要散场的意思,依旧乐此不疲。”
说着,吕长吉弯腰捡起一块扁扁的石头。
“吕先生……”李肥欲言又止。
吕长吉把石头递给潘凉,问道:“假使河泽乡便是那乡,乡俗便是不能把石头扔进水里,但是你又想打水漂,该怎么办呢?”
潘凉没有抬手,摇摇头,嘟囔道:“我不想打水漂,那石头见不见到太阳,和我有什么关系。”
吕长吉呵呵一笑,“不想要小泥鳅了?”
潘凉眼底闪过一丝乖离之色,一把接过小石头,将其用力掷了出去,力道之大,使得小石头在水面溅起极高的水花,一连跳跃了十余次,最终沉入水底。
吕长吉指着远处的涟漪问道:“你说它是不是从此不见天日了?”
潘凉开始焦躁起来,紧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吕长吉没有说的是,那外乡两千多年前叫做安阳乡,地理位置上与现在的河泽乡大差不差。吕长吉手指一引,远处水面刚刚平息的涟漪再度漾起,升起方才那块石头,流水将其缓缓推回岸边,吕长吉弯腰拾起,再次递给潘凉,“力道用太大了,试着用些技巧,再试一次?”
潘凉直直的瞪着吕长吉,不做反应。
李肥心领神会,看向吕长吉,出声道:“吕先生,要不给我试试?”
吕长吉点点头,李肥接过石头,入手居然是干的,仿佛方才没有掉入过水中一样。
虽然是第一次上手打水漂,却是看着不难,只见李肥猫下腰,手上使了巧劲,指尖石块打着转,微微倾斜飞出,接触水面时轻巧弹起,一上一下不断跳跃,竟是弹跳了二十余次才落入水中,那石头入水之处,距离岸边已是不远矣。
潘凉眼睑微动,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吕长吉欣慰一笑,不愧是李肥,再次招手,流水推送着石头沿路返回。
吕长吉没有再说话,只是将石头递给潘凉。
潘凉接过石头,蹲下身子,没有犹豫,不做思考,一下平掷出去,石头旋得飞快,力道也是不减,只见石头在水面跳跃,本就因为缺水而缩小许多的山塘水面上,仅仅三十几下弹跳,石头就从这一边,跳动至另一边的岸上。
吕长吉拍拍潘凉的肩膀,说道:“你看,只要用对方法,就算是你想打水漂,石头不见得会沉入水中,就算是真的石沉水底,你看那溢洪道中的砾石,每年黄梅季节山洪泛滥之时,不总有些顺着泥沙被冲出来吗?也没有说就一定会暗无天日的过一辈啊。”
李肥想起圣贤说过那句,“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体内浩然之气流转,似乎是对他有所肯定。
潘凉就算再迟钝,此刻也该明白吕长吉的意思了,多数时候,他不是不懂,而是不想懂。
吕长吉说道:“我方才已是从你足太阴脾经两副经络穴位中贯通血气,足太阴脾经对应巳蛇,左右两副共四十二个穴位。你试着用血气运行到心脉再使唤小泥鳅出来,与先前也无大区别,只是以后要经足太阴脾经这条路往返内外了。”
潘凉闻言一惊,急忙内视自身,他当然不知道什么三阴交、阴陵泉、血海、簸门的穴位所在,只是体内两副经络图自然浮现,一个念头,不需什么心思操作,心血涌现,凭空捏造实物,化作小泥鳅的一副躯壳。
潘凉身躯一震,低头看去,一条三尺长的灰鳞小虺已经缠绕在自己脚边,吐着信子,正小心翼翼的打量着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