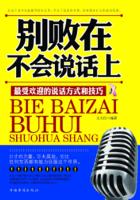六月初七,丁未日,出梅,休沐日。
黄历上说,宜出行。
李肥难得的起晚了,不过也不需早起上学,昨夜不知为何思绪作祟,不得安眠。
夫子和李先生也要走了,带着除李肥之外的所有学生,一同去往越州下菰城。
去往那座南边学子都梦寐以求的鸿都学宫。
起床之后,李肥去了水缸旁洗了把脸,取了一瓢水开始煮昨夜留下的米饭。
吃过早饭,李肥把剩余的泡饭粥喂给了碳球和黑毛,自己带上了篱架门,就往陈家走去。
昨日约好的,吃过午饭之后,所有学生都要在乡塾门口集合,由陈家大老爷雇了三辆板车,送大家去县城。
李肥受夫子邀请,要去陈家吃午饭。
李肥走到那扇不算陌生的陈府大门前,推开虚掩的半扇门,昨日夫子还交代过,上他家,不用敲门。
时辰尚早,还没有学生聚集在这里。
走过影壁,映入眼帘的,正是陈夫子坐在前院和李唔老先生手谈。
李肥只知道围棋的规则,却不下得很好,不过还是看得出个大概的。现在正是棋高一着缚手缚脚的局面,缚手缚脚的明显是那个紧揪长须而不自觉的李唔老先生。
看到李肥,李唔仿佛顿时眉开眼笑,行云流水般离开了精雕的纵横十五道的石桌,拉着李肥的手,热情得就像独居的老人突然看到探亲的孙儿一般。
李肥抽不出手行礼,只得口头问好。
陈凤垂投下棋子,自然心领神会,不再专注于棋盘。
“早饭吃了吗?”陈凤垂笑着问道。
“吃了。”李肥点点头,这时才抽出手来,连忙补了一个学生礼。
陈凤垂近来总觉得李肥有些心思活泛,却又不知为何,只能感觉那一枚他按在李肥心湖的梧桐叶,总是被他的心神拖曳摇动。
三四次后,陈凤垂都只能见怪不怪了,只能说临近心动境界,李肥这是心猿不定、意马四驰。
“夫子有礼物送你。”陈凤垂对李肥笑笑,“也是夫子借着先生的脸面,从鸿都学宫大祭酒陈道流先生那里讨要来的。”
“说是讨要,不如说是请是陈祭酒为你准备的见面礼,你这次不去,所以我就直接给捎来了,本来是想着你去当面和他道个谢,所以也别推辞。”
李肥受宠若惊,不敢推辞,只向夫子和李唔老先生能行礼道谢。
陈凤垂拍拍李肥肩膀,示意他坐下。
陈凤垂一招手,棋盘上的黑白棋子各自回归各自的钵子中,将桌子清理干净。
一架瑶琴出现在桌上。
李唔看到这一幕,满意地点点头,只怪徒孙来的太不是时候,这盘棋只能算和了,不然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呢。
“陈忌酒既是学宫大儒也是斫琴大家,我在你家门前那棵梧桐树上截取了一小节枝干,请他为你做了一架瑶琴,名为九霄环佩也唤作凤鸣环佩,也是一架仿琴。”
李肥喜出望外,双手捧起瑶琴,眼里是藏不住的喜悦,扶过琴身上的肌理,李肥感觉到了一些熟悉的类似小灵天的气息。
经陈道流之手,本就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妙,何况是取材于一个曾经是长气境的本命梧桐木,虽然只一件乐器,但是还是些品秩的。
“李肥,你夫子原先只以为你家门前那可棵梧桐树对他有些裨益,没想到是让他受益匪浅,这会儿才知道是占了你大便宜,当然是要告诉你一声,闷声发大财的事情不好做。”李唔说道。
“我知道这个道理,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李肥赶紧谦虚道。
李唔笑骂道,“你知道个屁,有些道理知道就只是知道,只有经历过了才算懂。”
李肥捧起凤鸣环佩琴,爱不释手,险些就忘了矜持,“夫子为何要说也?”
陈凤垂再度取出一架古琴,笑着说道,“太古遗音,师旷式,既是仿琴也不是仿琴,乃陈祭酒早年所作,本是作己用之物,但因为一番事故,陈祭酒不想带在身边,原名大圣遗音,现在不仅翻新,还易了名字。”
“这世上的真琴,为人知的,大圣遗音应该还有四架,九霄环佩则大概是有九架,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桐木胎,黑漆朱髹,虽存世千年,仍品相完好。通体断纹斑烂陆离,龙鳞,龟坼、流水、蛇蚹错杂相间,世间罕有能与之相匹者。”
“但也不是说仿琴就不绝对如珍品,以陈祭酒的手段高明,后来居上,所制之琴也不逊色真品几何,主要还是断纹的差距。几次斫琴,如若不是因为仿琴的尴尬处地,同样也能是流传于世的珍品,只是现世名声稍逊而已。”
“挑一架?”陈凤垂问道。
“学生想要凤鸣环佩琴。”李肥并无纠结,认真说道。
如若太古遗音给他的感觉是恰到好处的心头好,那九霄环佩给他的感觉就是惊艳,一见钟情,更深一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用自家梧桐木所制。
“你看看。”陈凤垂一手指,牵引李肥的视线,太古遗音的琴身上露出三行双钩小篆,“落落梧桐、凤鸣秋月、月上梢头、凤落梢头。”。
龙池凤沼处有篆印“么凤”,金漆填刻“振玉”以及“凤鸣环佩”。
草书:“佩剑冲金聊暂据,匣琴流水自须弹。”
手书:“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
“么凤?”关于草书和手书内容,李肥都还算懂得,却是对么风二字,神情有些疑惑与猜测。
“有何想法?”陈凤垂问道。
“雏凤清于老凤声?”李肥不敢断定。
“如果是前面半句还能算是搭边。么凤是方言,就是指桐花凤,‘家有五亩园,么凤集桐花’或者‘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凤’可曾听过?”
“夫子又不曾教过,我哪里会听闻。”李肥难得有些耍性子玩赖的回答。
“顽贼。”李唔笑骂一句,却是说不出的喜欢这个徒孙。
“再看看太古遗音?”陈凤垂问道。
而太古遗音的琴铭就只有三个字,“想环佩”。
所以忽然间,李肥便知自己后悔了。
“遗音想环佩?”他试探的问道。
“丰收啊,这句话,你教过李肥吗?”李唔打趣道。
“没有。”陈凤垂笑着回答。
李肥破天荒有些羞赧,问道,“夫子,我可以要这太古遗音琴吗?”
“都是你的,”陈凤垂轻抚凤鸣环佩琴,语气温润,眼带笑意,“太古遗音夫子就先替你收着,等以后你遇到了你喜欢的姑娘,就把凤鸣环佩琴赠与她,回来再向夫子讨要太古遗音,等那时候你才知道它的好。”
李肥点点头,神情赧颜,不知道在想什么。
“李肥啊,听丰收说教过你《云门大卷》和《招》,你对乐的部分掌握的很有灵性,所以后来单独教了你《琴操》,你也学得挺不错,是吗?”李唔问道。
李肥挠挠头,不敢觉着自己真就学得不错,只说能拨弄几下琴弦,听个响儿。也不好矜持或者真就受下了,因为乐这个东西要靠悟性,李肥平日也见不得同龄人学琴,自然没个对比。
若是李先生夸他学问上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学得好,有徐得意这样的珠玉在侧,李肥便直接说是先生抬爱、错赞就好。
“先生陪你奏一曲,考验考验?”李唔忍不住技痒。
“只会些简单的曲子。”李肥怕先生对自己期望太高。
“五曲、九引、十二操你哪一首熟稔些?”李唔问道。
李肥回答:“猗兰操。”
“不简单。”李唔眼睛一亮。
“我素来不爱讲究,觉着抚琴之前濯手焚香太过矫情,所以就取丰收的琴与你同奏吧。”李唔说道。
陈凤垂闻言,取出自己的爱琴,置于石桌之上。
“李先生,其实小子也太不讲究这些的。”李肥挠挠头。
“不,你得讲究些,为你斫琴的陈祭酒,是个大雅之人,曲艺高绝,向来有六忌五不弹,自珍得很。所以他所制作之前虽好,我却是不想弹的。”李唔说道。
“学生只知道六忌,五不探是什么?”李肥问道。
“疾风甚雨不弹,于尘世不弹,对俗子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
李肥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布衣。
“不过李肥你还未及冠,规矩少些吧。”李唔说道,施展了一个简单的水法,替李肥洗濯了双手。
“先生也不是故意要扫你兴致,只是想你知道这礼物的珍贵不在物价,而是在斫琴之人的情操,才希望你至少能身临其境一次,感受一二。”
“学生牢记。”李肥明白老先生用心,认真答道。
李唔有些欣慰,说道:“我虽不用,于我何伤?言霜雪之时,荠麦乃茂,兰者取其芬香也。今此操只言猗兰,盖省辞也。”
李肥心领神会。
二人不约而同抚琴。
淡淡琴声悠扬,起先是两股磨合,随后便是交融,宛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
房中的陈老太爷听闻琴声,都在身材婀娜的妙龄丫鬟儿的搀扶之下步入庭中。
“爷爷。”陈凤垂起身问好。
老太爷点点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静静聆听。
时间悄然流逝,猗兰操曲意幽长,悱恻不断,老太爷的丫鬟儿到底是受过熏陶的,听曲意便知这曲子一时半会儿绝不了,不敢忘记自己的本分,在老人身旁小声提醒道:“老祖宗,这黄梅天刚过,外头阴湿,别呆太久了,晚上腰腿疼的。”
老太爷也是耄耋之年,平日里被贴身丫头管习惯了,便由着少女搀扶着回了屋,走时不忘点头致意。
用口型说道,“洗耳了。”
李肥赧颜,眼神感谢。
曲罢。
李肥额头出了一层细汗,期间好几处调子都弹偏差了些,第一次与曲艺高绝的李老先生合奏,难免紧张,瑕疵毕露,无所遁形。
“不错不错,琴声在音不在弦,很不错了,以此琴操,可做饯别了。”李唔抚须大笑,拍拍李肥肩膀,“果真有灵气,我去和鸿都学宫的嵇大家说说,他肯定会很中意你这棵苗子的。”
陈凤垂听闻李唔老先生的言语,觉着先生对李肥也太偏爱了些,便提点道:“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李肥自然虚心受教。
李唔却是一个白眼翻去,“就你会说话?”
陈凤垂无奈道:“先生,这隔代亲也太过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