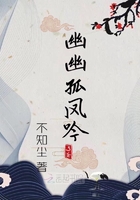冯嘉回营的时候,整个秦军都沸腾了。
三百铁鹰剑士从车城圆阵中心对穿而过,斩帅夺旗,杀了个来回,竟只有十几人受了轻伤。
司马靳的弓弩营伤亡更少。毕竟,在断粮四十余日之后,眼前这支赵军已不再是当年那支在瘀与狭路中惨胜秦军的那支血勇雄师了。阵前对射,秦军强弩能射到三四百步开外,而赵军弓箭能射到一两百步的已是极少。
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仗,真的要结束了。
果然,在第二日红日刚刚升起的时候,投降的号角声在赵营中呜咽地响了起来。
衣甲残破的赵国士兵缓缓从破碎的大阵中走出,依次将手里的武器丢在旷野上,渐渐垒成了几座小山。
血红的朝阳洒在已几乎被鲜血染透的土地上,直让人分不出哪里是血,哪里是光。
广阔的长平河谷里没有一丝人声,战马也已杀尽。二十万枯瘦如柴的赵国士兵犹如失了魂魄的行尸走肉,零零散散地坐在田野上,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这是长平之战赵国四十万大军被围的第四十六天。上将军赵括率军突围,被射杀于阵前,余下二十万人人带伤的将士终于弃械投降。
秦军足足花了一整天时间反复探查,才确认赵军已彻底再无抵抗之力,决意正式受降。
傍晚时分,冯嘉接受白起将令,带着一个什人队深入赵营清剿剩下的兵器。
入夜后的赵营,冰冷沉寂得不似人间。冯嘉每走一步,都觉得背脊更冷了一分。
野地里三三两两地坐着抱着臂缩成一团的人,一眼望去,不知是死是活。军帐间零星有一块块的火堆无力地燃着,朽木杂草冒着黑烟,不知混进了什么东西,味道很是刺鼻。
冯嘉暗暗心惊,不由握紧了剑鞘。他武艺不俗,能看到的东西,比常人更多了几分。
那些赵军士兵眼中泛的光芒,已经不像是“人”了。他们蹲在地上,死死盯着走近的人,好像一只只受伤的兽,绝望却贪婪。
每个人都形销骨立,眼窝深陷。有些失了衣甲的,后背能清晰地看见一根突出的脊骨。
又走了几步,冯嘉忽觉鼻中一下刺痛,立时抬手制止了部下前行。
前方是一座尚算完好的营帐。营帐门口生着一个火堆,其上架着一口大锅。
锅里的水咕咕开着,里面正炖煮着几根上下漂浮的白骨。其中两根较为短小的有整齐的断口。另外还有一些细碎的骨头沉在锅底,已经看不分明。
这是一个人的手臂!
而且——曾被齐腕斩断。
是那个刺客!冯嘉瞳孔急缩。一抬头,正见一个人缓缓从营帐里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独臂的将军,披头散发,拄着一柄乌鞘长剑,瞳仁乌金璀璨。他脸色极其苍白,嘴唇乌黑发紫,整条右臂齐根断了,连袖子都没有,只简单包扎了下伤口。
“是你。”冯嘉心头震动,皱眉道,“这是为何?”
独臂将军阑珊一笑:“反正是废了。剩几斤肉,不如索性煮来给将士充饥。”他浑不在意地道,“再晚一点,另一手煮来也无不可。”
冯嘉凛然,一时无话。
独臂将军看着他,忽然将乌鞘长剑向面前的泥土里一插,屈下一膝半跪了下来。
“赵国‘黑衣’统领赵宸,曾夜入秦营,刺伤武安君白起。如今赵国全军已降,但以在下头颅请罪,愿冯将军、力保我军降卒不死。”
他声音并不洪亮,甚至十分地虚弱,然而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毫无闪烁。
冯嘉只觉震撼至甚,直愣愣地刺到了他心底最深处。
虽然之前也有耳闻赵营已“人相食”,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会有将领愿意以存活之身割肉飨士。
看着赵宸,冯嘉毫不怀疑,如果秦军受降之后仍然不分拨军粮给赵军,他便会把自己浑身的血肉统统割尽!
“冯将军,请动手。”赵宸缓缓抬起头,伸手将剑柄向冯嘉推了过去。
冯嘉与那目光一触,猛地向后退了一步。
出发来赵营之前,他又探望了一次老师的伤势。虽然在众将之前,老师还维持着常态,可独对他时,他分明感觉到老师的情绪与以往完全不同。
“到了赵营,若找到那刺客,务必提头回来!”老师说这句话时,扶着军案的手都在颤抖,指甲敲着木头咯咯作响。
冯嘉自然答应了。可如今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英雄——他如何能忍心杀他!
“冯将军在害怕?”赵宸见他不动,忽而勾了下嘴角,露出点讽刺的意味。
冯嘉一皱眉,伸手将那柄剑一把夺了过来。
“我怕什么?”他鼻中轻轻“哼”了一下,抬起目光环视了一下四周,“降卒不杀,乃军争大道。还用得着你说?”
听到这句,赵宸微微蹙起眉,嘴角隐去了所有的讽意。
“我今次只是来收缴兵器。行刺之罪,待我回禀武安君之后另算。”冯嘉伸出手指,在长剑的剑鞘上磕了一下,“你营中可还藏有其他兵器?”
赵宸怔愣了一下,继而摇了摇头。
“那便退回休憩,约束部下,等待我军收编。”冯嘉抛下一句,拿着乌鞘长剑,转身便带着部下离开了。
二更时,冯嘉回到了中军大帐。白起刚刚换完伤药,正靠着军案闭目养神。
“老师。”冯嘉上前跪坐,将乌鞘长剑呈上了案头。
“刺客之剑?”白起睁开眼,缓缓问道。
“是。”冯嘉抿了下唇,“乃是赵国黑衣统领,名叫赵宸。‘有为剑’赵崧之子。”
“怪不得。”白起又闭起了眼,“杀了么?”
“尚未。”冯嘉低声叹了口气,“不过他武艺已经全废,逃不了。”
“妇人之仁。”白起面上的怒气忽然一盛,过了片刻,又长长叹了口气,语气里尽是失望,“靖长啊靖长,你何时才能真正担当大任!”
冯嘉咬紧牙关,没有说话。
白起看他不答,又兀自摇了摇头,不再言语。只是他手臂仍在不住颤抖,仿佛痉挛似的,带得铁甲摩擦,吱吱作响。
“老师……是觉得冷?”冯嘉皱眉,觉得纳罕。
他从来没有见过白起受伤,也从来没见过白起精力不济到连发怒都省去。在他的预想中,没有遵令把刺客的脑袋带回来,怎么也会领一顿杖责的。
白起又叹了口气,闭着眼,没有理他。
又过了良久,冯嘉只得低头道:“学生知错。明日学生再去,亲自取他头颅。”他抿了抿嘴,“只不知,赵军二十万战俘,该如何处置?”
“你意如何?”白起硬邦邦一句反问。
冯嘉攥紧拳头,略带磕巴地缓声道:“最佳……当然是……能收编入我军。”
“收编?”白起不以为意地轻哼了一声,“我军锐士如何选拔,你自是清楚得很。这么一大帮敌国之兵,聚在一起唯恐哗变生乱,分散了,却又如何混编?”
冯嘉咬紧嘴唇,没有言语。他其实又如何不知?
长平之战一打就是三年,赵国固然大败,战死了三十万人,秦国却也损失了二十余万,几乎是一命换一命。军中国中,人人结仇。这样的两支仇敌,怎么可能混编为一?
“那么……统统送去陇西之地做苦役,戍守边关,抵御戎狄。”冯嘉捏着拳,轻轻一敲桌案。
白起听完,叹了口气:“太远。”他摇了摇头,“以赵俘伤情,只怕没走到一半,就死得差不多了。更何况,粮草如何置办运送?我军前线尚且不充裕,如何有分来向后送的道理?”
“那秦王和应侯是何意思?”冯嘉陡然急了,心中涌起一股说不上来的不好预感。
“我已经发紧急国书,派蒙骜回去问了。”白起又重重叹了口气,“先等几日再说吧。”
冯嘉黯然,却也知道再无其他办法。
白起疲惫地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回去了。
冯嘉长长吁出一口气,行了个军礼,起身准备退出。
出帐门的一瞬,他突然听到白起沉声道:“想去赵营送衣食便去吧,我军既然受降,俘虏衣食本应承担。度量自己拿捏。”
“是!”冯嘉立即朗声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