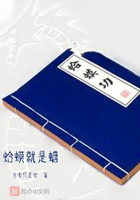“给我把门打开!”
一声远远的吼声,突然像斧子砍透冰层,把赵宁从深沉的睡梦中拽了出来。
她轻轻一动,剧烈的痛楚和干燥的喉管让她猛地睁开眼,然后发现,自己整个人都沉浸在黑暗之中。
这是什么地方?
她又动了一下,发觉自己似乎是躺在柔软的床榻上。
周围并非完全的黑暗,只是罩着帘幕,遮绝了房间外面的光线。
“水。”她用尽全力,从干痛的嗓子里挤出一个字。
“阿宁。”
左边的身侧,突然有人一动,抓紧了一直握在她腕上的手,把身子靠了过来。
那声音低沉又嘶哑。
确是熟悉的。
赵宁费力地慢慢转过头来。
“我给你拿水。”
还未看清楚,他已松开了手,快速地从榻上起身,大步走了开去。
门外的动静越来越大,有人风风火火地往他们所在的房间冲过来,一面走一面大声吼着:“冯嘉!你给我出来!”
赵宁努力挪动身子,想坐起来。却发现浑身上下一丝力量也没有,尤其是右边的胳膊,仿佛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
“来。”
他把胳膊伸到她颈后,把她的身子托了起来,头靠在他的肩窝上。
甘甜的水滋润唇角,顺着喉管流下去。
一瞬间,赵宁感觉鼻尖一痛,眼泪马上涌了上来,模糊了视线。
是他啊。
她没死。
是他回来救她了。
屠嘉没有说话,只是喂她把整碗水喝下,然后把空碗放在一边,抬手理了一下她的额发。
“砰砰砰——”剧烈的敲门声响起。
“冯嘉!开门!”粗重的男声愤怒地吼道。
屠嘉恍若未闻,只叹了口气,低着头轻声问她:“饿吗?”
赵宁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我们……在哪里?”
她的额头贴着屠嘉颈侧的皮肤,温暖熨帖。
“在咸阳。”
他轻声道,语气里无悲无喜。
“冯嘉!你躲着有什么用!你还是个人吗!”门外的人得不到回答,怒气愈盛,疯狂地拍打着门板,“明日珊妹下葬,你也不去吗!开门!”
赵宁眉心陡然一蹙。
下葬?
她感觉到,屠嘉的身子也明显颤抖了一下。
“咣”的一声,门栓终于被震断,灯火和人声猛地灌了进来。
一个魁梧的中年男人气冲冲地走到床榻前,一伸手就扒住了屠嘉的肩膀,想把他的身子拨转过来。
可这一拨,却没有拨动。
“靖长!”那人惊诧地瞪大了眼,更加气急败坏,“你到底想如何!”
赵宁身体仍还虚弱酥软,被这突然闯来的大声一炸,头又有些发晕。她只看见,屠嘉脸侧的线条一硬,咬紧了牙关。
“靖长!我真是不懂!你怎么就被这妖女迷了心窍呢!”那人气得发疯,吼声震瓦,“白珊可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比亲妹妹还亲!她因这妖女自杀,你竟忍心一眼都不看她,还天天抱着这妖女卿卿我我!你说!你还有良心吗!”
屠嘉依旧咬着牙关没有说话。
赵宁这才听明白了事情缘由,一时心中大震。
“屠嘉,你……”她挣扎了一下,想推开他。
谁知屠嘉却手臂加力,把她更紧地箍住,低声道出几字:“你别管。”
赵宁怔愣住,只觉他胸膛上热得发烫,心跳也砰砰作响,箍着她的力道大得像要把她的骨头捏碎,不由轻轻痛呼了一声。
屠嘉并没有听到,也没有松开。他浑身肌肉绷紧,仿佛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抵抗那个男人刺耳的唾骂上。
赵宁这才发觉,屠嘉呼出的气息里带着浓浓的酒味。整个房间里,都飘着这种味道,绝望又颓靡。
“你、你……”那男人气得说不出话来,指着他骂道,“我司马靳真是看错你了!我就不该答应让你住在我这儿!”
屠嘉长长地吸了口气,侧过头,忽从床榻边拉出了一柄长剑,慢慢横举了起来。
“奉明。你不如——就在这,把我们两个都杀了。”
他的语气冷肃得可怕,半点不是玩笑。
司马靳向后退了一步,怔愣了一下,然后更加大声地吼起来:“冯嘉!你别逼人太甚!”
“我没有玩笑。”屠嘉看着他,眼神如受伤的孤狼,“这是最好的选择。”
司马靳怔怔地看着他,僵持了半天,终于“唉”地一声,软了下来。
“靖长,我知道你心里也难过得很,可是……可是这事情,真的……也不能就这么拖下去啊!”
他语气里满是烦乱,在屋子里来回乱转,找了个矮榻一屁股坐了下来。
“大家都知道你回咸阳了,武安君府里更是清楚得紧。当时军中发生的事,目击者那么多,我们根本没法封锁消息!现在白珊出殡,你却不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吧!就算嬴栎和王孙拼了命护你,也挡不住众口铄金啊!
“唉!我知道你从前一直不肯向武安君求亲,是对白珊没那个意思。可是她对你一往情深,你又怎能这般残忍,就是视如不见呢?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妹妹,你也不能不去吧?白夫人也病倒了,你让她怎么想?这些伴你长大的亲人,哪一个比不上这妖女?你怎么就想不通呢!”
司马靳兀自絮絮叨叨,捶胸顿足。看见案上有水,便自己倒了一碗。
喝进口中才发现是药,又“呸”地一口吐掉,气得把碗碟摔得叮当作响。
赵宁身体太虚,听没到几句,只觉眼前金星乱冒,意识又沉了下去。
屠嘉叹了口气,把她又放回了榻上平躺,小心地掖好被角,才转回身来。
“我若去了,你能保她平安吗?”他沉声道。
“什么?”司马靳愣了一下,然后又破口大骂,“保她平安?我第一个就要一刀杀了她!那嬴栎也是荒唐,凭什么给刺客请什么特赦!要我说,你就该亲手杀了她,提着头回去给白夫人请罪!”
屠嘉惨然冷笑了下,手一伸,又从床榻边不知什么地方捞出来个酒坛。
“你看,我终是无路可走。”他意兴阑珊,仰头灌下一口酒。
“怎么就无路了?我不是都说清楚了吗!”司马靳还在纠缠。
屠嘉摇摇头,一句都不想再说了。
这世上,从来没有、也再不会有一个人理解他的坚持。
这是咸阳,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人人都认为,他应该好好地做“那个人”,做武安君的得意门生,做武安君的女婿,做继承武安君一统天下的志向的年轻将星。
而现在,事情闹到如此无可收拾的地步,他们还是认为——他只是一时被一个“妖女”迷惑住了,只要浪子回头,一切都还可以转圜。
可他们不知道,赵宁,并不是什么妖女。
在找到她之前,他已经犯过太多的错,杀过太多的人。
他所学的所有本事,所想的事情,都是如何去杀更多的人,来为自己赢得荣耀和升迁。
而在这一切寄望,被长平杀降的雷声击得粉碎之后,是赵宁让他知道,他活着,还是有别的意义的。
他得保护她。
他要她活下去。
他不能让这个乱世把她杀死。
她是他生而为人的——最后的一道界碑。
司马靳不是不明白,只要他离开她身边一刻,她就会立刻死去。
虽然嬴栎为了保他,向秦王给赵宁请来了一个特赦。可白起在咸阳的根系庞杂,随便一个大夫官卿,都有成百上千的门客死士。此时,每一个得知此事的死士,大概都在磨着刀,等着为武安君惨死的女儿出一口气。
司马靳也很清楚,他不可能带着赵宁去给白珊送葬。他无论如何,都无法面对白氏的养育之恩。
所以,他就是来逼他放弃的。
如他所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在此处,与她同死。
屠嘉摇摇头,苦笑了下,又仰头喝了口酒。
当真,生此乱世——此生何必?
还不如做个蝼蚁,朝生暮死,只求一日欢尽。
“靖长!你就真的、不肯去?”司马靳还不死心,皱着眉再次相逼,“今天在朝堂上,王孙为了护你,可是连应侯都得罪了!”
屠嘉皱了皱眉。
“王上都召你两次了,你还不进宫去见。下一次,怕是直接要下诏狱了!”司马靳语气越说越急,忽地一拍大腿,“差点忘了这事!今日传来军报,邯郸军情有变!魏国大将晋鄙莫名死在了邺城,原本止住的十万魏军被信陵君夺了帅[16],又往邯郸进发了!
“魏国这一动,楚国怕也按捺不住了。邯郸赵军应也得了消息,士气大涨,攻城更加困难。王上听了大怒,又要求增军,下诏强起武安君挂帅,务必灭赵而归!倘若不出,则阖族夺爵,贬为士伍,迁之阴密!”
“什么?”屠嘉终于心神大震。
“唉!我跟你说过,武安君长平被刺之后,身体一直不见大好。回来之后三年,几乎就没上过朝!”司马靳叹道,“这已经是王上第三次下诏,让武安君领兵出征了。之前两次,他都托病不出,惹得王上甚是不快。
“这些年,应侯治国有道,甚得王上倚重。自从长平撤军后与武安君有隙,应侯着意在王上耳边言武安君的不是,暗中料理剪除武安君的根脉。其间种种龌龊,我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也是因此,我们才拼命找你回来。毕竟武安君幼子尚小,不能指望。若有个左更高爵的女婿在,怎样都好办些。唉!可是你——”
这句落,屠嘉心口如遭重击,只觉刚才喝下的酒全成了烈火,要从喉咙里呕出来。
战场杀伐,他已司空见惯。可朝堂倾轧,他却一听之下,便觉胆寒。
那才是真正可怖的人心鬼蜮。君王一念之间,荣辱俱灭,九族血竭。牵枝连蔓,株连无算,连毫无威胁的幼童,都要无辜惨死,暴尸荒野。
他忍不了赵宁被杀,就忍得了老师一家惨遭屠戮吗?
若真到了那一步,他又该怎么办?
“靖长,你还是好好想想,尽快回家去吧!”
司马靳看他痛苦地弯下腰,起身走过来,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
“时间真的不多了,别再让自己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