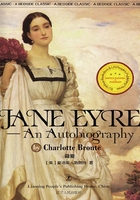夜已经很深了。
看着最后一艘渡船离开码头,邵云沿着墙根寻了半周,攀着一处枝藤轻巧地翻进了院子。
这是一座形制很大的客栈,名为“溱洧”。独门独院,建在大梁城西的逢泽湖中心的一座小岛上。
逢泽连通数条流经大梁的大沟大水,是魏国首屈一指的上古泽薮。虽比不上楚国云梦泽的一望无际,却也算是浩荡无涯。这小岛远离岸边,必须由渡船交通。方圆不大不小,正好容纳一座豪奢的园囿。
邵云也是第一次来,便循着院墙随意走走。天色虽早已黑透,但离他行动的时辰还早,正好摸摸地形。
这苑中有一座高楼,有三层,建在小岛地势最高的坡顶,可以俯瞰逢泽阔大的湖景。高楼一半是客房,一半用作宴饮。因为风景独具,掌勺的大厨又举世有名,素来热闹非凡,不愁生意。
楼下,依着山势还有供游人玩赏的亭台园林,飞瀑流水,半是自然奇景,半是人工雕饰,相互穿梭,浑然一体,甚是别致。景致延伸到水边,更有一片水榭楼台,围起了一小块内湖。湖里养着逢泽最出名的湖鲜,岸边圈了块地养着麋鹿,专供酒楼飨客。
邵云一边转悠,一边确认整座小岛上的人都已撤走,只剩高楼上还亮着两三盏灯火。
那个应侯夫人姬雨桥,确实是个聪明人。来到大梁,只两三次隐信往来,就与他接上了线,弄清楚了他的计划。
这座客栈“溱洧”是齐国“琅琊”设在魏国的据点,没有挂在田氏商社名下,伪装得十分隐秘,已经营了十多年,成了老魏国的一大“名胜”之地。
红楹应该想象不到,这白日里人流熙攘一位难求的酒楼,竟会在午夜后瞬间撤空,成为一处孤绝无援的死地。
姬雨桥这些天带着红楹在大梁城里城外地转悠,把所有著名的景点都玩了个遍。“溱洧”只是她计划中的一处,前日邵云还特别关照,让她第一次没能约到客位。这次终于约到了,便可顺理成章地跟红楹叫唤要在岛上多住一天。
方才客栈老板娘季璃撤走时,跟邵云大致说了说情况。当着红楹的面,姬雨桥跟她好一顿闲扯,问了逢泽其他的好去处,还托她帮忙定了第二日的船,浑不像知道今夜会有行动。而红楹全程无话,好像也不太上心,一直在神游。看样子,也没有怎么怀疑,十分容易铲除。
老板娘季璃十分不理解邵云的要求。如今整座岛上,只有楼上留了个专为她们那间房听召的小厮,其他人统统撤走。在老板娘看来,那个柔婉沉默的姑娘,就算武艺再高,也不至于要这么折腾,害他们半夜出来吹冷风。
但她再要啰嗦,邵云却锁着眉头,冷冰冰地拿出“琅琊”令,几乎要拍在她脸上。
现在已过子时,主楼上的最后一盏灯火终于灭了。邵云吸了一下鼻子,调转方向,开始向坡顶上走。
背后的长弓随着步伐一下一下敲在他脊梁上,平白生了一点冷意——好像冥冥中有什么东西正在他的心口上叩击,没有道理,也不知原因。
但他清楚自己为什么执意要全部人都离开。
假如跟着姬雨桥的人是静渊,他大概都懒得亲自动手——交代老板娘一声,翌日过来带人就行,连尸体都不用他处理。
可来的人是红楹。
他不确定,自己面对红楹,会出什么问题。
可他也不能容忍,让其他人来代他做这个决定。
虽然,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虽然除了田牧,也没有旁人知道他和红楹有过什么关系。
虽然——连他自己都不承认她对他来说有多特别。
但仔细想想,今夜,大概真的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所有的情与仇,都会在这茫茫的大湖边有个了断,从此再无以后。
邵云叹了口气,很难得地感觉到——有些伤感。他不是个很念旧的人,这十年来,也很少会想起她。
他也不是没有过其他的女人,比她更美、更媚、更让他感到欢愉的不在少数,只是同样没有入过他的心。
可如今,站在那漆黑的高楼下,月光如白雪一样铺在檐角的瓦片上,裹着湖泽水汽的风丝丝缕缕地吹过来,钻进他的脖子里,他突然感觉到一阵难过从心底泛上来,让他迫切地想要拥抱什么东西,或是一个人。
“云韶。”
就在这时,一个柔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邵云霍地转身,看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体孤峭地立在月光里,手腕上缠着蛇一样的长鞭。
“师姐!”他讶然扬眉。
红楹看着他,长长地吸了口气。月光照在她的眉梢和鼻尖,投下清淡的阴影。
“不必多说了。其实,从刚踏上岛时,我就明白了。”红楹淡淡地道,“但我还是留了下来。因为,这里不仅是我的死地,也是——你的死地。”
话语一字字落下,那赤藤索动了起来,像是一条毒蛇,忽然在她腕上苏醒。
“哎呀——”
高楼顶层的一间客房里,姬雨桥正吃着果子,突然听到声响,赶忙冲到窗台边往下看。
今夜的月光不算明亮,楼下黑洞洞的,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不过,打斗声还是越来越清晰,瓦片碎裂声此起彼伏,越来越往楼上靠近。
一个时辰前,红楹离开了房间,喊来小厮,把她从外面反锁在了屋内。
她知道她是觉察了,于是便没有反抗。
她很清楚,在秦国,这些由秦王直统的“萤火”是有很大的权限的——如果查知了有重臣背叛,哪怕没有证据,先斩后奏也是惯常做法。因为,整个“萤火”组织里一共也没有几人,里面全是秦国最忠诚的死士。其选拔过程之严苛,让所有知道这个组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必定值得信任。
这本来也是姬雨桥一直以来最害怕的。
她其实很明白,自己这一路不论怎么欺负红楹,红楹都不会对她怎么样的——她是她的守卫,护着她毫发无损地回到秦国,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
可是,一旦她察觉她的背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姬雨桥觉得,红楹一定会不发一语地对她背后来一刀,然后舒畅至极地呼上一口气,冷笑着看着她死去。
然而,实际的情形却出乎了她的意料。
红楹竟然就这么锁门走了,并且似乎以为她不会武功,破不开门,会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呆着等她回来。
“喂!师姐!”这时,邵云贱兮兮的呼喝声从楼下传来,“好歹这么多年没见了,不好好说句话吗?上来就打,白睡了那么多次觉了诶!”
姬雨桥听得一惊,果子都从张大的嘴边掉了下来。
红楹没有回答,呼呼的鞭声更急了,把檐上的瓦片抽得支离破碎,噼噼啪啪地往下落。
又过了一会儿,邵云突然一声惊呼:“师姐!你疯了!”
接着,针锋相对的打斗声消失了,只剩下一根长鞭的呼啸,一下、一下徒劳地抽打着高楼的废墟。
邵云死了?姬雨桥心里一惊。
不会吧——他的实力明明比红楹高上甚多——除非他是……真的忍不下心下手。
那可不行!姬雨桥想。
她搓了搓手,把黏糊糊的果汁在窗木上蹭掉,然后摸了一下怀里的刀刃,一个纵身,从窗口跳了出去。
外面是一圈窄窄的屋檐,虽然洒着月光,但还是黑漆漆的,看起来不太安全。
不管了。
她深吸了口气,抬起手保持平衡,踩着瓦片飞快地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