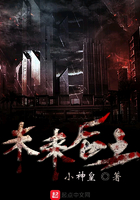才刚过午,薄薄的日头就隐去了。吕氏甲兵铺的陈掌柜还没来得及叹口气,冰寒料峭的冻雨又淅沥沥地洒了下来。
他放下刻刀,把竹简上的碎屑在桌边磕落,然后悉心卷起扎好,放进匣中。接着端起手边茶盏,将杯底剩茶一口饮尽,准备起身活动活动。
然而,屁股才刚刚挪开一隙,便有两位客人冒着淋淋的细雨踏进屋来。
“哟,客官辛苦。进来坐!”陈掌柜站起招呼,顺带将两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锦衣高冠,面容俊秀至极,两道峻眉浓黑爽利;女的高挑纤细,斗篷垂纱遮住了容颜。
“阿鲁,上茶来,有客人!”陈掌柜冲着内室喊了一声,转头将客人引上坐榻。
“多谢掌柜的。”男子礼貌地拱手作揖,继而广袖一摆,在长几边端正地跪坐下来。
女子却没有吭声,手臂一抬,掀起了斗篷。
陈掌柜转头一看,竟突然被惊得心头突突一跳。
这女子十八九岁年纪,也穿了一身游侠似的男装,把头发高高束起。她全然不施脂粉,皮肤不甚白皙不说,颈侧还有些仿若烧伤的疤痕,甚是可怖。不过五官倒生得俊挺,高鼻深目,瞳仁乌金璀璨,略有几分胡人形容。
——也不是什么倾城国色,也不至多么丑怪可怖。但陈掌柜没由来便觉得这女子身上别样的气息,让他有些不敢直视。
像是刚刚发硎的剑,一触就要割伤流血。
陈掌柜想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清了清嗓子道:“客人辛苦。等茶水上来了,润润喉再说。”
两人依言坐下,理好衣袂。陈掌柜这才注意到,这女子手中还握着一柄苍青色的古剑。那年轻男子倒是空着一双手,右手拇指上套着一枚浓绿的翠玉戒,一看便知价值连城。
不一会儿,小厮阿鲁便将陶壶茶杯送了上来,笑着行了个礼,退在掌柜身后垂手候着。
“两位从何处来啊?”陈掌柜一边斟茶一边笑问道。
“齐国。”年轻男子拱了拱手,“在下田牧。听说陈掌柜这里有出身墨家的工师,极善做剑器弓弩?”
“噢,确是如此。”陈掌柜笑道,“先生要做什么?数量几多?何时交货?”
“这位工师姓甚名甚?可否请他出来一叙?”田牧不答反问。
陈掌柜微微一愣,捻了捻胡须:“倒也可以。”他点点头,转头道,“阿鲁,去请梁工师过来!”
“好。”阿鲁应道,立刻向里屋行去。
“梁工师师从相里氏之墨,来我吕氏甲兵铺已有八年。”陈掌柜介绍道,“戈戟矛殳,刀剑弓弩,他是样样精通。在郢都,嘿嘿,绝找不出第二人!”
田牧温然一笑:“相里氏之墨啊!那敢情好。”
墨家自老墨子死后分裂为三派:邓陵氏之墨归附秦国,又称“南墨”,所出器械工师、学界名仕和技击高手大多均为秦国所用,不做他想;相里氏之墨迁居北上,总院设在齐鲁一带的山中;最后一支散入江湖,神秘难测,可能已经失传,被笼统归称为“隐墨”。三支之中,唯有相里氏之墨依然声名赫赫、传承繁荣。由钜子骆无尘直领修武立学的内院弟子人数虽然不多,从事机械工技的外院弟子却是遍布天下。
不一刻,里屋的帘子忽然轻轻一响。一个身材高大、红光满面的中年男子稳步走了进来。
“掌柜的,找我?”他一面说着,一面扫视了一下两位客人,微微颔首作礼。他的目光落在赵宁身上,也明显地一震。
“这位便是我吕氏的首座制兵工师梁大武。”陈掌柜起身介绍道。
“齐人田牧,叨扰了。”田牧起身行礼,音调不卑不亢。
“不敢,不敢。”梁大武连连拱手,“二位有何要求,但说无妨。”
田牧笑笑,示意几人坐下详谈。梁大武行了个礼,跪坐在了赵宁对面。目光与她一触,立刻闪避开来。
赵宁转头与田牧交换了一下目光,田牧笑笑,示意让赵宁先说。
“不知梁工师对青铜剑器是否在行?”赵宁手臂轻抬,将那柄苍青色的长剑搁上了台面。
梁大武眼神陡然直了,看着那按在古朴的剑身上修长的手指,暗暗咽了下喉。
“请借一观。”他沉声道。
赵宁抬起手,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梁大武双手捧剑,一寸、一寸地拉开剑鞘,冰凉的水汽霎时迎面扑来。
剑身也是苍青色的,凝神细看,顺着剑锋方向,一条条细密晶莹的墨线直直延伸开去,直抵剑尖。然而若是远观,便只有一片深邃而隐秘的暗芒,仿若古井之波。
只是可惜,靠近剑格处的锷上崩裂了几个小口,蔓延出数道极细的纹。
“真是口上好古剑。”梁大武叹道,将剑身推回了剑鞘,脸上的表情甚是落寞,“只是可惜,咱坊里早已在用精铁制兵,这等铜料,还当真没有。”
他将长剑放回案上,满脸都是憾色,却也让人无话可说。
“那便罢了吧。”赵宁叹了口气,垂下头,抬手拿剑。
“阿宁。”田牧将她手腕一按,“青螭宝剑确不是寻常人能修的,要看机缘。郢都乃工匠之都,藏龙卧虎,定能找到合适的人,暂且莫急。”
“嗯,我明白。”赵宁点了下头,气息冲撞,不妨皱起眉头轻咳了几声。
“我还有一事要问梁工师。这屋里气闷,你若不舒服,可到外面等我片刻。”田牧顿了顿,续道,“或者,我唤人来接你,先回商社。”
“不用麻烦。”赵宁站起身来,“我就在院里随意走走。”
看着赵宁的身影消失在门外,田牧转头看向梁大武,问道:“不知梁工师是否做过连弩?”
“这个,自是做过。”梁大武点点头,“蹶张、臂张,三、四连发,都不成问题,看先生作何用途。”
“那么,七连发呢?”田牧道。他一面说,一面从袖中取出了一卷柔软的羊皮纸,在案上小心地摊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