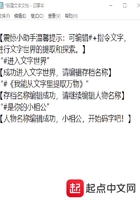大雪狂落。寂静的山林间,飞鸟绝迹,走兽隐匿。
本是在家围着炉火窝冬的时节,却有一个马队在无边的雪野上向着南方慢慢行进着。
领头的是一个身穿绛色皮甲、背负犀角长弓的青年男子。本是平常时候,他嘴角却微微上挑,狭长的眼中精光闪烁,好似天生带着一股戏谑和警觉。
在他后面紧跟着的是两辆双马轺车。前一辆形制略小,厢壁纹样古朴,却有些陈旧了。后一辆却是宽大稳重,崭新亮丽,两匹马也是高大的胡马,毛色漂亮得紧。
再后面是七八辆辎重货车,约有二十几个带着兵刃的民夫骑着马左右押送,一步步走得甚是小心。
忽然,那宽大轺车的门帘一动,一个眉梢柔美的年轻女子探了小半截身子出来。
“停车!喂——邵云,过来!”她冲着队伍的前端一边招手一边高声喊道。
领头的负弓男子闻声,兜转马头,向轺车慢慢靠了过来。
“怎么?”他在车辕边勒住马,从掀起的门帘缝中斜斜睨了一下车厢里。
“去告诉少东,她醒了。”年轻女子下巴向车里轻轻点了一下。
那名叫邵云的负弓男子眉梢一挑,没说一句话便打马向前一辆轺车走去。
片刻后,轺车停住,门帘一动,稳步走下来一个青衣白袍的年轻男子。
赵宁迷迷糊糊间,感觉有人用手搭了一下她的额头,又掖了掖她的被角。
车厢里烧着暖炉,略有一些气闷。她忍不住轻轻咳嗽了几声,忽觉胸腹间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刺得她立刻清醒了过来。
原来……没死吗?浑身都是刺到骨髓里的疼,真真切切,毫不含糊。
“哎,你醒了。”略带惊喜的男子嗓音在耳边响起——那声音清朗温润,犹如玉击。
赵宁猛然睁开眼,只见一个乌发冠玉的年轻男子端正跪坐在自己的右手边,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而她那一身血污的胡服已被换成了干净柔软的深衣,伤处都被仔细包扎好了,断骨处也绷上了夹板。
“你是何人?”赵宁挣扎想要坐起。然而刚一用力,浑身又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霎时激出一身冷汗。
“哎,姑娘[2]莫动!”男子急急直起身,抬手按住了她的胳膊,“躺着说就好。”
赵宁蹙眉,依言不再挪动。仔细打量,只见他皮肤莹白,五官端正,俊眉修目,一双手尤其修长漂亮,右手上戴着一枚翠玉戒,显是出自名门士族。
“在下田牧,来自齐国即墨。”男子微微一笑,抬起手臂恭恭敬敬地比了个拱手礼,“幸会。”
赵宁僵硬地动了一下脖颈点了个头。
“姑娘感觉如何?车马颠簸,可消受得了?”田牧见赵宁不接话,又再问道。
“无碍。”赵宁也勉强勾了勾嘴角,“你们是?”
“噢,我等乃是齐商。”田牧道,“齐国田氏商社,在下正是少东。”
赵宁不由皱起了眉。
过了一会儿,她才想清楚那日的情形。
就在她以为生路已绝之时,不知从何处竟忽然杀出了一队人马。为首之人箭法超绝,世所罕见,竟以一箭横截,生生挡开了射向她的七八支铁箭。继而包围圈被撕开,一队武士持着剑盾杀入,硬生生从飞箭铁流中将她抢了出来。
这样的一路神出鬼没的人马,怎会是商队?更何况,邯郸此时正被秦国大军铁桶一般围着。一支商队,又能有什么理由来冲杀秦军?
赵宁心中突的一下,手不自觉去摸剑,却摸了个空。
“我剑呢?”她立时冷下了脸,咬牙撑身坐起。
“当心。”田牧立刻伸手去扶,脸上神色关切。
赵宁侧身一避,直视田牧的眸子里精光忽绽。田牧与她目光相接,却不像旁人那般慌忙躲开,只微微笑了笑,从身后托出一柄苍青色的青铜剑,双手呈了上去。
“在此。”他面上忽然露出一丝遗憾,“只是……剑上有一些……磕损了。”
赵宁接过剑,“嚓”地拉开,眉心陡然一皱,眼中流露出几分心疼。剑脊靠近护手的地方果然被磕出了几处小口,虽不严重,却有些明显。
“姑娘是赵国人?怎么竟会独身一人深入秦营刺杀主将?”田牧问道。
“我要进城,这个方法最快。”赵宁不肯多说,抬起眼,“你们又为何会来邯郸?”
“噢。”田牧又笑了笑,从怀中摸出来一个锦囊,里面似乎装着个沉甸甸的圆筒,“方才没说完。我族叔,乃是如今赵国主持守城的外相——安平君田单。”
这句落,赵宁微微吃了一惊。
田单本是齐国名臣,三十年前齐国被燕国上将乐毅连攻七十余城,险些国灭。正是田单坚守即墨孤城数载,最后以火牛阵破围,一举复国。
可惜这位名臣在新王登基后屡受排挤,愤然出走。之后便入赵,做了相国,还为赵国攻下了几座燕国的小城。如今有他主持邯郸守城大局,倒也令人有些微宽心。
“我日前收到族叔飞鸽传讯,命我带人在邯郸城外某处,寻找一件密函。”田牧一面续道,一面把那锦囊拆开,“便是这个。不知赵姑娘是否知道,该如何打开?”
一个精巧的金属圆筒出现在赵宁面前。
“‘黑衣[3]’密令!”赵宁猛地被刺了一下,脱口而出。继而脑中电转,厉声道:“你怎知我姓赵!”
“唉——”田牧似是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愣了一下又赶忙笑着安抚,“姑娘别急啊!田氏与赵国同仇敌忾,绝不会害你!”
赵宁也顿时觉自己反应有些大了,脸上红了一红,有些羞赧。
这齐国商队拼死救她,自然不会要害她——虽然不知怎地,她一见这看去风姿超拔的商客,就直觉有些不对。
“你吓唬王陵的那一剑,不是赵国‘黑衣’统领赵崧的绝技’猎风’吗?除了自己女儿,应该也不舍得传给别人吧?”忽然,一个懒洋洋的年轻男子嗓音在车窗外响起,语气里满是戏谑,“还以为当真一击必杀呢,原来,也不过如此嘛。”
赵宁心头又狠狠一震,胸中一股热血霎时涌到顶心。
“诶,邵云,休要无礼。”田牧眉心一皱,转头叱责。
只听窗外的人“哈哈”一笑,竟扬鞭打马,一句话不说便向队伍前方远去了。
赵宁咬着嘴唇,强忍着浑身火燎般的痛楚,心头情绪翻涌。
那个人应当便是当日一箭破围把她救出来的卓绝弓手。方才他一直跟在轺车旁边,她竟是丝毫未有察觉。
“抱歉,邵云是我的护卫,粗野武人,不知礼数。姑娘莫怪。”
赵宁轻轻“嗯”了一下,深吸了口气。
“在下赵宁,多谢相救。”她从田牧手上拿过铜管,看也不看,手指一挫一拉,“喀”地一声便打开了,“我跟赵国‘黑衣’没什么关系,也不知城中情况。你们要做什么,自去做,不必问我。”
她把铜管丢回田牧手上,扭过头去,对里面的东西分毫不感兴趣。
田牧慌忙接住,想说什么,却无法开口,只得叹了口气,兀自低头把铜管里的绢帛取出来,就着窗口透进来的光看。
绢帛有两张,质地不同。一张大的略微硬挺,竟是当世极其少见的羊皮纸。小的便是士人写字常用的绢帛,却空空荡荡地只写了寥寥数语。
田牧看了好一会儿,深了口气又吁出来,把那羊皮纸又细细卷好,又放了回去。绢帛对折了一下,放在膝头。
“赵姑娘,你可知道,为了救你出来,田氏商社折损了多少人手?”田牧脸上的神色难得如此冰冷严肃。
赵宁皱着眉,沉吟良久,转回脸来,道了句:“抱歉。”
田牧忽又叹了口气,有些后悔似的笑了笑:“唉!田某失言。即墨田氏一族立誓追随安平君,救赵抗秦,死不旋踵。又怎能把牺牲,怪罪到赵姑娘身上?”
赵宁又沉吟了片刻,低声道:“不论为谁,总是为赵国。赵宁……多谢先生。”
田牧摇了摇头,露出一抹苦笑,抬起眉梢转了话题:“如今入不了城,赵姑娘打算去何地?”
赵宁摇摇头:“我还是要回去邯郸。先生若是方便,就在前面的城邑把我放下来吧。”
“这怎么可以?”田牧皱起眉,“姑娘受了四处箭伤,断了两根肋骨,必须卧床休息。实不相瞒,你已昏迷了两个昼夜了。而直到今天早上,我们才甩脱秦国的追兵,进入魏国。”
赵宁一时没有说话。
她知道田牧说的是实情。这一场刺杀闹的动静太大,此时消息大约已传回咸阳了。而那个叫做“萤火”的组织,必定会从此如同跗骨之蛆,与她不死不休。
“或者,姑娘先跟我们去陈城?陈城乃工匠之都,正好,也可找家甲兵铺给你修缮一下宝剑。”田牧道,忽而一扶额,“噢,倒忘了,那里早已是叫郢都了。”
“去楚国?”赵宁皱起眉。
二十二年前鄢郢之战,秦国战神白起拔郢都、烧夷陵。楚顷襄王一路东逃,迁都于陈,更名郢都。那座矗立于颍水之畔的古老城邑,一直是地处中原边缘的最为繁华的商旅都会。楚国法不料民,对所有人口皆不盘查,只要有一技之长,便能留下生存。故而陈城汇聚了七国能人巧匠和江湖草莽,对于现在的他们,倒确是一个好去处。
“怎样?”田牧有些着急,追问道。
赵宁抬起头,直直看着他的眼。那双俊秀明净的凤眼却是清朗坦荡,看不出丝毫藏掖。
“我只怕、会拖累你们。”过了一会儿,赵宁轻轻叹了口气。
田牧皱起眉,神情表露出些许责备。刚想说话,却又被赵宁打断。
“我答应为你们做一件力所能及之事,以报救命之恩。”她定定说道,“一年为限。”
田牧一听,哑然失笑,摇了摇头。略想一下,刚欲开口,又被赵宁抢白:“请先生想好再说。”
田牧这才正色,敛起了笑容。
直过了有一刻时间,田牧才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襟。他将膝上的绢帛拿在手上,挺身长跪,对着赵宁缓缓展开了那份密函。
“既然如此,田牧,便请赵姑娘,加入我们的计划。”
赵宁凝起眉,细看那张绢帛上的字。
字写得很稀疏,是齐国的文字,有些潦草。但最后的两字却写得很大,笔锋犀利,气势滂沱。
——弑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