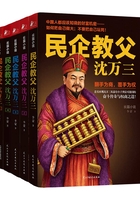“桑”第一份生意的后半段,波澜不惊地结束。原本定好由阿桑担任主持的追悼会,为了不再出现意外,(你们都知道,也就是说为了避免阿桑再与家属吵架)被青姐临时代替。于是一切按照流程,索然无味地结束。
“我活着的一辈子都泛善可陈,葬礼也果然如此无聊啊。”
俞聪再次感觉到亡者的质问。
“这就是你想做的事吗?”亡者冷笑了一下,像是卸下了所有重担,飘飘然而去。
“这是我想做的事吗?”俞聪却不能卸下重担,这个问题成为他此后最大的人生难题。
“这就是你想做的事吗?”阿桑问他。
“这就是你们想做的事吗?”阿桑转过头问我们大家。在葬礼结束后,大家进城在啤酒屋的聚餐上。不知阿桑是没从那位43岁女性亡者的葬礼中解脱出来,还是喝得有些多了似地问我们。
小可望向俞聪,齐骥将埋在胸前的头埋得更深仿佛落入宇宙黑洞,青姐早已离席回家,我在忙着观察每个人。没有人回答她。
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暇考虑这个难题,一次葬礼并没能改变“桑”,这个突然出现在A市偏远位置的初创殡仪馆的窘境。我们照旧没生意做,百无聊赖。
十月份,像你能预料的那样,A市的气候扔保持在夏天的样子。完全不是适合遗体保存的温度,这城市简直可以算是殡仪业的噩梦。
“好,行,知道了。”阿桑接到来自C君的电话,就是我们唯一经手的那个葬礼上,亡者的丈夫,C君。阿桑只说了五个字的这通电话,我们当时还未能料到,会成为“桑”殡仪馆以后的基石。
C君没有介怀阿桑在葬礼上的挑战,或者说,说不定他更多地认可了阿桑的意见,所以将“桑”介绍给了其他的朋友。
周文槐,1970.10.22–2017.10.23,47岁卒。
死因定性为他晚上喝酒回到家,由于喝到手脚麻木,怎么都打不开门。于是像是呕气似的,大力去推拽进户门,结果一次推拽时,门打开了,他闪了空,朝后边倒下去,头撞在路边石头上。当场死亡。
人,出生的方式大概相似,死亡的方式却千差万别。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活着的人类,却并不知道厄运会在何时降临。
上山来到“桑”点名要跟阿桑聊一下周文槐葬礼事宜的家属,只有两名,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仅仅6岁的孩子,另一个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他的前妻D女士。
“远是远了一点,但我们也没多少人会来,这倒是不怕的。”D仔仔细细观察了“桑”每个角落后这样说。
“你是老板是吧?”
“我怎么会是老板呢,他才是老板。”阿桑指了指身旁的俞聪。
D隔着高度近视镜片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俞聪。
“你们是两口子啊?”
“不是不是,你是觉得这殡仪馆的名字是吧?没关系的,这只是个巧合,他都注册完了才认识我的。”上一次丧仪结束后,阿桑又恢复到了我们认识的阿桑。爽朗,与人为善,知心姐姐。
老齐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片叫《热带雨林的爆笑生活》,那里头的主角阿布拥有换脸的神技,哭丧着的脸和笑逐颜开的脸完全是两个人。阿桑也根本就是具备这种“特异功能”!
“我前夫,是个不得志的文人。一心认为自己能成为大文豪大作家,但其实除了给报纸写写豆腐块儿,一个字都没出版过。”
D说到这里,我的同事们,齐刷刷看了我一眼。我只能回敬他们一个大大的白眼。
“他父母都过世了,没留下多少钱,甚至都不够他日常生活。我呢,我是个种菜的,也赚不了什么钱,还得养着这儿子。我当时不知道怎么鬼迷心窍,嫁给了他。我嫁给他的时候他都过了四十岁了呀!好死不死还生了个儿子,我命苦啊……”
D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坐在她身边的阿桑紧紧握着她的手,感觉即将跟着掉眼泪。我却看到D边哭边觑着大家,像是演一场戏。
“我们不会降价。”青姐的口气不带感情,没有同情也没有厌烦,像是一个写好程序的机器,这样制止了D。
阿桑扭头嗔怪地看着青姐。青姐回以严厉的一瞥。于是阿桑把目光递送到俞聪那里,试图寻觅支持。
“真是难办呢,我们的价格确实不能商量。”俞聪甚至没有犹豫,就这样说到。青姐明显松了一口气,不再指手画脚,又摆出了她惯有的“事不关己”样子。“降价并不能换得家属对我们的尊重。”跟着俞聪去兜售服务的时候,他这句话我仍记得。
“呵,说起来,”D将手从阿桑手里抽出来,摆正坐姿,瞬间整理好了情绪,“谁会大老远把丧事放到你们这里办啊?公家的殡仪馆就有好几个,看着比你们这里靠谱多了是不是?要不是贪图能便宜些,你们哪有生意做啊。你们这个吧,”她翘起二郎腿,再看不到悲伤在哪里,“跟我们种菜的是一样的,那么多菜农,为什么进货上要从我这里进啊?我让利啊!你们还是刚开始做生意,太嫩,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不是卖菜,”这一次,是阿桑打断了她,
“我们不是卖菜,也不是卖棺材骨灰盒的。我们……我们可以提供独家定制的葬礼。”
“什么?”我几乎同D一起问出来。
“就是,嗯……我们会根据每一个死者的情况,和家属的要求,专门为他准备葬礼,我们不是做传统殡仪馆那种程式化的业务。”阿桑略有磕绊着,说出这样的话。
“独家定制?呵,然后骗家属花更多的钱吧?”D女士完全不买账。
“对,独家定制。也许可以帮您省钱。嗯…看你要的葬礼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一项的基础收费不能变。但是你可以选择。”
俞聪说出这番话的那一刻,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甚至包括他自己。却让“桑”往前走了一大步。
那天,D女士最终决定收到我们的葬礼企划后,再看后事交给哪一家殡仪馆。遂带着孩子下山了。
青姐首先表态说:“你们这种莫名其妙的决定,我可以配合,但我不参与策划。程序化自然有程序化的好处,最节省成本,你们这样,随便吧。”
俞聪同青姐周旋,一再承诺一定尊重青姐的专业性不做出格的事,才让青姐答应留下来跟我们一同完成这份第二天就要送达给家属的“葬礼企划书”,据青姐说是本市绝无仅有的企划。
因为青姐与阿桑观点的完全不同,这份企划书一直做到凌晨四点才结束。虽然不过短短两页纸。青姐要避免掉一切不必要麻烦的出发点,最终让渡了很大一部分给阿桑的“突发奇想”,这不仅因为老齐、小可我们三个完全赞同阿桑,更因为阿桑抛掷给她一个她没能回答的问题,阿桑说:“你真的打算把每一个葬礼,都做成冰冷人生里最冰冷的一站吗?”
上一秒还充满斗志的青姐,在那一刻安静下来,沉默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坐到座位上说“随便吧。”
没办法再睡了,我走到后花园时,看见阿桑躺在长椅上看星。中国很多城市看不到星,真是悲哀的事。宇宙浩渺,个人生活再不如意,只要抬头观星,便会觉得全部去似微尘。我的父亲曾对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当然,他是用英语,但翻译成中文似乎更有意境。
“阿桑,我发觉你真是一个很棒的人,你时不时会与平常的你不一样。比如今天,你就很棒。”
“今天?今天很多时候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为什么?”
“比如当我假意握着D的手,甚至还挤出眼泪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一个种菜的女人,可能误以为能唠到点好处嫁给了一个文化人,婚后发现没有任何好处就选择了离婚。想一分钱不用处理掉丧事,所以找到我们,演一场戏。而我还不由自主地虚伪地陪着她演。我为这样的自己感到羞耻。不,她可能也付出过真感情,所以才会在前夫死后没有置之不理,而我却那么恶心去揣度她,我为这样的自己感到羞耻。Leo,你知道吗?我已经把自己丢了差不多有二十年,我觉得我找不到自己,就像桑,这个殡仪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我看着阿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具有“变身功能”的女子,又给我展现了新的一面。
“阿桑姐,你想改变吗?”
我坐到她身边。
“哈哈,当然,我可不是因为俞聪三顾茅庐或者超哥说了什么,才跑出来加入你们一起工作的。我想要改变。我已经习惯了麻木地活着,做一些我认为我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想找回我自己。”
她没有跟我说她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作为一个大概从未丢失过自己,一直冲动任性生存着的人类,也无法真正明白她的决心。可是她说出的每个字都让我动容,阿桑,不就是有这样魔力的人嘛。
“Leo,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孩子?”她晃着她又长又壮的腿,仍然仰着头看着天空,表情天真又认真,“才6岁。今天他妈妈与我们博弈的整个过程,他一直闷头玩着手机游戏,像是齐骥那样,屏蔽着外界的一切。可是他啊,今天开始,失去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