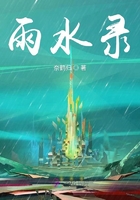周末进了一次城,A市的一个美术馆在做日本艺术家村上隆的展。栗小可说那是她最喜欢的艺术家,如果可以嫁马上就想要嫁、或者为他做任何事都可以的那种偶像。于是老齐跃跃欲试,要来看看这位艺术家到底哪里了不起。是的,他并不把小可那些换来换去的男朋友当回事,但是小可对村上隆表现出的热情很不同,让老齐对一个偶像产生了威胁感……
这世上的爱多种多样,形态是不同的。有一次我跟阿桑讲了这个道理。马上就要过36岁生日的阿桑,不但在经历着她人生第一份职业性工作,还在经历着人生第一次情感上的选择。阿桑说她之前始终觉得有一种客观不变唯一的东西叫爱情,举案齐眉、你侬我侬、白头偕老、生死相随。我在阿桑的爱情观里,体察到这些中文名词。然而爱是一件极复杂的事情,人性深幽,爱,没有绝对唯一的标准。我们看很多电影阅读很多书籍,经历很长的人生,想法秒秒会变。
栗小可是那种没有多少爱会分给现实存在于身边的人的类型。但当你能将满腔热情和精力都投向一个偶像,谁能否认那不是真爱呢?为他做任何事都可以。我短暂的人生阶段里,还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爱。但阿桑这么多年为了超哥是不是呢?俞聪为了阿桑又是不是呢?
周末的美术馆像夏天南欧洲的度假海滩或者是阿桑家刚下完饺子的柴火锅,人声鼎沸。A市的艺术产业做得并不好,无人能够好好管理的展厅里,人的声音已经制造了巨大的噪声场。更要命的是,没有多少人在认真看画。姑娘们都穿得很隆重(对不起,我不能说那是美,只能说是隆重),化了精致的妆容,每一个都那么瘦,拥有灾荒一样的平坦至凹陷的腹部。样式不一的自拍杆随处可见,整个展厅是个硕大的摄影棚。世界各地流行“网红”,颜值成为真正意义的生产力。美的她们在这里,与美的画一起,制造了绝对的丑的画面。更不要提,四处追逐打闹的孩子们,和跟在他们身后用更大的声音呵斥“不要吵”的父母们。
但,我喜欢。我喜欢这人声鼎沸。在殡仪馆工作生活久了,山野空旷下的宁静,让眼前这一切都脱离了常态。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像是会发生很多故事的契机。
村上隆的作品色调明亮,将植物、花朵、卡通融入到了他独创的“超扁平”理论中。
“所谓‘超扁平’就是Superflat啦。”栗小可跟老齐一幅画一幅画地讲解着。老齐则是一脸完全不懂她在说什么的样子。“你用用你那生锈的脑子好吧?不是号称学霸吗?”
“讲一下。”老齐低下头,面红耳赤。
“好吧,你看这幅,是他最著名的太阳花啦。是不是一个平面?村上隆认为,日本文化与西方不同的是,”说到这里小可瞥了我一眼,“日本艺术都是平面,文化里没有3D.我不是专业的啊,但我觉得中国绘画也是平面。这可能是东北亚文化的共性。所以他的创作提出了这个‘超扁平’理念,并且他认为,将来的社会、风俗、艺术、文化,都会像日本一样,都变得极度平面。”
“啊,我懂了。像是电玩、动漫,包括如今微信这样的社交软件,的确都在让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立体,好像是一个平面。”
“Leo聪明哦~”小可边夸我边走向下一幅展品,是村上隆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我和DOB》,完全不管仍然完全不知她所云的老齐。
“所以Leo,我们家村上隆是不是大神?”
“还好啦,美国太多类似文化,我没有很感冒啦。”
“尅你哦!”栗小可像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一样,讲话有点台湾腔,会用很多港台的流行语,说起来的样子有点好笑,我忍不住笑起来,“不喜欢那你还来?”
“我喜欢他写的小说欸,也算是我的职业偶像吧。”作为全球最炙手可热同时也饱受争议的艺术家,村上隆,同时还写小说。思路清奇,下笔如有神助那种作家。
“Leo,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你的职业是殡仪师!”对小可的抢白,老齐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同病相怜的同情。
“那你说,村上隆和你的聪神,谁更神?”我不死心地反击。
“Leo,”小可转过身收起她的吊儿郎当,严肃地看着我,“村上隆是属于人间的,我要是有机会一定追求他,是男女之爱。聪神是信仰,他就摆在那里,没有温度,供人观瞻。懂了吗?”
“太可怕了。”我吐了下舌头,老齐脸上现出诡秘的笑。好像栗小可这么神神经经的样子他也喜欢似的。
“今天很可惜,聪神没能来欸。他也很喜欢日本艺术家的。”
“村上隆???不会吧。完全想不出这会是他喜欢的艺术家啊。”我扭头又仔细看了看这些作品,不敢相信这是俞聪的口味。
于是,返工后我马上去问俞聪,
“村上隆我一般啦。我很喜欢草间弥生。”
“有什么差别……”我想了一下,那个永远红头发穿点点装,像从动漫里走出的怪婆婆的作品。
“我不懂艺术,我说不上她哪里好。但是我在日本,在欧洲,在国内,在任何一个美术馆看到她的作品,都会沉浸其中不愿走出。她的作品像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梦游。那些圆点之间是梦的倒影。我们这代人是伴随中国流行文化兴起成长的那一代人,像她这样流行文化艺术家的作品,是我们这代人看世界的眼光。是…”没想到说起喜欢的艺术家,俞聪竟发表了演说,然而说到这里,他犹豫了片刻才继续,“是每当沉浸在水底艰难呼吸时的求救声。”
我一时失了神,沉浸在水底艰难呼吸时的求救声。这不就是俞聪爱人的方式?小可爱人的方式是全情投入不顾自我再迅速抽离。老齐爱人的方式是默默享受自己内心世界。阿桑爱人的方式是中国传统教养。而俞聪,那是他沉浸在水底艰难呼吸的求救。这么多年里,他所给予阿桑的一切暗中帮助和支持,都让他能沉在水底呼吸得不那么艰难,然而问题是,他仍在水底。
“那么,不要沉太久吧。还是要及时呼救。”我真想像他发表关于喜欢的艺术家那段演讲那样,跟他说点像样的话。可是我的中文贫乏到只能说出这么乏味的语句。
日子日复一日地过,像中国学生写作文最常见的那句: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桑”最近变成了托儿所。被托之儿是超哥的儿子,小壮。
本以为已经平息的超哥风波,没想到还有后续。超哥突然带着儿子上山来,据说被太太扫地出门。太太想让小三知难而退,所以让他带着“拖油瓶”。
“哪有什么小三,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超哥摇摇头,完全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就像所有不忠于婚姻的男人那样,“逢场作戏”像是立场十足可判定无罪的理由。“油腻。”小可翻了个白眼小声说。我看着超哥,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网络上形容中年人的“油腻”。
“没地方去啊,借住在你们这里行吗?”
“不行。”阿桑马上反对。
“老板说呢?”超哥不紧不慢,像是胸有成竹。
我们都看着俞聪,等他拒绝。
“孩子不怕的话,那就,住吧。没地方去的话。”结果俞聪像是怕阿桑不答应似的,用哄孩子的口气看着阿桑,这样应了下来。小可气得一跺脚,我们也都觉得俞聪真是让人泄气。
从此这个叫小壮的皮猴就在“桑”上蹿下跳。一个皮猴能顶得上周末美术馆那一众人,“桑”不再寂寞。
超哥日夜进出,他不用做什么,只是出现在阿桑面前,已经是压力。我像是看着俞聪越来越沉在水底。
“快跟我去接体,青姐婆婆刚刚没了。”来不及想这些。俞聪跑下楼叫我和老齐,神色紧张。
哪还有什么水底不水底的?
生死之外,再无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