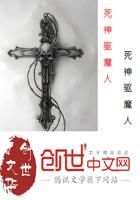明瑶心中紧了一下,众人也齐回头看去。不知何时,厅堂中僻暗的某个角落里,背着人群,凭桌正孤零零的坐着一个黑蓬玄袍的人。那才刚否定了明瑶的话,便正是此人所说。
众人一起驻足,都好奇狐疑的看去。英无声混在人群稀少的地头,也瞅着空档静静地向那人窥探,一霎时觉得似曾相识,猛可里想起,虽然那人面上,被斗篷上垂下的巾罩遮得严严实实的,连眼睛也看不见,甚至连双手都被宽大的袍袖拢得瞧不着半分,但从他的后影里辨别出,他依稀便是自己在伍妹儿家遇到的黑衣人的模样。
这人怎么会全蒙着面呢,难道他生得丑陋!也不对啊,这人杀人刨心,眼也不带眨的,又岂会在意自己的容颜,他遮面不以真容现世,多半是身份隐秘,有所藏匿,怕被认出来的。
难道他竟不是这黑血七渊中的人物,他混入此地是别有目的!那他又怎么能来到此间的,他竟会是谁呢?难道灭绝小镇人口的,除了赵家门里,还有另外的人!
英无声不自觉得往后退了退,听得一咎先生说;“这位爷台怎么称呼,不知通冥五圣与阁下可有渊源,阁下既来此间,便是朋友,阁下何不以真容示人呢,阁下既然说明姑娘言语有假,可有凭证。”
明瑶心中不安,猜测自己与赵宗之在密阁门口说的话是不是让此人听到了,还是这人亲眼见到了那骷颅客重伤左右二使的事。明瑶想,如果那让骷颅人潜入报复的消息被说破,说便纵如左右使功法这般玄妙,亦被重伤垂命。那么这个望海崖,立时便会炸开锅了。此间人众虽多,但多为乌合蚁聚,未有几人可比得过左右二使的。
明瑶猜不透,此人当下这般的道破自己的言语,到底是何用意。
那人未及回一咎先生的话,明瑶当下便试探着说;“这位英雄说小女子言语涉假,一定是另有高见的了,现今七渊的众位前辈云集于此,这位英雄如果心有疑虑,或有佐证,何不赐教一二呢,小女子若有差漏之处,定当恭聆尊训,也好得些进益。”
明瑶的话说的客气,她先前在厅中当众说论,是揣测了师尊当此之时的心思而作的决定,她说的话自然是有真有假的,所真者,小镇里的确有仇敌潜伏着,且已杀了诸葛四兄弟,重伤了七渊中顶尖儿的高手。所假者,是她讲了师尊和左右使并那焦三太祖,皆去追查戒备去了,她并未将七渊盟左右使受重伤的事讲出来。
据她的判断解析,在此紧重关头,敌踪已现的时候,师尊和他们黑血的首领,当然是要去查看的。她既说了师尊去访探敌踪,那么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二来她想,既然那骷颅人甚为了得,不好对付,这点虽然不可言明,但若按常情揣度,那骷颅人此来的目的极有可能是为黄月山中老祖脱困的事,这种情势之下,师尊和那焦三太祖将人招聚于此,亦无外乎拨派人手,多加提防而已,那么自己说了有人潜入的消息,让一众人早做准备,这便也是师尊与他们黑血七渊让做的事了。
她这么说,既可点示众人多做警醒,也不致落下刻意瞒报的话柄。她虽话有不实,却也用意不恶。
但奇怪的是,黑衣人见一咎先生与明瑶如此发问,却仍是没有做出应答。他依然像一团老木疙瘩般的,静悄悄的坐在暗光之下,连身子也没动一下。桌上的酒食齐整,是丝毫没举筷箸的样子,那人背对着人,一时沉寂如死,半天里好像连气息也没出一口。
庭中微风略动,英无声猛然看见,那玄衣人脸上黑蓬之下,竟然还戴着一个银白色的精密面铠。
一时一些粗鄙急躁的汉子已骂出了声,说那人藏头露尾故作神秘,算什么英雄。说那人傲慢无礼,大言欺人,也有一些焦暴的便怒气大盛,摩拳擦掌便欲上前出手的。
突然,就听得不知谁喊说了一句,说;“这人鬼鬼祟祟,必是奸细无疑,不必与他废话,拿下他仔细拷问,不可让他跑了。”
话音未落,已从人群里的桌上飞起了一只酒杯,旋转如陀,疾快如电,只向那黑衣人的后脑勺上击去。听得破空声呼呼震风,知道那杯上劲道委实不小,着上功夫不济的人,便立时有脑裂身亡的危险。
众人一来不忿此人的怠慢无礼,一来也想借机看看此人的门路手段,于时便没有一个去解救,都吵吵纷纷的后退,便腾出了好大块地儿来。
明瑶从大局出发,心想能来这无尘阁居的人,大多是师尊相邀,多与师尊交往密切,即便不是,也可能是哪位朋友的朋友了,真相未明之际,若因一两句的言语失和的小事而弄出人命,致使各门派各体系闹出误会,再因此耽搁了大事,那便追悔莫及了。
心念电转之间,明瑶作了如有急切,便有出手救人的打算。但她也想借机瞧瞧,此人蒙面遮身,言语相违,功法究竟是何路数。
明瑶便紧盯着看那人的动静,忽然提醒着说了句小心。她话音未落,却见那只杯盏滴溜溜的,已飞旋到黑衣人的斗篷垂布边上,眼见再不闪身避让,那人便要有脑浆飞溅的下场了。
有些老成些的不免替黑衣人感到惋惜,一些人却稍显喜悦,一些人却已转过头不忍看了。
那人似没有发觉般的,依然未动。明瑶和夜曦都掌中扣着暗器,作势便要出手。瞬间里,只听得众人讶异惊叹声不绝,两人便也都定睛细看时,只见那个酒杯,已不知如何,却正好端端的落在黑衣人脚下的地砖上了。
就见那酒杯平整,丝毫未见受损的样子,连那杯中满斟的酒水,竟也没有一丝洒出的痕迹。
明瑶和夜曦俱惊,看众人时,也都是惊疑不定,有些人更是面上现出了惶恐的神色。
明瑶和夜曦各想,那投掷酒杯的人,为了炫耀夸奇自己,在掷出的杯中斟着满满的酒水,如果要在尺寸之间不动身色的将酒杯击落,怕在场的很多人都可做到,亦无甚猫。如果在须臾之间,寸缕之地,要不动声色的将酒杯击落,且使酒杯不破的,在场的英雄中依然有许多人可以办到。若说玄异的,便是在电光石火之际,轻描淡写的将凶杀利器灭于无形,将那只酒杯打落地上,杯不破,酒不洒,声不出,招无形,怕便是寥寥无几个了,且如果论及临场的气度,怕是没人比得过那黑衣人。
此人会是谁,这身手绝不在左右使与赵老太爷之下,七渊盟中的高手众人尽皆知悉,怎么全无此人映像。他既然受邀赴会,怎么不以本来面目见众。
果然在一片刻,众人被黑衣人的身手气度所慑,俱各惊疑,再不敢冒然出手挑衅了。
那掷出酒杯的人的力道并不弱,相反还有几分霸道,却不想被黑衣人呼吸之间破于无影无形,这人是何等的深不可测啊。
众人一时皆收起轻浮猛浪之心。还是一咎先生率先又问道;“阁下到底是谁,敢问阁下如何称呼。”
骑鹿双客中的那个八字吊搭眉的牛入海也说;“阁下既然有那般说法,定是有那般说法的理由了,还请尊驾示下,也解大伙疑惑。”
众人再次安静下来,看那人依然没回身,只说;“难道在座的各位受邀前来,仅是为解救山中的老祖脱困,众位各负主命,难道没别的目的?”
有些人便不明所以,被黑衣人说的云山雾罩的,不知黑衣人欲说何事。但众人都是在血雨腥风中摸爬滚打久历杀伐的,都猜测黑衣人这般郑重其秘,一定是要说出什么重大的事了。
魔灵五老中的老四莫干山便显的有些急,好像极其按捺着性子,说;“大丈夫直立于世,先生有话尽可明言,这般啰啰嗦嗦的,藏头露尾,也太不痛快,只像个灶台上刷碗的长舌的娘们妇人,成什么话。”
其时大厅中尚有许多巾帼之辈,那才刚说话的莫干山,不知是性子使然,还是一时忘却,竟全未想到此点。他话音甫落,刻时便惹得一众妇人女子都向他怒目而视了。连明瑶夜曦也不满的向那老头看了一眼。
便听得聂三娘冷哼一声开口说,“魔灵山的莫四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自来喝风饮露,没食过人间烟火,当然不知道围着灶台刷碗的娘们妇人是什么话的。”
那莫干山听聂三娘这般奚落自己,果然便再压不住火气耐心,骂说;“贼婆娘,你骂说,你好大胆,敢这般阴阳怪气的,是找死么。”
聂三娘说;“矮冬瓜,谁认我就骂谁,你老朽糊涂,耳背到这地步了么,听不见我说的是莫老四么,活了一大把年纪,说话这等没有检点,却是活成狗了,我不骂你骂谁。”
厅上众人本多好事之客,一时哄堂大笑,有揶揄的,有规劝的,有起哄的,有乱嚷的,有喝彩的。那魔四爷便恼羞成怒,笼不住怒火,不待其余弟兄解劝帮忙,已顺手抄起一把座椅,力运双臂,暗地里使了魔灵山的杀招,就炸雷般的砸了过去,口中喝道;“淫贱婢,我废了你。”
莫干山说骂间便要欺身而上,却见那聂三娘并没有惧怯的样子,不知何时,手中已握着柄将及三丈长短的青蟒软鞭,却并未使出,只将那雷奔似的椅子轻轻的一拨已抓在手中,就慢慢的放下了,说;“莫老四,果真要打么。”
场上众人,魔灵五老,连及英无声,一时皆被聂三娘的露出的这手惊了一惊,都未想到,这聂三娘虽然看着娇娇滴滴,不胜弱风的样子,却原来这般了得,她竟然能将魔灵山的那手滚云头轻轻简简的接下来,举重若轻,看来是盛名之下无虚士。
众人便都在心中自较,如果是自己,能否接住魔灵山的那招看似平淡却如奔雷般的滚云头。
或许是莫老四被聂三娘的这手震慑住了一下,只见他在一瞬里愣了一愣,便已被其余几个兄弟拦住了,几兄弟并成一排,都虎视着聂三娘,有将聂三娘合围而击的情形。
明瑶见状,忽然心里猛得悸动一下,似想起了什么来,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却一时又想不起是什么,环顾四周时,只见那黑衣人还是之前的样子,竟然仍旧是一动未动的背着身子冷坐着,全猜不透他到底是何居心。
一瞬间,明瑶只想到,此间紧要关头,决不能再出差错了,若这些七渊联盟的人斗杀起来,让那骷颅人乘了便利,只怕还要死更多人了。
想通此节,明瑶趁着聂三娘和魔灵五老对峙的时机,拉了赵赫与夜曦一步抢到场中,便先行了礼,说;“致使众位前辈失和,自是鄙门师徒的招呼不周之过,小女子斗胆,请众位前辈看在家师薄面上,看在老祖往日的情份上,在此危重时刻,能携手同济,共克时艰。莫生无谓的斗杀,一切从大局计议,先救出老祖为要。”
赵赫和夜曦便也连忙向众人作揖陪情,终于聂三娘先将长鞭收了,那魔灵五老便也说;“且看在老祖他老人家的面子上,此间之事,一且以大局为重。”话毕都缓缓的归了座。
众人都静了下来,但都并没有即刻离去的意思,众人似乎都觉得变起突兀,极然蹊跷,但又不知何处可疑,似觉得,此间唯有那黑衣人举止诡异,遂都齐刷刷的将目光看向那人去。
便是连英无声,也觉出了那黑衣人的不可琢磨,英无声想,即便是脚手瘫痪无力的人,便是不能起身的坐着,至少也能见到气息的吞吐,背肩的轻微抖动,但现在眼里见到的此人,模样竟如刀刻斧雕,他那般一动不动的坐着,竟好像连一点气息也没有,更别说有丁点的动作了。
难道这人会是死人不成,或者像小镇上的那些魂魄一般。但奇怪的,他为什么要将自己的面目遮挡的那般严整呢,众人因他的几句话就闹动起来,作为此间客宾,他怎能无动于衷呢。
英无声躲在暗处,正胡乱猜测,却见一咎先生当前一步说;“这位明姑娘所见极是,我们且万不可着了什么人的挑唆,而致使大事贻误。”
一咎先生折扇轻摇,眼光死死的盯在那的黑衣人肩背上。众人便知,一咎先生是话有所指。他这般言语,自然是对着那黑衣人而讲的了。
众人也便像英无声一般的疑惑,众人皆想,这大厅之上,众人彼此之间尽是沾亲带旧的关系,或是同宗同祖,或是故交宾朋,若是刚才两派斗杀起来,怕终要酿成或不可控的萧墙之难了。此人以一句言语便致使酿成事端,他却俨然置身其外,不得不让人疑惑。
众人盯着那黑衣人看,不觉间将他已围了起来。但那黑衣人也不理会,仍旧是泰然自若,依然故我的样子。
一咎先生只得咳嗽一声,说;“听闻阁下刚才的话中另有他意,在下愚昧,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那黑衣人没转过面来,只慢条斯理的说;“吴法天,孟落星,孟落川,朱堂霜四人已死,你们难道没听说。”
就见一咎先生面色徒变,转瞬又复镇定下来,说;“怎么可能,先生是道听途说还是亲眼所见,先生这话,也未免太耸人听闻了吧!”
其事英无声正怀疑着黑衣人身份,想知道他是否为在小镇里无辜杀人的恶汉,英无声静听着黑衣人的每句话,见当黑衣人这般说过,那一咎先生反问后,在场的所有人,便都面色震动,满是惊讶了。
英无声便知他们说的那死去的四人,极可能是很不寻常的角色。
便听得魔灵山老四莫干山怒气冲冲的说;“胡说八道,信口开河。”
那久未说话的追星崖的孙仲年也说;“某家来此前见过盟主,也见到两位孟兄和朱兄,这位先生的话,怕有不实。”
一咎先生说;“孙兄所言极是,四位宫尊襄助盟主坐镇明宫堂,明宫禁卫森严,谁能公然闯入害了他们!”
那黑衣人并未接茬,却荡开话题说;“如此看来,此间并非说话之地!”
聂三娘说;“先生有话请便明言,此间如何不是说话之地了。”
那黑衣人说;“难道大伙这么多人,竟然无人知道双孟朱吴四位宫尊,已奉盟主之命来密守黄月山的事。”
众人俱是心中大奇,都盼望着黑衣人讲下去,众人都略微感觉到,黑衣人似乎要讲出一个奇闻来,众人都并未听说,那四位宫尊也到小镇来了。
却见孙仲年在黑衣人讲了那句后,面色刹那就沉了下去,一双眼中寒光点点,如要杀人般的看着黑衣人,说;“事关老祖安危,信口雌黄的话,孙某劝先生还是不要乱说的好。”
黑衣人不为所动,说;“你是在警告我什么吗,孙先生怕我说出什么真相来还是怎样?”
黑衣人幽幽说道;“四位宫尊已奉盟主密令暗守黄月山的事,大伙有没有想过,盟主为什么不让大伙知道。”
聂三娘说;“盟主雄韬伟略,定是自有安排,可能盟主怕事出意外,是防着六界中高手的意思吧。”
黑衣人没回面,却说;“孙先生,你以为聂夫人说得对吗?”
黑衣人不待孙仲年回答,说;“四位宫尊亲奉盟主密令,看守在黄月山中,他们玄功通彻,是盟内屈指可数的高手,大伙想过没有,谁有本事杀得了他们。”
孙仲年说;“先生口口声声声声说四宫尊来此小镇,且已身死,却有何凭证?”
黑衣人没接话,伸长衣袖从地上暗角里提起一堆包裹,打开了,竟然在一个匣子里放着颗血淋淋的首级。
众人大惊,看时,认得那正是四宫尊之一朱堂霜的头颅。
众人惊呼声中,就见孙仲年逼上一步,说;“阁下到底是谁,如何得知四宫尊奉旨密出的事,阁下可知是谁害了四宫尊。”
孙仲年目光如刀,是眼看黑衣人答有所漏,便要撕碎黑衣人的情形。
众人虽不明了,却在一瞬里,又将黑衣人围拢得更严实了。
众人都骇异狐疑的看着那黑衣人,他们想的正和孙仲年所说一般,他们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有没有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秘。
那黑衣人说;“谁害的,你没听这位明姑娘说,这小镇里已有六界中的正派高手杀了进来么!”
黑衣人说;“待过些时候,左右使回来,你们便可听到左右使定然会这样说的,左右使便说此间已被六界暗袭,四宫尊早为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