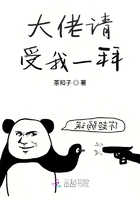我近日总避着薛兹,这变故来得突然,总要有时间接受。
薛兹是个榆木脑袋,不懂变通,只是觉得我冷淡许多,遇事无法只得去寻江兆,他向来鬼点子多。
江兆自然趁机敲一笔吃食,挑了个酒馆坐落二楼栏杆旁,薛兹瞧着外头首饰摊铺发愣,突然问出一句。
“泊延,安年近日好似心情不快,我曾远远见过她,望着一只钗愣神,神情语态都像极了我幼时见过的师太,你觉着可是出什么事了?”薛兹用着求助的目光瞧着他,已忧心忡忡许多日又不敢上前问缘由,只好找个法子应对。
“什么钗?倒是细枝末节说仔细了,我才能为你解惑不是?”江兆更是摆出一副老手模样,把玩着手里的兰花香囊,面露喜色。
“只是一只普通的簪花小钗,还没比她摆在妆台上的贵重。”薛兹曾见过大婚之日,陛下运来的珠宝是以箱计,件件都值足金,而那一只簪花小钗他曾细细瞧过,只是平常女子家的玩意,难登大雅之堂。
“将军这便不懂了,在情爱之上,不是越值钱的东西越重要,是看那东西在那人心中有着怎样的回忆。”江兆身子往薛兹边上一倾,极认真的瞧着他。
“……仔细想了倒还真有发现,那只簪花小钗是我那日跟踪她时无意在城墙下拾到的,本想偷偷带回去修好了再还回去,没想到却被她撞见。”薛兹托腮细思,极快忆起,说是这般实是见我苏醒便慌忙的四处翻找东西,却又不与婢子言说,也聪明料出是我不想被外人发现对我极重要的东西。
脑中突然忆起,那日接下我后似乎瞧见从我头上掉了什么东西,忙着替我寻医便来不及思索,大致猜测便偷偷跑去那里,刚巧碰上我寻了个理由去找。
“于是这簪花小钗便成了你俩的定情之物?”
“也不全是啦。”薛兹脸颊微微泛红,稍有局促的鼓弄着茶盏。
“还有什么秘闻,都说来听听。”江兆是被引起了兴趣,端坐在他面前,将兰花香囊塞进了怀中。
“此事连她都未知,我也只说与你一人听,你得先允诺于我,绝不告知旁人。”薛兹将这秘密埋藏在心底十余年,他本以为此生都无机会说出,也以为此生都无机会与她并肩偕老,共度一生。
“将军还信不过我?我虽恶名在外,但也是个一言九鼎之人。”江兆佯装微怒。
“我自是信你,江湖不都说凡事有个过程才算重要?”薛兹知晓江兆向往江湖,与他相处便时时提醒自己些江湖规矩。
“是有这规矩?看来我还是陋闻了。”江兆皱眉,“此事暂且容后,倒是先听听将军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我父亲是叱诧风云的老将军,曾为宣氏打下江山,而后又奉命辅佐先帝,先帝驾崩,又一直守护着陛下,镇守边界,安危难测。”
“母亲整日提心吊胆,为家族四处奔波已至早产,身子愈发不好,直到最后出殡时父亲都未及赶回,我身子从小羸弱,人人都哂笑我不能继承父亲的衣钵,继续守护陛下的江山,只有一人不同。”
“父亲忙于守护,也因此疏于与我亲近,幼时曾一连数年都见不着父亲一面,陛下见我孤苦伶仃一人,便时常接我过宫,与他的小公主玩耍,也就是安年。”
“安年幼时性子也顽皮,常偷带我从密道溜出宫墙,一玩便是一整时辰,直至疲累不堪才依恋不舍的回宫。”
“我第一次瞧见她便觉得她与常人不同,我每日无休的锻体塑身,只为了在以后某个需要我的时候能护她安好。”
薛兹提及母亲时还不免伤感,但时间总会冲淡一些。很快也因提及安年而面露喜色,像个面见心上人羞怯不已的少年郎。
“如此说来,您对公主是倾心已久?”江泊延也算听的明明白白,薛兹一点未提的故事却总结的完美。
“不敢!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将军,怎配扯进她的一生?”薛兹也不敢有此想法,他自认卑微渺小,安年是他命中高高在上的光,本高悬于苍穹,不可与深陷淤泥的他为伍。
“可将军如今是公主的驸马,您与她早在幼时初见便已注定纠缠不休。”那眸子深沉平静,像是要想看穿了谁。
“你……你从哪学来的这些,文文绉绉可不像你了。”薛兹却只注意到这些,觉得江兆说出这话奇怪,他乐天开朗,豪气不拘,从不看些诗文卷案却能说出这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