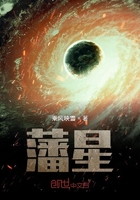映秀镇,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南部的一个小镇。与卧龙自然保护区相邻,是阿坝州的门户,是前往九寨沟、卧龙、四姑娘山旅游区的必经之路。从山顶往下看,小镇像一个婴儿一样,偎依在群山的怀抱之中。从北向南而流的岷江与从西北卧龙自然保护区而来的渔子溪在两江口汇合,潺潺地流向远方,而小镇,被这两条河水像围巾一样,又轻柔地围了一圈。这富饶美丽的群山,像取之不尽的矿藏一样,映秀镇的人们靠它种田,靠它养殖。这四季常清,清澈甘甜的河水,不仅给了小镇居民无限实惠与乐趣,还如镜一样,映照着秀丽的群山,温婉的田畴,小镇也因此而得名:映秀。
映秀镇位于汶川群山的边缘,是故,从映秀镇往西南走,是一路坡地,下至群山尽头后,便是大片的平原沃土。从映秀镇往东北走,也是一路坡路,不过是上坡。是矿产丰富,风景迷人的川西北山群。生活在这样美丽的地方,虎子习惯了自由地行走在大自然之中的生活。爬山涉水对他而言,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享受其中。
做为一个专业户外人士,每次出行,虎子总会计算山与山之间未开辟出来的山路有多长,徒步时需要的时间要多久。他很少开车或坐车,因此,一个城市与一个城市之间,一个村镇与一个村镇之间的实际距离,他很少用车轮丈量过。
自己的家映秀镇到可可的家陈炉镇开车有多远,虎子真不知道。不是他不能知道,而是他从未想过。
出了映秀镇,但见沿着岷江两岸,种植着无边无际的青竹。五月的午后,阳光明媚得令人目眩,车行在青竹翠影中,诗意盎然。不知名的鸟儿在林子的细枝上啾啾地婉转歌唱,竹林里看竹人家的狗充满闲情逸致地卧在主人脚旁午睡,偶尔冲着天空低吠几声,那肯定是被鸟儿的叫声惊醒了美梦。生活在竹林里的羌族人家,男人在懒懒的午后,唱着软软的羌歌,女人则拿出针线筐,坐在屋前的竹椅上,绣着羌绣。此情此景,让虎子的脑上立现出“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他看看阿坚,阿坚正目视前方开着车,他也就靠得舒服些,无限心事地享受着徒步时没有的悠闲与惬意。
出了竹林,是横贯岷江的美丽得如同彩虹般的金花大桥。车行桥上,满眼都是丰满的绿。绿的山与绿的水。那绿,有浅绿,深绿,碧绿,翠绿,嫩绿,苍绿。驶过桥后,是一个轻雾缭绕的山谷,那乳白的薄雾,绕在翠玉般的山脉,笼着琥珀般的山顶湖,如仙境一般。每每经过这里,虎子都会感叹映秀的美丽与宁静。偶尔掠过一个隐在大山里的小小村庄时,山间裸露的红色土、配一座座二层小楼的白墙黑瓦,又会让青绿欲滴的安谧画面,增加几丝活泼、现出几点趣味来。
其间,虎子经过了可可来时一定经过的一脉一脉石质疏松、山体软怠的南方山群,这是他习惯了的山。小时候,他就在这样的山系间翻越与穿行。
虎子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在映秀镇,无人不知杨如海、柳如烟夫妇。小时候,杨如海时常会带着虎子一起去采药。山里的每一棵植物都是与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他知道感冒时自己要采些秋天连翘树上的连翘壳熬水喝,拉肚子时要采些肥厚的车前草叶子嚼烂了咽下去,跌伤了要找几片田七叶子用两块石头砸成糊状敷在伤处……今天,他不知道哪种草药可以把打碎的青花瓷瓶重新粘起来。
出了山区,路过都江堰,驶过成都绕城公路,车一直往东北, 过了江油广元后,进入秦岭地带。窗外不复是映秀镇那清秀俏气的南方山区,而是野性十足的北方峰群。北方黄土的塬与北方冷硬的山替代了南方红色的土与秀气的岭。
虎子一直搞户外,他清楚南北气候的差异、南北地质的不同,南北风物人情的成因。若在平时,他会与同样喜欢户外的阿坚共谈南方的山川与北方的山脉各有哪些不同的特点,有哪些物种地貌的迥异。但可可的现状压得他找不见自己。仿佛一夜之间,他由一个天马行空的行者变成了一个有妻室的人,又仿佛一夜之间,他成了父亲。
上次走的时候,可可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仍然抑郁寡欢。自打与他在一起后,可可就沉静得动人。万事波澜不惊。面对虎子十几天乃至一个月的出游,她都仿佛对待要去上班或去买菜的家人一样从容淡定,不急不躁,细语轻声。这次回来,虎子一下子就看见可可的肚子明显地凸了出来。可可的性情也变得从没有过的焦虑与暴躁。
几个月前在山野小路上遇见的那个开朗任性的可可去了哪里?几个月前与她嬉戏山野间的罗曼蒂克的可可去了哪里?
除了阿坚,很少甚至是没有人知道虎子与可可的事。不过,阿坚也不知道她与可可那几天是多么忘情快乐。
那天,他背着大大的旅行包甩开大步往前走。他是行者,他想追不上他了,可可肯定会回去的。但可可并没有回去。幸亏她个子高,平时不用穿高跟鞋增加高度。穿着平跟鞋的可可并不喊叫他停住,只一味咬紧牙关紧追不舍。林娃望着他们的背影远成两个小黑点后,回去了。他只得带着任性得有些令人气恼的可可,改了登秦岭,穿山谷的计划,将穿越之行变为轻闲之游。
可能可可是不喜出门的宅女,因此,即使是陕西本地长大的,对秦岭深处的风景,她还是现出极大的好奇,极大的兴趣。
任谁见到冬天里的风景,都会如此夸张。因为没有谁喜欢在冬天出游,因此也没有谁知道冬天的山里会有多美。也正因为这次独行,虎子才有机会遇见可可。
冬天的北方群山。冬天的绵延秦岭。
在冰冻成路的小溪上,可可拉着虎子的手,小心翼翼地走着,就算那样,穿着普通鞋子的可可,因鞋底不防滑,仍然不时滑倒;或者在冰雪厚积的山腰上,冲着群山大喊大叫。最是那壮观撼人的冰瀑,从山顶到脚下凝成玉般的一整块,在寂寞的山谷间,静成凝固的奔流之势。可可此时会摘一条冰凌,拿在手里咔嚓有声地啃着。她因不停奔跑而热气腾腾的脸红通通的。那笑靥,虎子终身难忘。
两人不谈情,不说爱。只是心无城府地玩。
直到那天进入那片小树林。
说是小树林,是因为树棵都不大。但树林面积却极大。是北方特有的白杨。树杆笔直,树枝根根向上。仅有一棵,都会让人感到一股力量与一种气质。何况那是一个林子。那林子,不是一般的大,是那种怎么走也走不到头,走到哪里都景色一样的大。就像火车行驶在西藏的高原上,任火车如何走,都走不出那无边的苍茫与悲壮一样。
雪很厚。但阳光极好。大山里的天蓝得清澈明净。温黄的阳光照在光秃无叶的白杨树林里,洒在沉静而洁白的雪被上。那白白得耀眼,那黄黄得灿烂,那蓝蓝得人心跳加速。
也许,虎子那时爱上了可可?
也许,可可也在那时爱上了虎子?
在虎子蹲下去,抓起一团雪准备往嘴里送时,突然一个雪球砸过来,砸在他头上,开出无数瓣的白菊,然后,后颈里是雪粒浸入后透心的凉。他身上被禁锢的激情被这一砸砸醒了,在这一凉中复苏了。他立刻把那团准备吃的雪球砸过去,然后,二人开始相互疯狂地笑,疯狂地闹,尽情地在空旷无人的山野间奔跑嬉笑。最后,两人热得满头大汗。累得精疲力竭,双双倒在雪地上。
远远看去,彼时彼景,像一幅画。
蓝的天空,白的雪野,黄的阳光,配着墨绿的,虎子的户外服,玫红的,可可的羽绒服。
二人躺了很久,都不说话。如同刚才的打雪仗用完了二人所有的力气。
最后,还是可可先开了口。
可可对着天空一字一句地说:“我喜欢与你在一起的感觉。”她吐得很慢,说得很清脆,咬字很用力。像宣布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虎子也对着天空说:“我也是。”很低沉,很缓慢,他是想真实地找一下自己的感觉。
可可继续对着天空说:“可以一辈子都与你在一起吗?”
好久,虎子没有说话。他仍在寻找自己真实的感觉。最后,他说:“我没有想过,让我想想。给我时间。”
可可翻过身来,撑起胳膊,看着虎子那张帅气而坚毅的脸,委屈地说:“她人已经走远了,印痕还留在你心里吗?”她指的是虎子给她讲的他的初恋。
虎子说:“与她无关。”
可可赌气地躺回去,看着天空着说:“那就是与我有关。你看不上我。”
虎子只把头扭向她,仍然坚持:“婚姻是一件严肃的大事,不是仅仅几天的玩乐就能决定的。”
可可一惯的蛮横呈现出来,她气咻咻地嘟嚷:“我不管,反正我要与你在一起,一生一世。”
虎子没有吭声,扭正头,继续静静地看着天空,身体一动不动。
可可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她要的答案。忍不住又抬起上身。看到虎子一动不动地躺地那里。眼睛直直地看着天空。
可可随心所想地从雪地上轻轻的爬过去,把头慢慢地枕到他胸膛上,柔声说:“我就想这样自由自在地与你在一起,左右不离,一生一世。”
虎子仍没有吭声。
好久之后,可可又撑起身体,只垂下头去,在虎子的脸上用温热的唇深深地,深深地吻了一下。虎子感到一个温热的东西在可可的唇离开后,慢慢地流开去,最后变得冰凉。
那是可可的泪。
可可说,她没有谈过恋爱。没有过男朋友。
虎子不信。
不仅从可可的长相与气质,家境与性格能看到,从她的这滴泪里,虎子也能看到,事实并非可可说的那样。只是他不想说破。所以,他不能对可可的请求有任何轻率的回复。
他还不了解她。太不了解她。
可可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她虽然性格开朗,却不是什么都说。
虎子是一个没有太多故事的人。他虽然少言寡语,但他对可可很坦白。
那几天里,只有在雪地上,在小树林里,可可那个温热的吻与那滴温热的泪,是他们惟一一次零距离接触。
那天,离开小树林前,可可在一棵最大的白杨树杆上,用虎子的瑞士军刀刻下了一行字:“执虎子之手,与虎子携老。”然后头也不回地出了小树林。
虎子抚摸着那棵刻痕新鲜的白杨,抚摸着那十个霸道而率真的字,心轴渐渐松动。
一出深山,可可迫不急待地嚷着要回家。
本来虎子要送可可回家,正等车时,他的电话响了。他接到的新任务是带成都一个俱乐部组织的驴友们,去川北阆中。时间太紧,虎子只能看着可可孤单的背影上了过路的一辆公共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