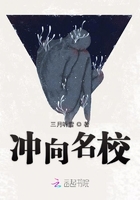夜色渐深。
无尽的黑暗之中,一只掌纹清晰的巨掌如山岳般悬于头顶,五指之上各戴着一枚光灿灿的金戒指。巨掌之下,八只大小不一的巨手竖立在八方,其五指上也都戴着金戒,与上方的巨掌一起构成一个手掌囚笼。
囚笼之内,悬着一弯斜月与三粒孤星,一星在上,二星在下,与斜月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斜斜的“心”字。斜月三星之下,地上横斜着一棵巨树,跟丑老鸭一样,一半黑一半白,树干的一端锲入一只青色大斧之中,另一端顶着一个由弯月形的树叶聚成的树冠,树冠如一颗心脏般不断地扩张与收缩:扩张时枝叶散开,排成与上方斜月三星相似的形状,并有一道道闪电由内飞窜而出;收缩后如拳头,如心脏,如一颗带电的黑白眼球。
树下,一百零八个亮点绕着圆心的一个光团组成三层同心圆,一条“S”形的阴阳线从中间穿过,将其斜分为左明右暗的太极图。太极图上,端坐着一个半黑半白的人,满头的长发披散下来,遮住了他的面容。
丑老鸭望着眼前的一切,心道:“不会吧,怎么又梦到了这里?”
这个梦境贯穿于他的整个鸭生之中,从丑小鸭到大丑鸭再到丑老鸭都不能幸免,每当他对外面世界生出向往,就一定会做这个梦。
他深吸一口气,像以前那样在心里默念:“来吧,我准备好了!”
像以前那样,上方的巨掌骤然拍落,穿过斜月三星拍在巨树、那人和丑老鸭的身上,拍得他们一起向下直坠而去……
鸭鹏里,丑老鸭骤然惊醒。
抬起头,透过破渔网的网眼望向夜幕,但见星河垂挂,弯月偏斜。忽然,他想起了大海,自言自语道:“听说星星和月亮都是从海里升起来的,大海可真好啊!”
大海,比好多个李家大院都大,可以尽情畅游;海水比蜜甜,可以无限量畅饮;海里的鱼永远吃不完,可以放开肚皮大吃;月亮与星河从海里升起和沉落,也许可以游到月亮上去呢……这时候,他油然生出一种冲动——离开这里,去看大海!
可是,这可能吗?
主人和众禽兽不会允许自不必说,就算他们允许,山长路远,世事艰险,什么时候能走到海边呢?而即便一路顺利,一大把年纪的他也许还未走到海边就老死了,何况更重要的是,一旦离开这里,他就再也见不到花花了!跟大海相比,花花近在咫尺,唉,要是能和花花一起去海边就好了……
想到这里,他摇摇头,长叹一口气,天还早,还是继续睡吧,或许可以做一个美满的梦。于是,他埋头于鸭背之中,很快再次睡着,再次进入那个梦境,被头顶的巨掌又一次向下拍落……
数日间,众鹰鸟带着瞌爷飞出月亮湖,沿着地图上的路线向南飞去。一路上,瞌爷站在雕背上,时时向周围张望,幸而一直没遇到众冰熊虫。
前方,五座雪峰如五指般耸立天际,各峰的峰顶之上各自立着一尊黑色玄武——十几丈大小的黑龟四足撑地,狰狞的龟首昂扬向天,露出满口参差不齐的暴齿,纹路纵横的龟背上驮着一块十几丈高的白色石碑,一条几十丈长的黑蛇盘绕在龟身和石碑上,蛇头立在碑顶,面向南方,长而红的蛇信不住从蛇口中电伸而出,又电缩而回。
每尊玄武之上,都有一个黄金项圈将黑蛇与黑龟束在一起,每尊石碑的北面都刻着三个黑色篆体大字:入吾阵。
这天,众鹰鸟带着瞌爷从北边飞过来,本来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是想绕过这五座雪山的,然而无论他们向南还是向北飞出多远,这五座山都像长了脚一般地挡在前方。
没办法,只得从山上飞过去。
雕背上,瞌爷紧张地注视着下方,随时准备喷火,然而直到飞过峰顶也没有任何异状,回首北望,他看到那些石碑的南面上都刻着三个血红的篆体大字:出无赦。
过雪山后,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春天的草原与万物的胸怀都格外地开阔,天空湛蓝,长河蜿蜒,花海烂漫,蜂蝶群舞,鹰隼翱翔于白云间,成群的汗血野马身上闪着银色光泽,四蹄翻腾着飞奔来去,不时畅快地昂首长嘶。
在瞌爷他们身后一百多里外,刚刚飞过雪山的骷髅冰掌向着前方的草原飞来。冰掌上,伸着鼻子四处嗅探瞌爷气息的公冰熊虫又一次颓然摇头,向着母冰熊虫有气无力地叫喊道:“还是没有。老大,太热了,咱们回去吧。”
母冰熊虫骂道:“回什么回!你是不是又欠抽了?”
公冰熊虫喜道:“嗯呢!”
母冰熊虫挥动冰髓抽过去。
“啊,好舒服!好舒服!再来一鞭!”
“滚!”
下方的地上立着一棵孤独的榆钱树,冰掌骤然向下拍落,一串串嫩绿的榆钱立即裹着一层白冰飞起,如纸钱般四散飞射,母冰熊虫吼叫道:“小虫儿,本王一定要捉到你!”
此后十多天,骷髅冰掌在草原上转着圈子搜寻瞌爷的气息。在他们前方,众鹰鸟沿着地图上的那条斜线一路向南飞去,飞过草原、戈壁、高山与湖泊,向着地图上一百零八崮围成的三层同心圆直飞而来。不久,后方的公冰熊虫终于嗅到了瞌爷的气息,指引着冰掌向前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