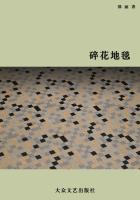今天的海很黯淡,跟天空一样灰,海潮涌进港口,拍击着渔船组成的墙。还好没有下雨。我走进船屋之前,清了清喉咙,这样我就能问出泰在不在,我还涂了点红宝石色口红润润自己的嘴唇,万一他想亲我呢。
船屋是空的,就像我昨天离开时一样,它看上去更凄凉。我刚刚在一张毯子上坐下,就被外面传来的嘎达声吓了一大跳。然后,我听见了音乐声。我回到鹅卵石滩,才发现声音是从上面的俱乐部里传出来的。我从俱乐部下面匍匐出去,爬上吱吱呀呀的楼梯到了露台上。船屋的窗户有一块木板被卸下来了,我能看见里面。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在搬椅子。在远处的角落里,大大的平板电视里正在放映的画面是一个女人平躺在海面上,身后有一轮明亮的红红的太阳。她沉入水里,银色的泳衣让她看起来像一条巨大的鱼。下沉的过程中,镜头一直追着她,直到她消失在大海深处。我感到窒息、恶心。我看到的是我的梦境在眼前成为具象,只是现在我十分清醒。音乐声很大,但隔着玻璃听上去很微弱,我感觉我爬到了相反的一边。那个男人转过身来,我开始想逃跑。
我逃跑了,在他发现我之前。
从港口到在麦凯伦大道的住处有一英里远。最快的路是从高街直接穿过墓地,我从未走过那条近道。我试过——站在墓地门口,两腿僵住,迈不动步。
相反,我走了条远路。左转从警察局门口经过,然后绕过所有的房子。路蜿蜒曲折,穿行在那些簇新的住宅区里——漂亮的大房子,有亮丽的车库和小飘窗。我们的房子更像是罗斯玛基的那些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在我们的街道上这样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
我走到门口时,父亲给我开了门,他抽烟抽得跌跌绊绊,气喘吁吁。
“你去哪儿了?”他吼道。
“学校。”我说,从他身旁挤进屋里。
“别对我撒谎。”
我不想理他,可他一把把我拽回去,面带怒色,他的眼角又多了皱纹。
“一个小时以前学校就放学了。你到底去哪儿了?”他的鼻息很重。
“没去哪儿,随便走走。”我说,“我有散步的权利。”
他按着我的肩膀,掐住我的脸,“你是不是去了海滩?”
“没有。”我说,盯着他脖子上的一颗痣。他并没有问及港口。
“你肯定你没有嗑药?因为你——”
“你弄疼我了。”我哀号起来,挣脱了他的控制。
他望向我回家的路,一副不解的样子。我抑制住了质问他的冲动,你是不是才是那个嗑了药的人?
距我上次做那个梦已经有好几个月,或者是一年。梦醒后,总让我觉得恶心。我会爬进父母的房间,挤到他们俩中间去。妈妈从来不问我怎么了,但她睡着的时候会摸着我的头发对我耳语说你很安全。
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赶回了自己房间。
“你太大了,不能再跟我们一起睡了,艾希,”他说,光着身子从床上坐起来,“如果你害怕的话就把灯开着,但是回你自己的房间去。”
他认为我怕黑。他可能从未想过我渴望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