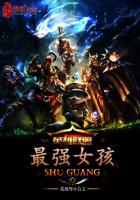天擦黑的时候,江折一行人到了距离涯渊城还有一天路程的一个无名小城,城中人烟稀少,街道上空空荡荡的,偶尔碰见一个人就像是见了什么稀罕物。
几人依然是在城中驿馆住下,江折跟花自闲聊了一天,彼此皆感到与对方很投缘,甚至还有几分相见恨晚。
花自闲没什么心机——或许说不愿意用什么心机更为合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江折若是有问题,他便一五一十地回答,至少听起来没有什么隐瞒避让的痕迹。既没有欲言又止,也没有遮遮掩掩,有的话问得过了他便直接告诉江折不能说,江折也就不再问。
“你跟我说这么多,不怕招惹什么祸事么?”临到驿馆的时候,江折问他。
“梦间能做官,什么听了能说什么不能说心里自然该有数,更何况这些东西就是涯渊城里的百姓也都知道得差不多,况且,我的事无不可对人言,至于其他的……”他眯起眼睛,终于在书生气里笑出了一点王室中人与生俱来的独特狡黠来,“我不也没说么?”
“殿下,该下车了。”外面车夫喊道。花自闲将手里一直拿来涂涂抹抹的小册子放回匣子里,坐正了整理了一下衣裳,然后弯腰摸了摸自己的小腿,这才起身对江折比了个请姿。
江折转身下了车,回过头扶了花自闲一下,让他踩着梯子下了车。
待他下了车,便有人走上前,将马和马车都带去了驿馆的院子里,赶了这一天路,马也得歇歇。
花自崇过来拉着花自闲走了,江折则进了驿馆找了一间房歇下脚。
房间里和街道上一样,干干净净的,称得上简陋:一张桌子,一张床,床头一口小柜子,床脚一只大柜子,桌子前放了一把椅子。
江折在床上躺下,默默地回想了一番自己和花自闲的对话,没什么有用的东西,倒是有不少家长里短。
原来礼亲王的五个儿子里,最小的一个是收养的,花自闲是嫡出,上面有三个庶出的哥哥。家里最受宠的自然是花自闲这个嫡子,三个哥哥也都照顾他,唯一一次没照顾到就是让他从树上掉下来了,摔坏了腿。打那以后,他就一头扎进了笔墨纸砚中。
“软儿最小,不是我娘亲生的,但收进来也是收在了我娘名下,算是我的亲弟弟,也就是我的亲弟弟。他生得漂亮,父王又一直叫他学戏,还学的是旦,唱青衣,也学花旦,看人一眼,能把人的魂儿给看丢了去。”
什么叫“算是我的亲弟弟,也就是我的亲弟弟”?
“去年冬天,我们陪伯父出去围猎,把软儿也带上了。我这腿,自然是打不了猎的,就在车里陪着软儿坐着。这一车的芙蓉,就是那个时候画的。”
明明是他腿不好骑不了马打不了猎,怎么又说是“陪软儿坐着”?
“对了,软儿这名儿可别当着父王的面叫,他在官府里的名儿叫花尽误,尽兴的尽,耽误的误,直接叫就行。除了娘亲,别人叫他软儿,父王是要生气的……”
这两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江折摇摇头,这些宫闱里的事,想得他脑袋疼,怎么就不巧摊了这么个差事。他这次出使,明面上是正常的同涯渊商议岁贡,交涉国事,暗里却还要将宜信公主发疯这个以往的使团没调查出来的事调查清楚。
如果真是让王室逼疯的,那么大启有理由怀疑涯渊已经没了对大启的敬畏之心,甚至于,不惧一战。
而如果是旁的原因,或者宜信公主根本没疯,那么这绕过了竹州,湖州,抚州一路到了琛州临沧的消息,就值得深究了。
房门笃笃笃地响了几声,应该是万宁吧。江折眼都没睁便扬声说:“门没锁,进来吧。”
门响了一声,然后又关上了,一阵很轻的足音和衣摆拖在地上的窸窣声响起来,一直走到桌边坐下了。
不是万宁……“春山?”江折猛地睁开眼,看见那个一身淡紫色衣衫的小王子正坐在屋里那唯一一把椅子上。
“梦间好耳力。”花自闲笑了笑,“我们哥儿几个要出去喝花酒,来问问你去不去。”
“嗯?”江折有些困惑,“你也会去喝花酒?”
“回头你去涯渊城的花柳巷子里问问,哪个不知道花春山。”花自闲说道,“去么?不去我就先走了。”
原来是这样,江折心里暗自有了定论,学画么,总得有东西画。“去,怎么不去。”说着他站起身来,和花自闲一起出了房间。
走到地方才知道这城里为何人烟稀少,原来都藏在了犄角旮旯的小巷子里。巷子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一派热闹。
几个跑出来喝花酒的都刚刚及冠,模样长得嫩,又一眼能看出来青涩,很是受那些揽客的姑娘们欢迎,尤其是江折。涯渊虽然盛产美男,但大都是花自闲那样长相温柔精致的男子,相比之下,涯渊的女子甚至显得更为英气一些。江折是地地道道的大启人,长了一张典型的大启人的脸:宽颧,窄额,高眉,长脸。再加上书卷气与一点张狂糅杂于一身,顿时显得格外独特。
一群姑娘拥到江折面前,使了浑身解数想要把他揽进自家的店里。
江家世代公卿,家风甚好,江折也是家里老人给教出来的,从来没进过花柳巷,更别提应付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姑娘了。
“梦间。”正在江折手足无措之际,他突然听见花自闲在叫他,那些拥着他的姑娘们也往声音来的地方一并看过去。
江折这才注意到花自闲换了打扮,之前在马车里他没戴发冠,只用一根簪将前半部分的头发束起。现在却是全都散了下来,似乎在脑后用发带略略扎了一下,右边鬓角编了一根细细的辫子,末尾用淡紫色的丝带系着,清淡中平白地多出一股媚气。
那些原本拥着江折的人看见他之后却呼啦一下都散了,转而去招揽跟他们一并过来的几个王子。那几个倒都是轻车熟路,三言两语逗得姑娘们咯咯直乐,最后走进了一家挺大的店里。
江折径自往前走,花自闲垂着手在他身侧跟着,来来往往的人或有看他们一眼的,不过转眼也就走了,也有几个女子本来准备过来叫他们进店坐坐,却都在看见花自闲之后转身走了。
“梦间,别走了吧。”花自闲扬声叫住了江折,“我这腿受不了了,前面有个正经酒馆,进去坐坐,我请你。”
江折这才意识到自己一路为了避开那些人走得相当快,这会儿都快走出巷子了,而花自闲就像怕他丢了似的一直紧跟在他身边,对于他的腿来说,恐怕的确是受不了了。
“抱歉。”江折心下有些愧疚,赶紧伸手搀住花自闲,“我扶你。”
花自闲看起来是真的不太好,脸都白了,也没推脱,就借着江折的力往前走。两人进了前面一家酒馆,花自闲从荷包里拿出一块小银锭放在柜台上:“一间雅间,两坛兰花酒。”
掌柜的盯着花自闲看了好一会儿,又看看江折,见江折没说话,这才吩咐小二领他们去雅间。
一进了雅间,江折回身关了门。花自闲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你不是说只有一条腿的伤么?”膝盖磕在地上的声音听得江折心里咣当一下,赶紧半搀半抱地把花自闲扶到了椅子上坐着。
花自闲慢慢把腿放到对面的椅子上,有些吃力地试着把裤子挽起来。
江折看他弄得费劲,便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替他褪了鞋袜,将裤子挽到了膝盖上。
他的小腿已经完全肿起来了,左腿稍好一些,右腿摸起来甚至有些烫手。
“麻烦你了。”花自闲笑得有点无奈,“不过,你没来过这种地方吧?”
“的确是,家里不让,也没什么兴趣。”江折如实回答,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瓶子,从里面倒出来一点油状的东西在花自闲腿上。
“这是……”花自闲说着便往外抽腿。
“别动,镇痛的,治不了病,但是能好受一点。”江折一只手把药油在花自闲腿上肿起来的地方抹开,另一只手把身上的糖盒子递给他,“挺疼的吧,来吃块糖。”
花自闲沉默了一会儿,打开糖盒子把糖塞进嘴里,笑道:“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