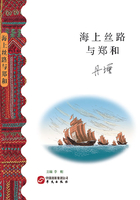至此我才大悟,原来流景便是我在寿宴上认做女子,还大肆夸奖了一番的人。
可是我同他不大熟络,除了先前的事对他颇有冒犯,也没同他结下什么梁子,想来他作为将军的儿子气量也不会那般狭小,为着一个月前的小事来我这闹上一闹。
我左右想不出他来找我的原因,便问了竹青前头的情况。
“我拦不住他们,这会应该快上来了,足有七八个人。”
我一听便觉得情况刻不容缓,若是平常,我定是寻个清凉地躲起来,继续吃自己的枣,任由他们闹,他们寻不到我,自然会离开,可这回不同,阿爹和狼爷爷正在离那门口不过五里的亭子里对弈,如果流景恰巧撞上阿爹,我也不晓得他找我是为了什么事,若是什么坏事,让他告上一状,我便吃不了兜着走。
想到这里我便急急下了树,也顾不了撒了一地的甜枣。
赶至廊下时,他们已经准备进门,我急忙施法变出一堵光墙阻了他们的路。
他们见前头进不去,又见我从后面悠悠走来便知是我的手笔,几个人甚是恼怒,要我撤了光墙再让冉蘅出来一战。
果然是来找我的,可我也不知自己哪里惹上他们了,看他们连我的光墙也破不了,加之又不识我这个正主,想来只是些无名的小辈,我便大度的不与他们计较,抬高了声音说道:“让你们的主子出来,来找我的麻烦怎么也不见他的人影,倒派你们这些个来。”
“你放肆,主子也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主子早就去到沧琅王处了。”
我说怎么不见流景,果然是去告状了。
小人,真是小人,我心里气得厉害,也没问他们上门来的缘由,便让竹青用笤帚将他们打了出去,看着他们狼狈逃跑的样子,心情倒是舒畅许多。
这才刚解决了一桩事情,另一桩又出来了,竹青说,阿爹的近侍在门外候着,说是请我过去一趟。
我的右眼皮突突跳了两下,大抵不是什么好事,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我一到阿爹的院门口就瞧见一抹扎眼的蓝色正慢悠悠地朝我走来。
我瞪大了眼睛看他,好家伙,可不就是公子流景吗?
他同样看见了我,冲我微微一笑,落在我眼里倒是带了几分挑衅。
如此,我琅山小霸王怎能忍。
虽这般想,面上仍带着微笑,却从地上踢了块石子起来,捏在手上,待他视线移开时,用足力气丢了过去。
他注意到了,挑眉,偏头轻易躲开。
我有些懊恼。
他想开口说什么,我却用另一颗石子阻了他的话。
可惜他又躲开了。
我接连丢出几颗,他像是配合我一般,左躲右闪,石子几次险些砸中他,却又只是擦着衣服过去,没伤他分毫。
真是白费了力气。
他的唇角带了一抹若有若无的笑,“不知在下如何惹得小姐不快,以至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我并未说话。
他继续说道,“我初来琅山,不太懂这里的规矩,若是有礼仪不周的地方,还希望姑娘指点。”
我皱眉,他这样谦逊倒有些不像我想的小人模样,可他就是从阿爹的院子里出来的,不是告状又是什么。
告状的都是小人,我不答他,心里认定了他是个小人,这时候不说话就是气势,说了反倒遂了他的意,落了下乘。
我继续拿石子丢他,耍着小孩子的把戏,他侧着身子躲开。
我撇撇嘴,刚想有所动作就听得一声惨叫从后头传来,流景回过头去,我同样看了过去。
地上倒着一位上了年岁的老翁,头发和眉毛已经全部花白,嘴上不住地发出呻吟,能得阿爹引见的都不是什么低地位分的,我便知自己又闯了祸。
正巧阿爹和狼爷爷一道出来,我的手仍僵硬地停在半空,尴尬得很,这明眼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刚想跑路就听见阿爹几乎暴怒的吼声:“冉蘅,你给我站住!”
我只装作没听见,用了毕生的修为飞快地逃回自己的霁雪阁,结果可想而知……
因着这件事我被阿爹禁了足,这日子还没个期限,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我一哭二闹三上吊,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这日子没法过了,阿爹你肯定是看着我是捡来的,又不孝敬你,觉得我还比不上萝卜青菜能炖个汤。
总之我表现得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但是阿爹就是不为所动,还差人送来了厚厚的几大本《戒律》和《礼仪》之类的书,说只要我将书中的内容抄录百遍再滚熟于心就解了我的禁足。
我一听顿时万念俱灰。
朔方听说我被禁了足,当天便过来瞧了我:“原来意气风发的琅山小霸王去哪了,怎落得如此狼狈。”
我伏在桌上,哼哼了两声没理他。
朔方见我如此,捂住胸口很是痛心地说:“我这般关心你……,唉,当日我明明劝你不要出门,你偏不信我,还惹出一堆祸事,把自己也一道坑了进去。”
我白他一眼,若不是他平日里常与我玩笑我也不会在紧要关头栽了跟头。
“这事还有流景的一份。”我哼道。
“流景?”朔方一怔,“这事同他其实没什么干系,听是被沧琅王请来品茶论道,当日是循例去参拜。”
那竹青之前可能是恰巧瞧见从廊下经过的流景,就以为他同那些人是一起的。
真是什么倒霉事都撞上了。
“那我又是怎么得罪了管药草的仙君。”后来阿爹将我的罪状一一列出,除了伤了仙君一条竟还有毁他药草一说,我瞧着坐在阿爹下首位的老古板,竟不知他还有胡乱捏造的本事。
朔方正在喝水闻言被呛了一下,涨红了面皮,我登时就觉得不对,扯着他的衣襟质问。
茶水洒了他半边袖子,他讪然道:“我说就是,你先松手,松手。”
到底还是那天醉酒后惹下的麻烦,据朔方描述,他将醉酒了的我一路扛着上了琅山,说为什么是扛着,朔方一脸的义正言辞,为着男女大防。虽然我把你当兄弟,但你确也是个女子,我不能趁你酒醉占这个便宜。
我白他一眼,腾朵云岂不方便。
他摸了摸脑门,呵呵一笑,我忘了。
……
说到朔方一路扛着我上了琅山,半路上我被颠得狠了,吐了他一身。
听到这我哈哈大笑起来,朔方幽幽地盯着我看,眼里满是哀怨,我止了笑,他继续说下去。
他被我吐了一身,心里别扭,将我随手放在地上,寻了个水潭收拾起来,再回神看我时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听得紧张起来……他看我一眼,“我后来在琅山的入口瞧见了你…瞧见……”
“瞧见什么?”我讨厌他这副卖关子的样子,却仍忍不住问道。
“瞧见你在调戏着守门的护卫,俨然一副登徒子的模样。”朔方拢了拢衣襟,“冉蘅,我竟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个……生猛如野兽的女子。”
我从没想过自己的酒品会如此之差,关听朔方描述便红了一张老脸。
我咳了两声,掩饰自己的尴尬,稍稍平复下来后骂道:“你怎的不拦着我。”
若他拦着我,我也不会这么难堪,我想他铁定是想看我的笑话。
“我倒是想拦啊,可你醉了酒,走路却不晃,跑起来脚下生风,同那菩提座下的鲲鹏一般,一会便没影了。”
“等我寻到你的时候,你正蹲在那仙君的院子里,对着那一院子的仙草上下其手,美其名曰:除杂草。”
“人家做好事还不留名,你干了一通坏事不说还摞下自己的名号,生怕别人不认识你一般。”
天!真是太丢人了,我将自己整个儿塞进锦被里,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感慨。
原着上琅山的那八个好汉是来讨公道的,我要是好好礼遇一番说不定能私了,却不想因为流景将他们全打了出去,那仙君也是上门来问问阿爹的意思,大不了损些宝贝,轻轻揭过,却又因为流景使我伤了那仙君,才落得这般凄惨。
左右都是因为流景,我一抹眼泪,这梁子算是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