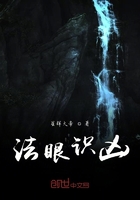魏主任的话,孬孩一句也没听到。他那两根干棒似的细胳膊搭在石护栏杆上,双手夹着八棱小铁锤。听着黄麻地、苘地、蓖麻地、庄稼地、簸箕柳地里传来“唧唧啾啾”、“叽哩呱啦”不同声音的鸟鸣,还有音乐般的秋虫“唧唧唒唒”歌唱,就像一个大舞台,在一起比赛演唱。逃逸的雾气缭绕着深红色、淡绿色、青绿色、深绿色、浅绿色的黄麻叶、苘叶、蓖麻叶、簸箕柳、庄稼地叶子和茎杆上,以及庄稼上,随着秋风呼喊“呜呜呜”的声响。蚂蚱剪动着翅羽的“啪啪啪”声,像火车过铁桥发出的“啪啪啪”,“啫啫啫”,“咯噔咯噔”的颤动声。那天夜里孬孩做了一个梦,梦中见过一列大火车,那是一个庞大独眼的怪物,黑乎乎,好长好长,像个大蟒蛇,趴着跑,比马快,要是站起来,那得多高呀。想着,想着,梦中的火车真的站起来了,上擎天,下着地,正高兴,屁股挨了几下。被后娘扫地的笤帚打醒了。“还睡,到什么时候了,还不起来干活。”笤帚打在屁股上,像用棍子抽打在一袋棉花上,不痛,只有热乎乎的感觉,却也吓得不得了哇。喊一声,“去,跳水去。这么懒,睡到这时也不起,想找死啊。”气不汹汹的样子,至今让他难以忘记。
朦朦胧胧的孬孩,继续沉浸在梦境里。他把扁担钩儿挽上去一勾,挑起来到井旁,打满提上挑起。水桶刚刚离开地皮,担着满满两桶水,骨头压得“咯崩咯崩”响,肋条胯骨连在一起。双手扶着扁担,摇摇晃晃,打着趔趄一步一步向前挪。
挑水要经过一座小石桥,上桥的路坡低一层,高一层,个子矮,前桶昂起,后桶下坠,不好走,顾前顾不了后。桥坡上像装了个磁铁,将前铁皮水桶吸得昂不起,后边桶摇摇摆摆。桥面撞上了前桶,桶碰上了桥面,水洒在小桥上。前桶水一汤,减轻分量,后桶下沉,桥面又滑,一脚踏上,像踩着一块西瓜皮,“咣啷”一声,扁担水桶扔在一边,从桥上滚了下来,自己不知用什么姿势在桥下趴下了,水像瀑布一样将他全部浇湿了,浑身湿漉漉的。他的脸碰破了路,路擦破了他的鼻子,好家伙,成了一个平面,一根草在平面上印了一个小沟沟。
几滴鼻血流到他的嘴里,他吐了一口,咽了一口,铁桶一路欢歌蹦跳,骨碌碌滚到桥下去了。他爬起来,去追赶铁桶。两个桶一个歪在路边的水沟里,不用再追了。另一个滚得老远老远,这时过来一个男孩子,把它当做皮球,走一步踢一下,“叽哩咣啷”,“叽哩咣啷”被那个男孩子越踢越远。孬孩一边追着,一边大声喊着,“别踢了,那是我的桶……别踢了,那是我的桶啊……你别再踢了……”
可是那个孩子装着听不见,还是一边踢,桶一边蹦跳,咣啷啷啷……咣啷啷朗……孬孩一边向前追赶,还是一边喊着。脚下满是四棱八骨的石子,绊得他趴下,爬起来继续没命地追,追,追……那个男孩根本不理会,照样踢着铁通,“咣当咕噜”,“咣当咕噜”向前踢,铁桶向前滚。嘴里不住地叫着,“你追呀,你快追呀,追上我,我就给你了,追不上,就别想要了。”
孬孩不让了,“你怎么这么欺负人呀,踢坏了,你赔我的桶。”
那个男孩也不转脸,回道:“赔你,你等着瞧吧,等我踢够了,高兴了就赔你。我若不高兴,滚你后娘那头去吧。”
“我求求你了,小哥哥,你还给我吧,穷人家有个桶可不容易呀。”
那个男孩软心了,“要这么说,我就可怜你一回。”说完一转脸,呵呵呵,他笑了。
“哎哟哟,我当是谁呢,你不是我大孬哥嘛,你怎么这样与我过不去呀。”小孬孩惊讶地叫了一声。
“呵呵呵……小兄弟,我与你开玩笑的,哪能将你铁桶踢坏了呢。要是真的踢坏了,我就真的陪你一个新的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把你引来,与你说个事。”
“说事,说事也不能这样呀,你看我,穷了破眼的,好看吗?”
“没什么的,咱俩不是好朋友吗?”
“还没什么,还好朋友,亏你说得出口。现在亏没人,要是有人看见了,多不好啊。你说,要问我什么。”
“你后娘真的像人说的那么厉害吗,除了喝酒,就是养汉,打你就像我踢你铁通一样,不当回事。”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嘛。”
“噢,说来确实像人家传言的如此了,难怪外人这么讲。你看你瘦的,成皮包骨头了,喊你瘦猴亏不了你吧。”
“大孬哥,别说了,没事别扯这个了。”
“好,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不扯就不扯吧,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咱们摆摆了。”说完,大孬走了。
小孬孩找回两只铁桶,重新打满水,挑起急急忙忙往回走。这么长时间,一担水没挑回家,到家这顿是少不了的,屁股等着挨板子吧。担起挑子,向前走……向前走……担子一颤一颤的,孬孩挑着担子回家迎着挨板子去了……
“孬孩!”
“孬孩!”
孬孩猛然惊醒,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后娘的板子挨到他的身上,惊吓的不得了。摸摸屁股,好好的,大孬也不见了,一切消失了。回想一次次梦,心里寒颤颤的,他定了定神,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八棱小铁锤从他手中脱落了,笔直地钻到下面的绿水里,溅起一朵盛开的白菊花般的水花,美丽极了。
“这个小瘦猴,脑子肯定有毛病。”魏广南走上去,拧着孬孩的耳朵,大声说:“过去,跟那些姑娘娘们砸石子去,你看哪个好,能不能从里边认个干娘来,省得再受后娘折磨了。”
小五随后跟着走上来,摸摸孬孩凉森森的头皮,说:“去吧,摸上你的锤子来。注意安全,砸几块,算几块,砸够了就耍耍,可不能随便乱跑哦。”
“你敢偷懒耍滑,我就割下你的耳朵当做下酒菜。孬孩,你信不信。”魏广南拍着孬孩头咧着大嘴“嘿嘿嘿”地笑着说。
孬孩哆嗦着一下,“信信信,割耳朵那不是小事吗。我一定好好干,不能让你割耳朵。”
“好吧,有你这句话,我就高兴了。好好干,亏不了你的。”魏主任夸赞着。
孬孩从栏杆空里钻出去,双手勾住最下边一根栏杆,身子一下子挂在栏杆下边。
“你找死啊!”小五惊叫着,猫腰去扯孬孩的手。孬孩往下一缩,身体贴在栏杆上,轻巧地像个小狸猫,呲溜溜溜滑了下去。就看小孬孩一翻身,贴在桥墩上,像墙上趴着的壁虎,回头看着魏书记和小五,嘴一咧,打着手,又一声跐溜溜钻到水槽里,将八棱小铁锤摸上来,爬出水槽,一弓腰不见了。
“这个小瘦猴,真有意思!”回头看着小五,说,“你呀,看你调皮,你还不如他,看他这个样子,他比你强百倍,调皮调出个棱出来。你能吗?就茶壶打把落了个嘴,嘟嘟嘟了。”魏广南一只手摸着自己的下巴,一只手指着小五,摇着头,呵呵呵笑着又接着说,“他妈的,这个小瘦猴!我倒要好好看看他了,会是怎么样。”
“要不队长派遣我们俩了嘛,他是我的好搭档,合得来。”
“我看到了,他的头皮是你手指头的鼓。棒棒棒……棒棒棒……敲个没完。你就没看到,他缩着脑袋,咧着嘴,硬撑着,随你敲。我看了就好笑,你和他怎么这么对家。听你一说,你们俩是个好搭档,难怪服服帖帖任你敲弹他的脑瓜崩。你没看到嘛,他的头皮被你弹得高一块矮一块。你认为他的头皮真的当你的鼓了。今后要做到好好保护他,不能随便敲来敲去了,要学会尊重人家,才是当哥哥的样。”
“这不是小意思吗,好戏还在后头呢。”
“那可不行,这儿不是娱乐场,也不是你们玩的地方,这儿是工地,不能胡来,竣工了,你们再演戏吧,我可不想看你们在这儿出事。一切安全第一,其他都是次要的。”
孬孩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畏畏缩缩地朝着那群女人走去。女人们正在笑骂着。说话很脏,都是女人见不得人的肮脏口头馋。“你那个主贵不想……”
“你这个娘们,就张着臭嘴说别人。”
“她不是人,可能昨天晚上……”
“你好,俺不像你,说出这样的话,俺才不相信呢。”
“就算有那个事,也碍不着你,拔了萝卜栽葱是俺自己的自由,与你何干。”
“好好好,拔了萝卜栽葱,你自由。”
“怎么了,你是不是坐不住了。”
“你这个女人,不叫人没得叫了,胡扯八拉做什么,谁像你,人不当,当鬼。”
“都别说了,来人了。”
“来人才好呢。”
几个大女人唧唧喳喳,说的满嘴不中听的话,嘻嘻哈哈,不当丑事,反而为荣。难怪人说,三个男人无好口,四个女人一台戏,只要女人在一起就没有好话说,不是肮肮脏脏的话,就是婆婆儿媳妇之间关系。有几个姑娘夹杂在里面,想听又怕听,听了觉得丢人,脸儿一个个红扑扑的,像个鸡冠花。
孬孩黑黑的,笨笨拙拙地出现在她们面前,她们的嘴一下子全封住了。愣了一会儿,有几个咬着耳朵低声俏语,“他是个孩子,听不懂,没什么关系的。”
“那也不小了,说话没个分寸。”几个女人看着孬孩没反应,声音又渐渐大了起来。
“你瞧瞧,你瞧瞧,这个孩子多可怜!都到什么节气了,还让孩子光着身,穿这么单薄。”
“不是自己腚里养出来的就是不行。”
“谁不说呢,你看这个孩子瘦的,还像个人样嘛。”
“听说他后娘在家里干那个事,太不是人了。”
“谁不说呢,男人在家也没挡了她。”
“她很专业。”
“专业个屁,简直就是个疯女人,男人不在家,都是被她气走的。”
“这下可好,男人一走好几年,在家行食了,没人看管她了,当家所为,简直就是鸡。”
“这个家当的好,家里像一窝狗,‘啁啁啁’,‘啁啁啁’。”
“那就更见不得人了。”
“噢,你也想这样吗?”
“你这个贼女人,说她,怎么说到我的身上来了。”
这些秃腚子,你一言,我一语,“唧唧喳喳”,竟说些没完没了不好听的人话来。
孬孩转过身去,望着河水,不再看这些女人。河水一块红,一块绿,岸上的柳叶像蜻蜓一样在树的周围不停地飞舞着,寻找住处栖息。
白果叶像金子一样,飘了这儿一片,那儿一片。树下的孩子们,捡着金叶,瞧着蜻蜓,“叽里呱啦”,不知在说些什么,“叽叽喳喳”一阵子跑走了。
一个蒙着一条红方巾的姑娘站在孬孩背后,轻轻地问道:“哎,小孩,你是哪个村的?”
孬孩歪歪头,眼角扫视了一下这位姑娘。姑娘嘴角上有一层细细的金黄色的茸毛,两眼很大,是她含在嘴里的,睫毛太多,毛茸茸的,显出一副惺忪的样子。
“小孩,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孬孩正和沙地上一棵老蒺藜作战,七八个蒺藜护在他的脚上。他不用手,却用脚指头,把一个个七八个蒺藜撕下来。然后再用脚掌去捻。哎哟哟,他的脚掌真出奇,像马驴骡的蹄子那样坚硬,蒺藜尖一根根断了,蒺藜一个个碎了,脚掌像个铁板,样儿没变。
姑娘兴奋地笑起来:“你真有本事,脚板像铁掌一样。”
孬孩看了姑娘一眼,没吭声,只是笑笑。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姑娘用两个手指轻轻点着孩子的肩头说,“你听到了没有,我问你话呢!”
孬孩仍不吭声,却感到她那两个温暖的手指顺着他的肩头滑下去,停到他背上一处的伤疤上。往日的旧景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你这该死的东西,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打死你,打死你。你怎么不死的,我那眼看你那眼就够,你不如死了好。你那个混爹爹,野死在外面了,将你丢在家,不是给我找罪受吗。你要是死了,我也安静了,省心了。”
一块坚硬的模版像下雨一样落在孬孩的脊背上,从此肩背留下了两处伤疤,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就和他开玩笑,说,“孬孩,你真棒,有钱没处花了,在肩背上镶上了两块通明“玻璃”,像个镜子,前面不照照后面,过好了。”孬孩明知人家在取笑他,他却不说话,只是苦笑着,任凭你们说去吧,反正这样了。
“哎,你聋吗,我问你话呢,你这是怎么弄的?”
孬孩依然不吭声,两个耳朵动了动。姑娘这才注意到他的两个耳朵长得十分特别,像宰相刘罗锅的耳朵,出奇地会一动一动的。夸张的说,又像个驴耳朵,特别惹眼。
“哎吆喎,你的耳朵真好看,还会动,像小兔耳朵一样。”
“孬孩,你以先也是这样的嘛?”
“哪能呀,哪有一下生会是这样呢,你怎么这么说呢,有可能是他后娘给拽的吧。”
“有可能。有了后娘,就有记号,要不说后娘‘好’了嘛。”
“这是做后娘的标记,还有那两块透明的‘玻璃’。”
“对对对,耳朵拽长了,背上又有两块玻璃,好美哦。”
“你这个贱女人,拿人痛苦幸灾乐祸。就不能亲者疼,非得仇者快,你怎么这么臊。”
“你臊,骂谁呢。”
“不骂你,骂鬼。”
孬孩装着听不见,只感到那只手又移到他的耳朵上,两个指头在捻着他那漂亮的耳垂。后娘扭耳朵的情景又出现了。“你怎么不长耳眼的,你聋了吗,你哑巴了,我问你话呢,你怎么不长耳眼的。”后娘说一句狠命地咬着牙拧一把,说一句狠命地拧一把,孬孩疼得咬着牙,咧着嘴,泪水吧嗒吧嗒往下掉,就是不吭声。“你死了吗,不能说话了。我拧死你……我拧死你……拧死你……你真是个臊女人养的……怎么这个样,像个死人啊。”
就这样,孬孩的耳朵经常被后娘这样拧。耳垂大了,也动了。只要听到有人大声说话,他的耳朵就动。是否是他后娘拧的,这样灵便,这是猜想,谁也说不准。“玻璃”是真的,总之,耳朵成了人们说笑话的话柄了。
现在被队长安排在这儿砸石子,妇女姑娘们见到孬孩,拿他开玩笑,议论起来,也没离开孬孩相邻相亲说的话题,都说到一个点子上了,是后娘所为。孬孩仍和往常一样,不言不语,任凭说去。
“你告诉我,孬孩,这些伤疤是……”姑娘轻轻地扯着孬孩的耳朵把他的身体调转过来,孬孩齐着姑娘的胸口。他不抬头,眼睛平视着,看见的是一些由红线交叉成的方格,有一条梢儿乌黑的辫子躺在方格布上,有点儿温暖。他觉得这个姑娘是个好女孩,不说不道,一个劲地关心他,就像自己的母亲那样问寒问暖,细致周到。他想说话,却又说不出来,睁着眼看着这个温柔可亲的大姑娘,泪水在心里,没有哭出来。“是狗咬?是生疮留下的痕迹?跌倒佧的?还是人打的?上树拉的?你这个可怜的小弟弟……你说话呀。”这位姑娘眼神盯着他继续追问着。
孬孩被这位姑娘温柔可亲的话语感动的泪水噙在眼眶里,敬重地仰起脸来,望着姑娘漂亮的脸蛋,和她那会说的嘴巴。他的鼻子抽噎了一下,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怎么了,小弟弟,我说的不对吗?”孬孩摇了摇头。姑娘温柔地问道,“哦,都不是,那是为何呢?”
孬孩哭得更伤心了,可仍是一句不吭。姑娘哪里知道孬孩内心的伤处,他不能说呀,完全的不能说呀。说了,话传到后娘那儿,不得要了自己的命吗,只能强忍着。
多少年来,都是自己强忍着,对谁也不说,对谁也不能说。别人说,只是猜疑,与自己无关,后娘拿他就没办法,反正自己没说,问心无愧。就是挨打,也觉得心安理得。
“杏子,你想认这个孩子做干儿子吗?”一个胖大女人冲着杏子姑娘脆生生地喊一声。
孬孩翻着白眼,转了过来,瞅着那位胖大女人。心想,你说的对,这位姑娘真好,我要是真有这样的干娘,算我有福气了。可是,不可能呀,人家年纪青青,是个大闺女,怎么可能做我的干娘呢?要是做我的干姐姐嘛,倒是可以的。可是,不可能有这个希望的呀。
“对,我叫杏子,前湖村的,离这儿十多里路,小弟弟,你叫我杏子姐姐好啦,我喜欢你。”姑娘笑嘻嘻地对着孬孩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孬孩惊讶了,刚才想的,不可能有这个希望,一转眼就成了。想喊姐姐,没能开口。
“杏子,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想招个小女婿啊?那可够你熬的,等小鸭子上架,还要十好几个年头哩……你受得了吗?”
“有什么受不了的,这是人之常情,别看人小,不次大劳动力。”一个瘦女人仍嘻嘻哈哈没有收敛地说着。
“你们都是臭老婆子,张嘴就拉屎。”杏子姑娘骂着那两个一胖一瘦的女人。
“黄花大闺女,你嘴里不说,心里能没这个意,哄谁呢。等你到了一定岁数,就知道了。”一胖一瘦两个女人又说了一句。
杏姑娘吭也没吭,言也没言瞅了他们一眼,她拉着孬孩的手到山一样碎石堆前去了,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摆好,说,“小弟弟,你就坐在这儿吧,靠着我,慢慢砸,能砸多少,就砸多少。”说完,自己也找了一块光滑石头,给自己弄了个座位,靠着孬孩坐下来。
十几岁的小孬孩,他能砸石子吗?会不会出现危险,谁也不知。只要魏主任放心,在一起干活的人也就放心了。要知端的好,请看下面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