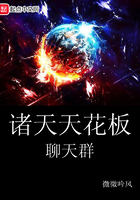整整一个上午,孬孩就像丢了魂一样,动作杂乱,活儿毛糙,有时把一大铲煤塞到炉里,搅得满屋狼烟滚滚,呛得人无法在屋里站着;有时,他又把钢钻倒头儿插进炉膛,该烧的地方不烧,不该烧的地方反而烧化了。惹得小铁匠张申不耐烦了,骂道:“你这个狗娘日的,怎么了,没魂了,你的心到哪儿去啦?心不在焉,欠揍了,是吧。”说着,自己敲打起来,嘴里仍是絮絮叨叨,“你看你,做的什么活。你是不是又想那个老东西了,认为我不行。对你说吧,不会再像上次了,让他们找来找去的。咱就一次成功,你也有面子。我要不行,你的手艺能学成吗?你这个小兔崽子。站着干什么,还不过来打。”孬孩也不吭声,过来摸起二等大锤,铿铿锵锵砸起来。“好好砸,用点心。”
小铁匠不在焉地骂着。孬孩全神贯注地砸着。他的小叫锤也学着他的爹爹那样,叮叮当当地敲着,点式着,孬孩跟着点儿,一锤一个准,一锤一个准,不偏不移,实实在在,小铁匠很满意,啧啧夸赞着,“好,好,好,砸的好。人不大,蛮有力气的,到底身子长肉了,没白吃。”
他忙得满身是汗,孬孩被催的周身是水。绝技在身的小铁匠兴奋劲儿从汗珠缝里不停地流溢出来,“怎么样,我的儿子,孬孩子。”
孬孩看到他在淬火前先把手插到桶里试试水温,手臂上被钢钻烫伤的地方缠着一道破布,似乎有一股臭鱼烂虾的味道从伤口里散出来。心想,师傅的确不赖,带这么重的伤,就像没事一样,胳膊手这么灵便。难怪老爷爷说,好孩子,错不了,你跟着他,一定有出息,也会一举成名的。只可惜,他老人家不声不响地走了。他的话就是座右铭,我可不能忘记。忘记了他老人的话,就等于忘记了他呀。这就是对我最后的嘱托吧,我不能辜负他老人的期望。孬孩的眼里蒙着一层淡淡的云雾,刚才情绪非常低落的心情一下化为乌有,精神提起来了,劲头十足了,也来威了。他抖擞神威,操起大锤,跟着师傅铿锵又砸起来……
九点钟了,阳光异常美丽,阴暗的小屋里,一道光线照着西壁,折射得满屋通亮。小铁匠把钢钻淬好,亲自拿着送到石匠师傅去鉴定,他的功夫是否到家。
这次送去,不像上次那个样了,孬腔说到脸上,钢钻一次次退回来。他有着百分百的把握,自觉自己的功夫超过了他的爹爹,不会再有上次那样的事了。确实像自己所想的,钻子拿去,再也没回来。自从他打出的钻子,石匠们用着,没象往日那么多了。坚硬无比,吃掉的石头,就像吃饭一样,那么轻松,无挂无虑。钻子不怎么磨损,烛火的事也就少了。背地里石匠们交头接耳夸赞着,一个说:“这个小东西算是行了,老家伙怨不得半夜三更,趁人不备,无人知晓,不声不响悄悄地走了呢。原来儿子的手艺超过他了,再不走,打出的钻子一比,水落石出,砍了蒿子显了狼,脸上多没有光彩。”
“你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水落石出,砍了蒿子显了狼了,脸上没有光了呢,这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他虽不是少年,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一代新人换旧人。有状元的徒弟没有状元的师傅,这个你不懂,怎么拿这个事来污蔑老人家呢。这样是对儿子的历练,根基才能扎得更稳,更稳固,更深。出走江湖,永立不败之地,你懂不懂。不懂,别张着臭嘴乱说话。”
“这位老兄说的对,不经一失,不长一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要是花喜鹊窝里抱鸇鹯,一辈不如一辈,那就糟了。人才怎么才能倍出,国家怎么才能发展,社会怎么才能进步。就说咱们修建的红旗涵洞吧,都像你说的那样,红旗涵洞还能修建吗,那不得停工下马。照你这么说,永远不能修建了。”
“你说的在理。”
“在理不在理不说,就说刚才他亲自送来钻子吧,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客客气气,让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他师傅做到了吗?没有呀。你看,他爹爹一走,他就来个新鲜的。当时谁也没把他当回事,上几次,咱们跑了多少个来回趟,结果怎么样了,还是不成。这回呢,谁也不去了,使了还想使,没有秃头的时候,能不说人家有本事,手艺好。你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更不能小瞧人。人哪有不求进步的,这就是发展,你就是倒退,赶不上新时代,跟不上新形势。”
“是是是,我错了还不成吧。”
“你也长点记性,不能光张着臭嘴说别人,看不到人的长处,你的弱点也就出来了。”
这边议论、评价、赞赏,暂且不提。
再看孬孩,活干完,没事,他扔下手中工具,蹑手蹑脚溜出炉匠铺,突然的光明也象突然的黑暗一样使他头晕眼花。略微迟疑,停了一下,他便飞跑而去,十几秒钟后便立在河水边缘。水边沿上的杂草棵子上没经秋风扫败的沾有这样那样的花儿,看着它好像知道他的心,在想着他那不声不响离去的老爷爷。在微笑中,他呆了,傻了。这些花儿、草儿好美,他却没放在心上。他哪里知道这些好奇的花儿都在敬慕地望着他,向他张开了笑脸呀。那些开着紫色花朵的水葫芦,还有水芡和擎着咖啡色头颅的香附草贪婪地嗅着他满身的煤烟味儿,感到那么的亲近。
此时的孬孩被河上飘逸着水草的清香和鲢鱼的腥味,急得嘴馋了,使他又想吃鱼了。他那圆圆的鼻子翅着,扇动着,嗅着这些的味道,肺叶活泼的像和平鸽的翅膀在展翅飞翔,心胸更开阔了。他又蓦然清醒,河面上白里、黑里、紫色的花儿,频频竞放。他看不厌,也不想走,被这些鲜艳的花儿迷恋了。眼睛生涩刺痛,仍目不转睛盯着,像看穿水面银般的亮色。他不再看了,提着裤头,直接下水,试试探探向前走。河水淹到膝盖,淹到大腿。弯腰使劲捲裤头,露出深紫色的小屁股,就像荞麦蒸的窝窝头。他立在河中央,四周水光一齐扑来,涂到他身上,脸上,眼里,黑眼染成了青色,揉了揉。
河水湍急,他站立不住,稍不注意,会被冲击倒退,他硬硬地站立着。脚底的沙一会儿被流水掏空,立在沙坑里。裤头全湿了,一半贴着大腿,一半在屁股后飘起来,裤头上煤灰染黑了身边河水。沙土卷起来,水混了,抚摸着他的小腿,琥珀的水珠挂在他黑黑的腿上,又滚到了河里。嘴角抽动着的孬孩像有什么事,轻轻地走,弯腰腿脚试探,摸索着,寻找着,一步一步向前走。走一段,停一停,歇一会儿,再往前走。
“孬孩!孬孩!你这个小东西,到哪里去了。”
孬孩听到小铁匠在铁匠炉铺门前喊叫,正走着站住了。他不能再走了,知道师傅找他有事,应当回去,不能耽搁师傅的工作。
“孬孩,你想死吗?你到哪里去了……”
“下河了。”一个人对小铁匠说,孬孩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龟崽子,到河里找死啊。”
孬孩听到小铁匠来到岸上,头也不回,小铁匠只能看到黑黝黝的背。
“你这个贼东西,到这儿做什么,咱是闲人吗,快上来呀!”
孬孩回首看了一下,小铁匠正挖起一块泥巴向他投来,“再不上来,我就……”话没说完,泥巴擦着他的头发落到河水里,啪……哗……河面荡开一圈圈波纹,一漾一漾荡开。又一坨泥巴擦肩而过,孬孩害怕了,师傅生气,还是和他闹着玩,他心里没底。听刚才喊叫声,师傅是生气了,误了他的任务,影响工程。他正想着,一块泥巴又扔过来,正打在他的背上,呱唧一声,贴在身上,他往前扑了一下,嘴唇沾到了河水,喝了一口水。他不敢再耽搁了,急转回身,“唿唿隆隆”躺着浑水上来了,挂着遍体的水珠儿的孬孩,站在小铁匠面前。水珠从肌肤上滚动,一串一串,“嘟噜噜”,“嘟噜噜”滚到脚下。
小铁匠举起他那只熊掌一样的大巴掌搞搞举起来,就要扇下来。要知他的师父手下能留情吗?要知详情,请看下面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