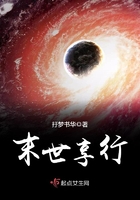眼看小铁匠张申于小五一场血战就要开始,谁是谁非,谁好谁伤,谁输谁赢就在眼前。老铁匠一直没搭理,听到这样,也没回言。看到其变,不能再等而视之了,好象无意地往前挪了一步,撞了他一下。小五猛然觉得老人那双深深的眼窝里射出一股慎人的冷风来。这股冷风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明晃锃亮。又好像在暗示着什么,提醒着什么,不要胡来,沉稳着为好,不要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惹出祸端来。小五的感觉和想象,使他顿时感到浑身肌肉松弛,不再像刚才那么刚强那么较劲了。此时的老铁匠微微扬起脸,极为随便地哼了一句说不出什么戏文歌词来。
“走江湖,闯天涯,挥刀戈壁,所向无敌。恋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吃尽了世上千般苦,走满天下,弹指一挥间……”
老铁匠只唱了一句多一点,声音戛然而止,听得出他把一大截悲怆凄楚悲惨的往事埋藏在自己的肚子里。可以想象,老铁匠的一生,是走南闯北老江湖的一生。他不光是铁匠这一拿手活,凭着他这大把年纪,轻轻稍微一伧,眍一望,使你周身酥麻,功底何等深厚,可想而知了。再看他这个儿子,为什么是独眼龙。也有说法的。常言道:能走三江口,不打独眼门前走。说明他阴,险,毒,狠;这家伙不是好惹的。手里十八磅的大铁锤,在他的手里,只是个小玩意儿。打一天的铁,除了流点汗,根本没当回事,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做累。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自行其变,省事饶人祸自消吧。
老铁匠看了小五一眼,一语不吭,低头捋起右衣袖,粗糙嘎嘣有力的大手伸进水桶试着水温,然后给刚打出尖的钻子淬火。他的小臂上有几个深紫色铜钱大小的伤疤,有圆的,有长的,还有别样的,尽管这些伤疤虽不象牛眼,看上去倒觉得又像古怪的人的眼睛,老是盯着自己。小五撇了一下嘴,恍恍惚惚中,像中了邪魔,不知东西南北了,飘飘悠悠出了铁匠铺门,回到自己工地。对于自己是怎么出来的,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像喝醉了酒,胡哩咣当,一摇一晃,跌跌撞撞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同伙问他,你去办得怎么样,孬孩是否听你的了,能否给杏子姑娘赔礼道歉,他却什么也不知了,“吱吱唔唔”,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别人一看,他是怎么了,去了一趟铁匠铺,变成憨子傻子了。小五为了掩饰自己,也就将计就计,糊里糊涂装了起来。一个下午也没说话,低着头做自己的活。直到第二天,装着清醒过来。人问他,他装作什么也不知,忽悠着过去了。
再说铁匠铺,一下午没见到小五的影子。至于小五什么样,他们根本不清楚。
孬孩心急如火,好不容易熬到歇炉。这个时候,还没到放工,他就急急忙忙跑到女人这边工地,一撸子跪倒,像鸡餐碎米一样给杏子姑娘磕头,让她求饶,能够原谅他,苦苦地抱怨起来。“姐姐,我对不住你呀,你的手……我不该,你对我那么好,我却……”
“弟弟,你是怎么了,姐姐没怪罪你呀。”
“姐姐你不知,我跑回去,方知自己错了,想回来向姐姐赔礼道歉,老铁匠爷爷说,马上开炉,想赔礼道歉,事过之后再去吧。那边一歇炉,我就跑回来了。姐姐,花钱是我的,石子砸不够,我来帮你砸。”
“又说荤话了,哪有够不够的,一天到晚砸多少是多少,你不知道吗?有什么要钱的,你的手我要钱了吗,我的手还不是和你一样。有‘血见愁’,比医药还好,既省钱,少受罪,你说不是吗?”
“是是是,姐姐说的是。”
女人那边有人说话了,“我说怎么样,打我的话来了吧。孬孩是个有情有义,有人心眼子的人,不会恩将仇报,反目为仇的。你看他,多诚实。上午是他疏忽,做了蠢事。孬孩,你说说,上午你为什么要这样,咬你杏姑娘大姐姐手的,让大家都明白明白。”
孬孩一五一十地将老铁匠老爷爷和小铁匠叔叔说的话原本宣科说了一遍。“你们看看,越说我说的越对了吧。孬孩一定有大原因,有大感情,有大恩惠。不然,他不会这样的。孬孩呀,要好好干,你一定能成为好铁匠的。也像你老铁匠老爷爷小铁匠叔叔那样有名。到时候,大家也能沾上你的光了。”
“您放心吧,只要有我那一天,你们要什么我给你们打什么,既好,又不贵,必定让你们心满意足的。”
“那就中,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呵呵呵,“好孩子,好好干。”大家一起夸赞。
杏子姑娘看着,心里酸楚楚的……孬孩的眼睛也酸了,杏子姑娘安慰孬孩,“不要伤心,事就这样了,有什么的,好好干,就算对得起姐姐了,可不要辜负老铁匠爷爷对你的期望,小铁匠叔叔对你的嘱托哦。”
“是,姐姐,我忘不了。”
过午了,太阳还是比较热的,头皮晒得发烫。孬孩从杏子姑娘姐姐的座位上站起来,告辞了大家,踱回铁匠炉。铁匠铺里很暗,他摸摸索索地坐在老铁匠的马扎上,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双手便火烧火燎地疼痛起来,他把手放在凉森森的石壁上,想起了过去的事情。
几天前,老铁匠请假回家拿棉衣和铺盖,说人老了腿值钱,不能让他吃亏,但也不能天天往家跑,在烘炉旁铺个铺,冻不着的。孬孩看到屋北边的那个洞已用砖块堵起来了,几缕亮光从留出的砖缝里射进来,斜照着老铁匠那件油光光、锃亮亮的旧棉袄和那条脱落毛的狗皮褥子,还有老铁匠的铺。
老师傅回了家,小铁匠成了一洞之主。那天上午进屋来,挺着胸,腆着肚,好言悦色地说:“孬孩,生火,老东西回家了,咱俩干。”
孬孩不相信他能完成任务,可又不能说,看着他愣了。心想,他……他怎么这么说话呢,这可是他的老爹爹呀,真没有礼貌,对老的不尊重,丧失了儿子对老的尊严,孝心到哪里去了。他只看,却没开口,心里嘀咕起来。
“瞪什么眼,想什么,你个狗娘养的,兔崽子!你瞧不起老子是不是?老子跟着老东西已经熬了整整三年啦,他那点把戏,我能不会。你是不是小瞧我了,是吧。实话于你说了吧,那点儿活,我全知道。”小铁匠自吹自擂起来。
孬孩懒洋洋地生起火,心里还在担心着。平日里你要亲自下手干一次两次的,我就不会有什么想法了。你一次皆无,我凭什么会相信你呢。孬孩的想法,小铁匠怎么会知道,老铁匠不在,小铁匠得意地哼着什么歪曲儿,孬孩根本听不到字袂,由他叽叽歪歪哼去吧,反正与自己无关。他把几支没来得及修的钢钻插进炉膛烧着。孬孩仍和老铁匠在的时候一样,慢慢地拉着风箱,使火更旺,照着自己黑黝黝的脸,透出黑红黑红的红光来。小铁匠忽然笑呵呵起来,“孬孩,你小子冒充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军准行,浑身都是伤疤。可是,你没那个福。年龄不相当,就是冒充,也不启事。”
孬孩想,谁想那样的好事了,都是你胡扯巴拉的。他只顾使劲地拉风箱,吹着火更旺,不让他挑出毛病来。对他的问话,根本没放在心上,一声不吭,风箱杆一出一进,长短一致。这是拉风箱的功夫,没有这样的功夫,是不够拉风箱料的。因此老爷爷说,我们铁匠有名气,都是靠拉风箱拉出来的,的确如此。风箱杆受磨损不说,样样都吃亏。
“你怎么不说话呀?”小铁匠张申问他。
“叔叔,你让我说什么。什么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军,这个我一点都不懂呀。”
“你没看过电影、电视,或者没听人说过去的战斗故事吗。”
“这个我上哪看,我的情况你不知道吗。别说电视,就算电影也没看过。就是有人讲给我听,我也得感激人家。我上见过听过这些呀。困得像死人一样,哪有时间出门与人说笑话听故事,看电影看电视那就更没有门了啊。”
“你真的没听人家说过。”
“听说过有什么用,擀面杖吹箫——一窍不通。半夜吃汤丸子,不知哪进糖了。”
“你说的倒也是,苦命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福。这回行了,工程进行一半,公社党委要安排一场电影,来慰问我们,有可能是战斗故事。到时候,我带着你,给你讲讲,提示提示,你就清楚了。”
“那我就谢谢叔叔了。”
“我再问你一句,这几天怎么也不见你那个浪干娘来看你啦?你咬了她一口,把她得罪了吧,狗儿子。她的胳膊什么味儿?是酸的还是甜的?你狗日的好口福,能尝尝女子娇嫩的胳膊。要是让我捞到她那条白嫩胳膊,我就像吃黄瓜一样‘咯嘣咯嘣’啃着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