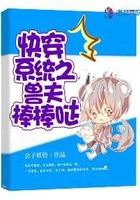赫林捂住隐隐作痛的胸口,眼睛看向别处。
“我们当他是挚友,可是他却对我们处处隐瞒,他当我们是什么,只是用来安抚他受伤心灵的工具?哈。”
辞安转向赫林,面色平静异常。众人的喧嚣在后面响起,如同海潮一般,一阵高过一阵。
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所有的人都围在广场的中间,兴奋地喊着:“十,九,八,七……”
赫林听到辞安的声音,低沉遥远,仿佛来自于不可触及的地方。
他说:“我十三岁生日那天,杀了人。”
烟火在身后炸响,只一瞬间,在高空中四处飞散,把这黑夜照耀得如同另一个白昼。
夏延用双手捂住嘴巴,睁大眼睛,耳边的一切噪响都忽然消失。
赫林看着辞安,呆住。
礼花如同流星一般,在天空中放射出最美丽的光华,四处交汇。整个天空,都是满溢的光。
“这不可能,不可能……”赫林如同失神一般,抓住辞安的胳膊,“你刚刚只是开玩笑,陈辞安,你又一次骗了我们,对不对?”
辞安突然笑了,从赫林手中挣脱,“你不是想知道吗?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赫林摇头,“我没想到会是这样,辞安。”
“没有关系了。”辞安看着在天空中盛放的烟火,脸上流转着奇异的色彩。
“你想的没错,是我杀死了陈善文,我的亲生哥哥。”
辞安一直都记得那一天。1998年的2月16号——他的十三岁生日。
那天与平日并无什么不同,父亲去上班,母亲和善文一早便在家里为他准备着生日蛋糕,善文特地从外地赶回来。
一切都如同被推上了一条轨道,慢慢前行,只是人不自知。
饭桌上,善文拿出他为辞安准备的礼物,是一块乳白色的小玉饰,穿着一根细细的白色绳子。
母亲责怪:“他都这么大了,你却送他这样的玩物,好像是女孩子戴的。”
善文笑道:“这是我跟同学去庙会的时候,特地求的。是护身符,很灵的。”
辞安把那枚玉佩放在手掌上,冰冰凉凉的,仿佛是一粒种子,即将萌芽。他欢喜雀跃地把它握在手心,不断抚摸着。
他说:“善文,谢谢你。”
母亲起身去看蛋糕烤熟的程度,善文靠近辞安,低声问他:“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吗?”
辞安偷偷地看着母亲,有些胆怯,“我想,去公园里走走。”
“你多久都没有出去过了?”
“自你走后,他们每一次出门,便把我反锁在家里。”
善文看着辞安,不禁觉得难过。他还这么小,却要承受这些成人都无法承受的东西,他只不过想要出去走走,竟然都这么艰难。
善文拍着他的肩膀,“没问题,等会儿妈睡午觉的时候,我偷偷地带你溜出去。”
辞安咧开嘴笑。
在十三岁之前,善文一直都是一道光,轻轻照耀辞安昏暗的小小天地,让年幼的他看到生命的另一面。只是看着他,辞安便觉得安心和温暖,好像所有的阴霾和孤独都会消失无踪。
所以,他才会那样地追逐着他,贴近着他。好像,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
那个光亮的、完整的、健康的,他一直想成为的自己。
母亲睡着之后,善文便带着辞安悄悄地出了门。这天虽已是冬末,阳光却是异常的温暖,一缕一缕地掉落在脸上,好似会发出声响。
善文和辞安在街道上欢叫着奔跑,伸开双手,如同鸟儿一般,翅膀承载着冬日里最美丽的光辉。鸟儿盘旋,不休不睡。
飞鸟自由翱翔,所以天空不远。
到了通往公园的那座桥边,辞安像往常一样,闭着眼,让善文牵引他过去。
辞安闭着眼睛,被善文在一旁拉着,一步步地前行。只感觉到阳光在视网膜上扑打,一片亮红色,照得眼皮有些微微地发痒。
这样的一段路途,辞安时常会记起。在精神病院的黑暗病房里,在每一个辗转的梦里,那个时候,善文拉着他,好像是牵走了他所有的重量,他闭着眼睛,那么信任地跟着他。
那种信任与安心,任谁,都不会再有了。
那短短的一段路,却走了很长的时间。快接近桥尾的时候,辞安听到一声訇然巨响,甚至都来不及反应,只感觉身子往前一倾,好像被人猛地推倒一般,跌落在岸边。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刚刚走过的那座木板桥,已经从头至尾断裂,裂痕一直到辞安的脚边。
辞安想要喊,却完全发不出声。他看到善文在急流的河水中挣扎,他一边痛哭一边跟随着漂流的善文奔跑,他看到善文伸出的手,直直地指向天空。是那只手,抚摸着他的额头,对他说:辞安,你有什么生日愿望,我都会满足你;是那只手,把那玉佩轻轻地给他挂上;是那只手,在他这十三年里给他阻挡了所有的风雪和艰难。
他看到善文爬上阁楼,拍着他的后脑勺,叫他的名字:辞安,要吃饭啦,不然妈又要骂了。
他看到善文泪流满面地对他的父母吼:辞安只能待在这里,他哪都不能去,他没有病,他只是孤独。
而现在,他看到善文陷在湍急的河流中挣扎,他却什么都不能做。
那只手终于消失。
辞安跪倒在地上,只觉得浑身仿佛都被割裂一般的疼痛,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人,曾短暂地成为我们的光,陪伴着我们走过一段路。
然后他离开,只剩下我们。
可是,我们余下的人生,却都陷进了那道光消失以后的阴影里。
即便是往后那么长的岁月,辞安仍无法摆脱善文离开后的阴影,他一再逼自己去相信,善文并没有死,善文只是离开了一阵,他会回来,他会看到他,和他像往常一样说话。
然后,他便坚信。
这年的冬天,雪是异常的少,偶尔飘散落地。只稍稍抬眼,便已不见踪迹。
寒冷,却如同一把烟雾一般把人轻裹,渗进裸露出的每一寸肌肤。
辞安站在监狱的外面,穿着厚重的棉衣,等着狱警的传达。天空仍是一片朦胧,迟迟不肯褪尽云雾。辞安清楚地看到自己呼出的白色气体,在面前簌簌地下落。
这个城镇,不知不觉,已经待了这么长时间了。
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暂时告一段落。
辞安看到那场风的来临,所有的鸟儿,顺着这场从南方飘过来的风声飞翔。那些刺骨的寒冷,仿佛都只是披挂在身上。辞安抬起头,看着那些鸟儿成群飞过,翅膀掠过天空,遗留下条条的斑痕,如同掌纹。
再次见到父亲的时候,父亲仍是清瘦,但气色已经转好。
辞安把烟递给他,父亲却摆摆手,并未接过,“我已经很久不抽了,这烟带在身边,恐怕也只是被旁人抢去。”
辞安默默点头,把烟放下。
“有你母亲的消息吗?”父亲又问。
这似乎是永恒的话题,每一次,父亲都在关切着这个。
辞安心中隐隐作痛,说:“没有。”
父亲垂下眼睛,轻声叹息。
“辞安,我昨天做梦,梦到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在终审的法庭上。我站在被告席,听着法官的宣判,看着坐在下面的你母亲,满眼都是绝望。我以为我可以给她很多,却最终什么都给不了她。”
“母亲希望的,只是你能健康安心。”辞安说,“这件案子,不是说可能会重审吗?也许事情会有转机。”
“哎。”父亲叹气,“除非找到当年的那个毒贩子,让他为我做证,也许还有机会可以减轻量刑。不过,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海茫茫,这是没有指望的事。”
“他竟没有被判刑?”
“他并未直接参与,并且为求自保,供出了背后的许多人。所以只是轻判了十二个月。”
“这不公平。”辞安低声说。
“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言?我们的感情,付出,永远都不是等价交换。我早已看透。”
“那个人,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父亲想了一会儿,说:“我只知道,他姓苏,开庭那天,他带了一个小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别的,就再也没有印象了。”
“姓苏?”辞安似乎有些恍然。
“怎么?”父亲看到辞安面色异常。
“没什么,只是也许,事情会有转机也不一定。”
“辞安,我已不再奢望。我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现在只是希望,你能够好好地生活下去,不被任何事物所干涉。”
“我会的。”辞安看着父亲。
“辞安,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我现在很好。”
“与表姨他们相处得可好?”
辞安垂下眼睛,点头。
父亲叹息,“我知道,你一直都只会说好,从小就是这样。受到委屈,被人欺负,只要问你,你都说你很好,没有什么。可是辞安,我们这一生当中,快乐的时间并不多,若是连痛苦都不能表达,凡事只会忍耐吞咽,那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
辞安只觉牙齿都在打战,浑身的血液都冲到头顶一般。他用力地按住自己的右手,直到掐出青紫色的淤痕。
“你从未对我说过这些。你从来没有告诉我,除了忍耐,我还能做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长那么大,人们只会远远地看着我,小心翼翼地应付我。所有人都只拿我当怪物。你说,你什么时候对我说过,辞安,你不应该忍耐,辞安,你应该快乐。你甚至连拥抱都没有给过我一个,现在你又在这里夸夸其谈,对我说,辞安,你要过这样那样的生活,你有什么资格,你凭什么?”
父亲低声颤抖着说:“辞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遭遇了这么多,这一切,都不应该由你来承受。”说着,伸手去抚摸辞安的额头。
辞安厌恶地把脸别过去,背着他。
父亲怔怔地看着他,慢慢把手放回去。
“我要走了,不早了。”辞安站起身,朝门外走去。
“下次来,你多给我带一些可口的饭菜吧,监狱里的食物太难入口。”父亲说。
辞安看着坐在那里,抬起头望着他的父亲。他知道,他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雄心壮志,有着坚强内心的陈勋成了。他已经是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了,尽管他还不到五十岁。
辞安轻声说:“再见。”
父亲看着他,突然就笑了。辞安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笑容,满眼都是感怀与释然。在这一刻,他终于还原成最初的那个父亲,没有岁月的摧残、世事的变迁,有的,只是面对子女的最原始的情感。
辞安突然原谅了他。
父亲轻轻地对他说:“辞安,再见。”
父亲的药已经渐渐用完,这些时日,体重也明显增加。夏延看着脸色一天天好起来的父亲,觉得宽慰。
夏延去药店拿药。
像往常一样,店员一看到她,便把提前备好的药包起来,递给她。
“你再清点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店员说。
夏延甚觉感谢,把药袋打开,清点了一遍医生开出的药。
“全部都在。”夏延笑。“真是太感谢你了,还有你们王老板,若不是他肯帮忙,我真不知会怎样。”
“王老板?”店员一脸莫名,“我们店主不姓王啊,姓张。”
夏延抬起头,“不是叫王明伦吗?”
“我在这里都快两年了,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们店主姓张,这是不会错的事情。”
夏延仍未反应过来,“那……我在这里为什么可以拿药?”
“哦,那是因为有人已经替你付过钱了。”
“付过钱了?”夏延已经隐隐地觉得不安,“你可知是谁?”
“不知道名字,只知道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个子高高的。他每两个月便会过来结算一次。”
夏延恍然。
她早该想到,就算真是赫林所说的,是王明伦开的店,可以赊账,但这么多次,店员也从未向她提及过欠款的事。
她突然有些恨自己,赫林对她隐瞒的这些事情,她竟然一直都没有发觉。
那么,赫林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
所有的真相,都让人不敢去想。一想,便会难忍。
她记得赫林被一群人围着打,满脸是血,赫林说:这是我赚的钱,为什么要给你?
她记得赫林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上,漫天的星光都黯淡下去。她说:赫林,你不要再去打架了。
赫林说:你不懂,我有我要做的事。
原来这就是,赫林要做的事。
夏延捂住嘴巴,只觉得心脏颤动不已,似乎随时会跳出来。
而这所有的一切,她却从未知晓。
赫林看到陈向明,远远地走过来,看看四周,对他挥一挥手。
赫林小心翼翼地跟过去。
陈向明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了几个纸袋,递给赫林。
“新货,你瞅瞅。”
赫林轻轻地把袋子打开一个口,往前走了走,照着巷口路灯的光看了看,又用手点了一点,放在嘴中,对陈向明点点头。
“我说,你小子上道倒挺快的。”陈向明咧着嘴,“你年纪轻轻的,这么拼命做什么?”
赫林把袋子收好。
“自然是有要用到的地方。钱,有谁会嫌多?”
“好。”陈向明哈哈大笑,“我就是看中你这股劲,够聪明。”
说着,把手搭在赫林的肩上。
赫林把肩膀别过去,甩开他的手。
“怎么着,呵,想出来混就别老那么把自己当回事,混就要混得彻底一点。不然,别人怎么服你?”
赫林低声说:“有人过来了。”
陈向明还未来得及反应,便看到对面突然出现一小群人,有五个左右,飞快地往这边跑来。
他们还未来得及躲闪,那群人便已到眼前。
陈向明走过去,不动声色,“你们干什么?”
“原来是陈大哥。”后面的女孩轻声地说,慢慢走到前面来,看着他们,“东区的地盘这么大,陈大哥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怎么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
陈向明笑,“姓苏的,以前你做的那些龌龊事,兄弟们可都是憋了一肚子的火。我念你是个女的,不跟你计较,你他妈的也别扶着脸就上墙。”
“哼。”苏尘笑着说,“这么说,陈大哥是不给面子了?”
陈向明并不搭理她,转身要走,被最前面的一个男的拦住了。
“你们想干什么?”陈向明有些慌,但依然做出镇静的表情。他早已在心里思量过,他们只有两个人,若发生什么冲突,恐怕只会对他不利。
“我们不想找麻烦,不过最近,日子确实不太平。这不,听说你来了新货,我们就想来帮帮忙,替你验收一下,看看是不是假的,免得向明哥被骗了。”
陈向明还想说什么,被赫林从后面拉住。
赫林贴近他,在暗处,把包放在他手上,低声说:“你赶快走。”
陈向明看了他一眼,眉头凝在一起,脸上都是滚落的汗。
“你快走,这里我还应付得来。”
陈向明也不犹豫,退后两步,立即转身往巷子深处跑去。
有人马上大步去追,被赫林一把抓住,狠狠地摔在墙上。
“你快去追,”苏尘吩咐着,“你们两个留下来,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赫林撑起双手,仿佛是一扇墙,挡住这个狭小巷子的入口。
“你们谁都别想过去。”
“赫林,陈向明这种人,你何必像狗一样护着他?”苏尘语气轻蔑。
“不用你管,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他护着那个入口,眼睛在这漆黑的夜里发出光亮,他听到自己极力抑制的喘息声,好像随时会混着眼前的那团影子一齐把他击倒。
“不想死的话,赶快给我滚开。”最前面的男人大声地吼了一声。
赫林仍是一动不动。
“你他妈找死!”
那人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块,重重地砸向赫林的头部。
黑暗,是不是就只有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去习惯它的样子。
赫林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一路上,每迈出一步,都仿佛能听到骨骼发出的响声。疼痛都早已失去了知觉。
到了门口,赫林扶着墙站立,艰难地用右手拿着钥匙。突然听到旁边的走廊上有微微的轻响,他转过头。夏延蹲在那边,把头埋在膝盖里,好像已经睡着。
赫林默默地低下头,许久,打开门。走到夏延面前,轻轻地摸着她垂下的头。
夏延睁开眼,看到赫林,连忙站了起来。
“我刚刚过来找你,你不在,我不小心睡着了。”
赫林不说话,只是看着她,默默地笑,却只觉满脸僵硬。
“你的脸怎么了,怎么都是血。”夏延惊呼道。
眼前的赫林让人不敢正视,满脸都是肿裂的伤口。鼻孔,嘴边,都是血迹,还未干涸。衣服从衣领直直地被撕裂到腰部,裸露的皮肤全部都是一块一块的淤青,让人惊心。
夏延看着他失神的眼睛,用手抚摸着他脸上的伤口,“怎么会这样子,赫林,你到底……”
赫林俯下身子,亲吻了她。
夏延完全愣住,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赫林已经紧紧地拥住了她。
“赫林,你干什么?”夏延挣脱着。
赫林如同不受控制一般,用力地抱住她,亲吻着她的脸颊,脖子,每一寸赤裸的肌肤。
“赫林,你疯了?放开我。”夏延哽咽着,只觉得心底仿佛落了一块巨石,沉沉地往下坠。所有的语言,都无从出口。
夏延从未见过这样子的赫林,凶狠,暴戾,满眼都是欲望的光。他撕扯掉夏延的衣服,在夏延身上勒出一道道血痕,却视而不见,只是奋力地抓起她的肩膀。淡淡的灯光照耀着他狰狞的脸孔和满脸的血迹,在夏延越来越黯淡的视线里,逐渐融化。
辞安看着苏尘走过一条条的街道,在一家杂货店稍稍停留了一下,买了什么,然后往市郊的方向走。
辞安走进那家杂货店,见到店员便问:“刚刚那个女孩子买了什么?”
店员看着辞安,仿佛看怪物一般。
辞安自知唐突,便又说:“哦,那是我妹妹,我担心她最近交上了什么不好的朋友,所以便处处留心她的动作。”
店员仍是一脸的怀疑,有些不情愿地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她买了一些炒货,还有一些年糕。她倒是经常在这里买东西,也没见过和别人一起。”
辞安心中自是有底。
谢过店员,辞安快步地走出去,看到苏尘仍未走远,便又牢牢地跟上去。
苏尘走进一条小小的巷子,往四周看看,便小心地走进去。
辞安在二十米以外的距离,紧紧跟着。到了巷子口,稍稍往里面探视,便看见苏尘正在与四五个年纪偏大的男人说着什么。
辞安记得那几个人,上次在夜里偶然碰到苏尘时,便是他们几个在她身边。
辞安深深吸了一口气,躲在一边,等着苏尘的动作。
大约过了十分钟,苏尘从里面走出来,手中多了一个小小的黑色纸包。辞安逐渐明了,但仍不动声色,并且快速地拐进一旁的巷子。苏尘停下来,仿佛察觉有异样,回头看了看,也并未发现什么。
苏尘向通往西区的街道走过去。
辞安跟随苏尘在一幢破旧的房子前停下来,看着苏尘走进去。
如果说东区,是富商、官员们的居住地。西区,则是刚好相反,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几乎都是穷苦不堪。辞安看着这栋房屋,四面的围墙已经几乎塌陷,露出青灰的斑驳颜色,木质的大门上面全部都是裂痕,仿佛稍稍用力,便会碎裂开来。
辞安轻轻地推门进去。
苏尘看到辞安,慌忙地站起身来,旁边坐着的中年男人回过头看着他,一脸的茫然。
辞安一眼便认出他,原本准备的许多话,都拥堵在嗓子眼,无从说起。
五年前的那个下午,就是面前这个人,站在法庭上,指着父亲的脸,说出他的名字。
他一直都记得他的样子,深深地记得。四十岁左右,略有些胖,眼睛总是慌张地晃来晃去,好像受了惊吓一般。
而此刻,他站在他的面前,辞安看到他满头的白发,脸上的皱纹纵横,如同刀刻。只有五年,他却仿佛老了二十岁一般。
“你怎么来这里的?”苏尘走到他面前,满脸都是讶异。
辞安并不理会她,直直地看着那个中年人,苏尘的父亲。
“你还记得我吧?”
“你是谁?”他好像并无印象。
“呵,也对,你陷害过的人那么多,又怎会记得?”
“陈辞安,你给我滚出去。”苏尘大声说。
“陈勋成你还记得吗?那个当年被你陷害,现在还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待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的人,你还记得吗?”
“陈勋成?”苏尘父亲倒吸了一口冷气,又细细地打量辞安,“这么说,你是他的孩子,仔细看来,倒是有几分相似。”
辞安看不得他的冷静,只觉胸中似乎有火焰灼烧一般。
“对,我是他的孩子,自从他进了监狱之后,我们便一直经受苦难。而你却毫发无伤,依然在这里,和你的女儿一起干着肮脏的勾当。”
苏尘看着辞安,脸色瞬时变得苍白。
“所以,你是来讨还公道的?”他依旧不紧不慢,“你想怎么样?”
辞安稍稍镇静下来,说:“很简单,只要你去告诉他们我父亲是被冤枉的,你做了伪证。现在事情过去那么久了,你不会受到任何的刑罚。”
“陈辞安,你不要太过分。”苏尘怒视他。
“过分的,从来都不是我。”辞安压低声音。
“很抱歉,我没有要帮你的任何理由。”苏父从椅子上缓缓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眼看就要回去房间。
“不。”辞安正视他。“你当然有。”
苏父停下来,有些莫名地看着辞安。
辞安不紧不慢地说:“你看到你女儿手上的黑色纸包了吧,那里面是什么你自然知道。如果我现在出去,打上一通电话,警局不过就在旁边,要过来也只是不到五分钟的路程。”辞安看着他越发紧绷的脸,继续说:“当然,你们也可以让我消失,但是我猜,你没有这个勇气。”
苏父沉默了半晌,说:“我会考虑你说的话。”然后走进里屋。
苏尘一把把辞安推开,狠狠地说:“好了,你目的达到了,你还在这儿干嘛,还不快滚。”
辞安低下头,吐出一口气。
“谢谢你,苏尘。”
“谢我?”
“你是故意的吧?”辞安直说。
苏尘看着辞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一开始,你就知道我在跟踪你,你故意让我看到你在与人做毒品交易,并带着我来到这里,让我有借口与你父亲交涉。你在帮我,对不对?”
苏尘有些黯然地笑,嘴上却仍说:“你别自作多情了,我为什么要帮你?”
“为什么?”辞安仿佛没听到一样,继续问她。
苏尘定了定神,低下头,语气变得低沉:“你是否还记得,五年前,在法庭上,给你糖葫芦的那个小女孩。”
苏尘眼中有微微的光,闪动不息。
辞安皱起眼眉,注视着面前的苏尘。
“那是……你?”辞安似乎不敢相信。
“对,那便是我。”苏尘笑。
“可是……怎么,你会是他的女儿?”辞安仍未能明白。
“这也便是我那个时候,在那里的原因。”
辞安恍然。
“我第一次看到你时,你独自一个人,坐在小小的角落里,满眼都是恍惚。所有眼前的喧闹好像你都听不到一般。后来在开庭时,我坐在对面,一直都看着你。我看着你和母亲,听到宣判时,满眼的绝望。我虽年幼,可是尚还懂得人情世故,孰对孰错。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诬陷的。后来我便同父亲离开那座城市,来到这里。我无数次想着,若是再次遇见你,我会作何反应。可是,看到你的那一刻,你坐在人群之中,仍是我初见你的表情,我便知道,你如同是我的罪,我永远都无法补偿你。”
“苏尘。”辞安轻轻地说,“你不需要补偿我,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苏尘摇头,眼泪掉下来。
“辞安,过去的五年,这仿佛是我唯一的事业,我每一天会告诉自己,我要看到他,然后告诉他所有的事情。若不是靠着这些,我不会存活到现在。现在你说结束了,可是我要如何停下来?”
“苏尘,你可以停下来,停止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你应该过正常的生活。”
“你并不知道,我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我在孤儿院长大,在整个城市最昏暗的那条街上。十二岁之前,我已熟练所有偷盗的技能,每天傍晚都在街道上逛,看到哪一家的灯暗着,便会翻窗进去,偷取一点财物。那个时候,只是想着,存够了钱,我便会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虽然如此厌恶这种生活,却无法离开它,所以更加恨自己。直到有一天,我被人发现,被打得浑身淤青,甚至无法站立。我躺在街上,感觉像是要死去一般。父亲就是那个时候看到我,然后他什么也没有问,就把我领回家。他从来没有结过婚,直到现在,但是他待我像亲生女儿一般。辞安,他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人。”
“可是,他让你去贩毒。”
“他已经很久不做,这是我私下做的,他起初并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辞安眼中都是茫然。
“辞安。”苏尘看着他,只听到自己轻声的呼吸,“我是被抛弃的人,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得到幸福,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们都是被抛弃的人,我们被生活抛弃,被时光抛弃,或是被自己抛弃。
幸福,却永远都是天上的星,只能远远地看着。以为靠近,一伸手,却是空落的风。
赫林推开窗,堆积的光线一下子涌进了屋内,仿佛瞬间变换的白昼。
夏延蹲在房间的角落里,抱着膝盖,头发蓬乱地披散下来,眼睛如同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波澜。
赫林走过去,弯下身,看着她,然后伸出手去抚摸她的脸。
夏延厌恶地用手推开他,把脸转向一边。
“延。”赫林低声说,“对不起,我好像被附身一般,完全不受控制。”
“你变了,赫林。”夏延说。
赫林猛地站起来,抓起旁边的杯子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满脑子想的都是陈辞安。是啊,我变了,他却永远不会变,他根本就是个疯子。”
夏延靠在墙上,看着恼怒的赫林,一字一字地说:“他不是疯子,你才是疯子。”
赫林只觉大脑一阵冲撞,抑制不住,伸手打了她一个耳光。
夏延捂住肿起的脸,看着他,说:“赫林,你做任何事,我都不会怪你。”
赫林跪下来,用双手扶着额头,好像有千万根针在刺一般,只感到深入骨髓的痛楚。
“延,我们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夏延扶着肩膀,仿佛寒冷一般。“也许,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怨不得别人。”
有敲门的声音急促地响起,赫林失神般地站起来,用双手抹了一下肮脏的脸,去开门。
陈向明站在门外,并没有进来的意思,“你快准备一下,有生意等着。”
赫林挺着身子,“我拿件衣服,马上跟你去。”
赫林走进屋子里,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准备离开。
“赫林。”夏延叫他,声音都在颤抖,“你不要去,你停下来,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