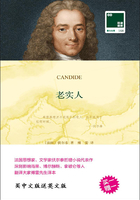尚海眼里含着泪花,发觉自己说错了,歉意地对两个人说:“哦,没什么!你们俩听好了:有些事情并不是有了爱情就可以解决的,更有些人是有了爱情后变得更加孤独的!可以流浪的时候就尽情去流浪,等到好多事情成为流浪的羁绊时,流浪已经成为不可能,成为一种想象!”说完又喝了杯酒就先走了。看着尚海的莫名其妙,果儿气得非要追上去问个究竟,良品硬是按住她:“尚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她肚子里最能盛东西了,今天是多喝了两杯才露出来的,一定是王红烈那个王八蛋!”
岁末年尾,王红烈所在的科室很忙碌,见果儿和良品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王红烈很是不自在地笑了笑,让其他人都出去了。果儿顺手将门反锁了,靠在门上不说话,良品踱着方步把办公室上上下下看了个遍,慢条斯理地说:“王科长最近很忙呀?”
“唉,机关那点事可不就忙在这个时候了,写总结啊,做报告啊……”
“行了!”良品声音小却有力地喝住了王红烈的沾沾自喜,“尚海到底怎么了?”
“尚海?没……没什么呀?”王红烈故作镇定地说。
“连尚海这么宽厚的人都快撑不住了,一定是有什么事。”
“她……她跟你们说什么了?”王红烈支支吾吾地问。
“什么也没说。你还不知道她?她为了你们家那些所谓的荣誉,所谓的面子,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你说不说?再不说就别怪我声高了啊!”
果儿也帮腔:“别跟他费话!”
王红烈一看实在不行了,才道出了实情:“我们管辖范围内的一个效益不错的公司,各种证件和手续其实都应该归我们管,可是那老板和市区局的关系好,所以不在我们这办,有个资料非得我们这盖章不可才过来。我们局长想治治他,就让我变着法地为难他们。没想到他们不仅不服软,还让人给尚海打恐吓电话威胁我。尚海是让那电话吓着了。”
良品:“你是怎么解决的?”
王红烈:“我能怎么解决?就吓唬吓唬呗!他们敢怎么样?已经没事了。”
良品:“没事?你知道她多失望、多恐惧吗?”
王红烈:“真没事!不知道为什么市里一个领导知道了,也没声张,暗地里把这事给和解了。可尚海还是怕,我也没办法。”
良品:“我跟你说对尚海好点,替她想想,要不然没你的好,办公室在这长着呢!”
说完良品和果儿急匆匆地走了,直奔尚海家。
带着一身的冷气和大包小包的东西,良品和果儿出现在尚海面前,尚海看到她们高兴。
“哟!我们的公主快成人来疯了!”
“来,亲一个!马上新年了,你开不开心?”
尚海招呼着小阿姨又是端茶又是洗水果又是买菜又是做饭的,大家在一起分外开心。果儿说:“这段时间我不出去,我准备搬到你这住一段时间。”
尚海用目光询问着良品:“住倒是没问题,就怕朵朵影响她。”
良品劝慰到:“没事儿,她本来就是夜猫子,听说我们的朵朵也睡反了,她俩正好。”又是一阵开怀的笑声,大家却都谁也不看谁,谁都怕被对方发现了眼里转着的泪花。
什么是爱呢?就是让对方融化在这幸福里,却不露任何痕迹!
北方的一月没有雪
爱一个人,爱到惶恐!
深爱着他,在他讲述每一段曾经幸福的回忆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一部分,于是很幸福,幸福得溢满他的过去。爱他,爱得只想沉浸在此刻的幸福里,幻想着,这个有着长长乌发的女子,这个时常眯起媚眼的女子,应该终日依在他怀里。然而,怀揣的不安是什么呢?是未来,是那个美好的未来!自欺欺人地去填补他的过去,无限荣耀地占据着他的现在,而未来的某一天,他会被谁从自己身边无情地带走呢?不敢想!于是,明知道未来对自己来讲很渺茫,但是仍愿意把它当作一个愿望来追求,还要告诉自己:终有一天能实现。那……就好好爱吧!
在这冬日细碎的暖阳里,良品幽幽地思恋着那个令她心仪的男子。在她,听到他的声音就会禁不住地幸福。而这一切在目风眼里,她幸福的样子不过就是一个小女人的傻笑。她喜欢目风丰富的面部表情,就是肯定的时候撇一撇嘴角。而在目风看来,良品的快乐就是冲他吐一吐舌头。每当她欣赏着那个深爱的脸庞发出慨叹“啊,我心爱的儒雅小生!”时,目风始终不能认同自己属于该派,总是反驳着:“我哪‘儒雅’呀?我哪‘小生’呀?”然后凑过来非要良品亲一下。良品自顾自地忙着手里的活,微笑着断然拒绝:“不!”目风当然不肯罢休,凑得更近了,良品的笑会更开怀一些,但仍然要说:“就不!”于是目风强制执行了,良品只觉得自己如此幸福,像绚丽的颜色落下来然后一直向四面晕染,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灵的契合。良品喜欢静静地诉说:“遇到你以后,我越来越喜欢倾听。和你在一起,我最喜欢的是安静;最开心的事情是抚着你的脸醒来,摸到你硬扎扎的胡子茬;最想和你做的事情是一起锻炼,一起读书,一起晒太阳,一起安睡;最爱的事情是让你把我宠坏!”
如果每个在一起的日子都是一个静静的午后就好了,只需要彼此拥有,彼此静静地感受!
早早地就在怀念一场雪的到来。雪花纷飞是一种少女的情怀,大雪铺天盖地就是一个晶莹、纯粹的世界。而今年的一月多数时候是阴阴的,却不见雪飘,好像总不能释怀。马上就到新年了,而新年对于尚海来讲不是憧憬,不是希望,是一段日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过着过着就只剩日子了!
王红烈陪着他爸开始了辞旧迎新的“上供”,这“年”仿佛也只有他们忙得热火朝天了。对于尚海来讲这个人无论是在自己眼前晃,还是招呼也不打、头也不回地离开,都变得遥远,变得无足轻重,变得陌生。唯一印证他们曾经有过关系的就是女儿朵朵,她的眉眼,她偶尔的一个姿势、一个动作都很像他。
从傍晚开始,朵朵就一直焦躁不安,不停地哭闹,尚海也不知道她是饿着了、冷着了、凉着了,还是哪里疼,着急得满头是汗,想着让王红烈早些回来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可是催了好几次他都说脱不开身,后来就是电话通了也不接,再后来就是关机。尚海给王红烈他妈打电话,王红烈妈妈说一定是着凉了,让尚海先拿热水瓶捂一捂,因为有客人王红烈一会儿才能过来。尚海照做了,朵朵果然安静下来,一边吃着奶一边睡了,可就是不能放下来,刚沾枕头就大哭,弄得好像枕头上长了针一样。尚海把枕头从上到下摸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就只好抱朵朵来回在屋里踱着步,手酸了、胳膊麻了仍然放不下。
大约九点多的时候,尚海想倒一下手,只见朵朵的小肚皮一鼓一鼓的,随即将刚吃的那些奶全都吐了出来。孩子并不哭,尚海吓晕了,看着那些半消化的汁液从嘴里涌出,流进孩子的脖子里、耳朵里,她足足愣了有五秒钟才反应过来,哭喊着:“朵朵!朵朵!孩子你哭出来呀!睁开眼看看妈妈!看看妈妈!”不知道是怎么样跨出的家门,不知道是把电话打给谁了,反正良品、目风、果儿相继赶到了。不知道找到的是什么医生,反正见到穿白大褂的都让他来救朵朵,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迈哪一只脚。
等一切的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平静地告诉尚海,朵朵只是常见的小儿消化不良。“可是,她吐了那么多奶!”“正是因为吐出来了才没什么大碍,吐不出来才不好办呢!”“可是,她为什么不哭呀?”“这么小的孩子有多少体力?折腾四五个小时早累了,一会儿输液扎针她准哭。”大家都吐了一口气笑了。尚海透过玻璃窗看见朵朵的小小身体,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往下掉,任凭良品和果儿怎么劝,她也不肯去休息。良品张了张嘴却又咽下了,这个时候提王红烈也许是雪上加霜吧!而果儿望了望目风,又看了看良品,于是三个人尴尬地分头向南北的窗口走去。这楼里异常安静,安静得能听到暖气蒸腾的声音。
直到早上六点,朵朵被送进了病房,尚海摇着她的小床闭着眼。护士过来量体温,她马上惊恐地睁开眼,把护士也吓了一跳:“我看你的手还在一下一下摇着小床,不知道你睡着了。”尚海无奈地笑了笑,脸色惨白。一直到她第二觉醒来,已是十点多了,果儿正逗着朵朵玩,小家伙居然乐出了声。尚海头沉沉的,良品提着大包小包的吃的走了进来:“这一晚上折腾得,赶紧吃些东西吧,趁热啊!”
尚海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你不吃饭,朵朵可就吃不上东西了啊!”果儿和良品连哄带吓唬,好不容易又让尚海吃了些。过了会,果儿和良品老是对视一下,然后支支吾吾地有话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
“怎么了?”尚海焦急地问道。
“王红烈,可能……可能有点忙!”
“他忙不关我的事!”
“不是,是……尚海你千万别上火呀!”
“良品,怎么你也说不清话了?”
“朵朵……的爷爷,今天早上去世了!”
“说……说什么呢?”
“我们也觉得很突然,但是……是真的!”
“喝酒……过量……引起心脏病……没……”
“别说了,我知道了!朵朵是有预感的!从他们父子走后她就闹,如果朵朵的哭闹能够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事情也不可能发展成这样!”尚海贴着朵朵的小脸,“朵朵,这一切你是知道的!”眼泪下来了,她却不知道是为谁流的。而此时,一个更大的灾难和不幸在中国的南方暴发了——雪灾!王红烈父亲的追悼会因此而显得萧条,任何人都不想沾惹这个不祥的不吉利的事件,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更何况王红烈的父亲只不过是王红烈的“大树”而已,他的去世只是王红烈自己——这个尚未长成的小苗失去了依靠而已,而别人仍可以再寻一个可以庇护自己的大伞,或许还会因祸得福,找到更为合适的支点,凭空一跃!
你是我在二月纳入箱底的霓裳
书上说趴着睡会压迫心脏,目风也总是提醒良品:“乖乖,躺好了睡啊!”良品总是在享受身体全部舒展的同时在目风的爱抚里重新缠上他。
“我得想个法子做个枕头。”目风若有所思地说。
“做枕头干什么?”良品缠得更紧了些。
“唉!解放我的胳膊呀!”话一出口,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怎么?受委屈了?”良品抬起头,看着目风。
“没……没,幸福还来不及呢!”
幸福的人们总是想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爱,而对于目风和良品来讲,这一切又何必呢?这样珍爱的一个人,这样的一段感情,只需要安静地放好,就足够了。
目风微微起身,准备点燃一支烟,良品嘴里阻止着,眼睛却欣赏着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目风唏嘘了一声,大有不可阻挡之势,打火机“咔”一下,一支烟悠闲地燃起。倘若一个男子吸烟的姿态都如此有味道,那么爱他的女子也只有陪伴了。目风尽量让烟雾避开良品,俊朗的脸上带着雅致的笑意:“我一周不过一包烟,不上瘾的。”良品默不作声,盯着他点头,忽然伏过身去,追索目风嘴里淡淡的烟草香……
早上的太阳刚一露头,良品就拽着目风起床,看着他实在耍赖,干脆将被子全部夺过来:“懒虫,起床了!今天都腊月二十五了,我得把被子拆洗一下,不然就邋遢一年了。”目风跳下床,双手环住良品:“我不怕冷,我有天然毛裤!”良品开心地笑了,两个人额头顶着额头:“你再来件天然毛衣就成猴子了!”良品催促着目风赶紧穿衣服。等把被罩拆下来了,良品盯着露出来的那床被子足足愣了有一分钟,目风走近她问:“乖,看什么呢?”“这被子……”“我奶奶给我带的,这被里被面听说还是她的嫁妆呢!”
红色,耀眼的红色!
花朵,富丽堂皇的花朵!
鸳鸯,情投意合的鸳鸯!
目风有些不知所措:“你不喜欢,我们今天就去买一床被子!”良品着急地摇着头,眼里带着泪花,趴在目风肩头:“没……真的没,想到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床被子,我更觉得幸福!”
“噢,我的乖乖如此容易满足呀!好了好了,我带你出去转转吧!”
因为良品坚持将被子拆洗好,等两个人赶到早市时,赶集的人们大多都已经满载而归了。
“有点晚了吧?”良品失望地说。
“这个时候刚好,许多小贩开始降价处理货物了。”金色的太阳将两个人呼出的哈气照耀得几近透明。
“在早市上买菜呢,最好要那些骑自行车驮大筐卖的,那些基本上是自家产的,绿色、健康;其次是那些开三轮车只卖单一菜品的,他们是二道贩子,肯定是从菜农手里直接采来的;那些品种全,用纸箱整齐码放的,基本上就和我们到超市和菜场买的菜一样了,买那些就失去了来早市的意义。”每件事情到了目风这里总能讲出一大堆条条道道来,良品幸福地笑着,目风淘气地哈了一下她冻得发红的小脸。
“讨厌!脸上长斑了就找你!”
“凭什么呀?”
“因为你哈我了!”
“哈一下就长斑呀?”
“可不是吗?”
“谁说的?”
“我妈说的!”
“哈哈!”
“呵呵!”
两个人有说有笑,大半圈下来,冻得良品的牙都开始打战了。一对卖山药的夫妇在一大车上好的山药前忙碌着,良品紧紧地挽着目风的胳膊,跺着脚说:“真冷!”那个套着厚厚军大衣的女人瞟了一眼良品说:“穿那么点能不冷吗?”什么意思呢?是出于好心的劝告?还是一个女人本能的嫉妒?良品微笑着默不作声。“好好卖吧,卖了咱们买过年的衣服!”也许是怕良品因为这句不中听的话走掉了,那男人对女人说完,冲良品憨憨地笑了笑,表示对顾客的歉意。良品刚刚挑好了,目风就将一件厚厚的军大衣披在她身上,良品很是诧异,目风说:“十五元一件!”
“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