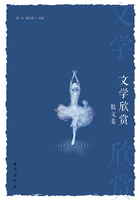但是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就不同了,钱先生用同样俏皮的语言再加上博闻强记,驱遣古今中外故事,以《管锥篇》作者之渊博,信手拈来经典名言与这种不伦不类的连篇歪喻相结合,遂构成钱先生特殊的幽默风格——谐中有庄。荒诞中有机智,其理往往颇歪,然而歪中有正,正者,其论据之经典性也,其推理之层层演进也。他在《谈教训》中提出一个歪论:“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这本是反语,亏得他说得振振有词。有时还在征引多种经典之后,层层演绎,明明是诡辩,逻辑上漏洞全然不顾,却作雄辩之状,其歪理歪推之气魄不能不使读者又惊又佩。为使得他的这个幽默歪论显得庄重,他引用西方格言、王阳明的《传习录》、基督教哲学,言之凿凿,以歪语警世:“世界上的大罪恶,太残忍……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连续的歪理歪推,越推越歪,最后也有歪打正着之妙。他的推理,常常歪加比附,十分可笑,然而,其中也有钱先生的愤世嫉俗的机智。
在散文中,他是一个过度张扬的智者,他的幽默常常失去幽默家视为要义的宽容。钱先生的幽默,过分富于进攻性,属于硬幽默,与林语堂、梁实秋、余光中散文中自我调侃的软幽默正成对照。当钱先生的尖刻发挥到极端的时候,读者虽能莞尔而笑,但又不免叹息:何其毒也!如他嘲笑把文学研究当成毕生事业的人偏偏不懂文学艺术,毫无鉴别力。这倒也罢了,可他还要刻薄一番:“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这样就差不多把幽默变成刻薄的讽刺了。
17.挑战文坛权威——从《十作家批判书》谈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十作家批判书》,对中国当代十名当红作家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进行了“批判”。批判的对象都是十分走红的文坛真正的明星,不像影视明星那样具有泡沫性,这自然就引起了海内外传媒广泛轰动。这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商业性的成功炒作。其次,在学理上,很可惜,其严肃意义一时间并未引起充分的注意。太原日报文学副刊在北京开了一个座谈会,除了少数,青年表示理解以外,一些著名文学评论家大都以为这本书的批判态度不够严肃。
公平地说,书中有不够严肃的文章当然是事实。例如,把余秋雨的散文的文化智性与诗性相结合的创造性成就,简单地归结为“煽情”而一笔抹杀,轻率地归结为“文化口红的游荡”;把梁晓声对当前文坛的严肃的道德批判,贬之以“道德激情的作秀”,嘲笑他的相当警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是一种“力不从心的越轨”;等等。
但是本书中大部分文章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思想的自由、人格的独立”的精神,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冲击着文坛,正是中国当代文坛生命力的表现。由于中国的特殊文化传统,权威崇拜的意识特别深厚,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比之西方更突出的特点是,从权威的重新阐释/解剖开始。托古改制,曲解经典;只有到了五四时期才出现对权威进行直截了当的批判。正因为这样,胡适才在《尝试集》中写了那首终于被挖倒的《威权》,而郭沫若则振臂高呼:“我是一个偶像破坏者。”
1980年,朦胧诗大辩论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我写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第一句就是:“在历次的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
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规律的作用,在90年代,王蒙的权威才遭到无情的挑战。当王彬彬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时候,批判了王蒙“聪明地”“躲避崇高”。王蒙起初轻率地嘲弄对方由于发表文章困难而以批判名人来出名。结果连王蒙自己都感到后悔。目前这本书中对王蒙的批判只是换了一个角度,说他“在世故中把玩‘批判’”。分析比当年是深化了,但从根本上来说,只是继承了当年的主题。至于对余秋雨的批判虽然有诸多不当,甚至有尖刻、轻率之感,但是,这也不是作者朱大可的首创。对于余秋雨的批判目前发展到几乎有点走火的程度,但这对于一个伟大国家的思想论坛的活跃来说,仍属正常。一切思想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直线的。用黄子平先生80年代的一句话来说,总是有点“深刻的片面”的。钱钟书、王蒙、余秋雨、梁晓声、汪曾棋受到的赞扬已经太多了,肤浅的溢美之词本该使人感到肉麻的,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些作家的权威和成就早就受到过质疑,只是相当一部分质疑都是在学术论文中,读者是有限的。例如对于钱钟书,早有一批上海的博士生在论文中,对于他的脱离现实,居高临下,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只是没有在大众媒介上有足够的反映。这本《十作家批判书》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拿钱钟书的红极一时的《围城》来开刀,那标题就相当醒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钱钟书氏的《围城》被当成经典是近年的事,早在90年代初,笔者在香港一家报纸上就发表过《围城为何未列入经典?》的文章。当然,“伪经”用语不够文雅,但是,批评的勇气是可贵的。从夏志清先生把《围城》说成可能是现代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讽刺小说以来,还没有一个评论家在艺术上对《围城》的弱点进行过艺术分析。文学史家们先是出于政治工具论的局限,对之视而不见;继而走另一个极端,对其艺术上的弱点,麻木不仁。《十作家批判书》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很值得深思。例如,钱氏这种模仿西方“流浪汉小说体”串连人物的方法,中间既无曲折,又无呼应,是不是包含着艺术上的失误?小说以幽默见长,但是,就故事情节的整体来说,除个别章节之外,却缺乏喜剧结构。一味靠不伦不类的比喻取胜,对于小说艺术来说,这是不是一种缺陷?作者还认为钱氏“理智大于情感”,小说的构思“局部大于整体”。主题是结婚好比围城,在城外的人想进去,在城里的人又想逃出来。可是主人公方鸿渐则恰恰相反,他本不想进人婚姻之城,而是被别人拉进去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理有据,而且还引用了徐讦先生和吴组缃先生的类似的批评。
当前中国文学评论中文化评论、反本质主义批判、新历史主义批判的声势压倒一切,文学批评的任务据说就是作哲学文化和历史文本的分析,艺术分析据说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了;在这样的时候,出现这样严肃的艺术批评,实在令人鼓舞。
如果要说这本书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漏掉了一个更该批判的权威——陈忠实,没有用分析钱钟书的方法来分析《白鹿原》的艺术上的失误。
18.《废都》:灵魂对肉体的败北
这一阵,老是听到文学界的同仁说,今年是文学的淡季,发行量上不去,但是突然出现了一本《废都》,作者是颇有知名度的贾平凹,居然大为轰动,6月份第一版印了37万册,才过一个月第二次印刷又印了11万册。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刊载文章评论《废都》,文艺界内部也议论纷纷。在北京,据说买《废都》要排队,而在福州压根儿就买不到。好容易找朋友转了好几手弄了一本来看,40万字的长篇花了我整整三天,仔仔细细念了一遍,总的印象是有点失望。
这本书有极其严肃的一面,那就是写西京古都的文化风俗和文化界名人的笔墨,作者用他非常精练的叙述语言刻画了他们的空虚的心灵以及心理的和社会的环境,其中不少章节写得相当精彩,这是一方面。作品的另一方面则是写主人公庄之蝶的性生活,写得相当露骨,直接写到做爱的有几十处。本来有了一系列正面的描写,已经够惊人的了,可是接着又出现几个方格,下注:作者删去几百字、几十字等等。这就引起了很多非议。许多论者认为这是故弄玄虚,也有的认为这是一种商业广告的变形——吊那些低层次读者的胃口,对于贾平凹这样一个有成就的素称严肃的作家是极不相宜的。的确,这种作法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这部作品的品味,但我总觉得光是这样简单地批评一个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现象,似乎不够深刻。
贾平凹在《废都》中有关性的描写和“省略”,固然有不够严肃的一面,但是也有比较严肃的一面。
首先,关于主人公庄之蝶的性行为,作者在行文中十分强调一个对比,那就是他和他的妻子牛月清的性生活总是很难成功,以致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而和他的外遇唐宛儿、阿灿及至柳月却完全相反。这是由于他和他的妻子牛月清之间缺乏情感,甚至动物性都很少;而在别的女人身上则除了动物性以外,还有某种精神的寄托和交流,因而他的性生活就分外地泛滥。
作者也许是有意通过这种对比,向读者揭示某种人生体验的奥秘,不管这种奥秘是多么不深刻,但是你却不能说他不严肃。
其次,作者为主人公庄之蝶设计的结局是鸡飞蛋打。他的妻子坚决要与他离婚;他最钟情的情妇唐宛儿被她的原夫绑架回乡;而阿灿则在把自己的面容毁了以后,再也不和他相见;那个与他偶尔有染的柳月又嫁给了市长的儿子;而他最早的情人和他打了一场名誉官司,他又彻底失败了。因而他变得颓废,最后等于是精神崩溃,在出走西京时中风,倒在了候车室里。
这个结局是很严肃的,很显然这是一个名人的精神毁灭的悲剧,其意味是相当深刻的。
但是,许多读者,包括很有欣赏力的读者,似乎都没有为这个悲剧所吸引;相反,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被贾平凹那种大胆的性爱描写所转移了。这是由于贾平凹一心追求《金瓶梅》式的感官刺激,有时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了。其实他在这方面缺乏深邃的理解。远一点说,他的作品不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富有社会批判性;近一点说,不如米兰.昆德拉对人性的深层探索;就是比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缺乏超越的诗意。
对于《废都》的评价之所以这么纷纭,是因为作者的故作玄虚的删节和性行为描写的空前露骨。但是,这一切都只有商业性的实用价值,于作品的艺术价值只有某种干扰,而无助益。
为了对《废都》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艺术成就的评价,我想暂且撇开其中性行为描写的干扰。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作者在删节时,再忍痛割爱,删彻底一点,或者在再版的时候,删一个洁本出来,我想完全不会损害本书已经达到的艺术水平的。
撇开一切干扰不谈,贾平凹这本书最没有争议的部分要算它的叙述语言了。和当前一些新潮派的小说家追随西方叙述风格的潮流相反,贾平凹独树一帜,他追求的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述风格。这种风格既有一种唤起传统文化趣味的功能,又有一种展示当代市井语境的趣味,更难得的是有时颇具幽默感。贾平凹语言是很丰富的,他对现代书面语言、古典雅言和口语显然有过相当精细的琢磨。他在本书中曾借庄之蝶的太太朱月清为了退一件小商品和售货员吵架的事表现了他的语言才华。朱月清问:“吵起架来用书面语言还是用粗话?”庄之蝶让她用书面语试试。朱月清说:“你们强词夺理,混蛋,小王八羔子,****娘的!”庄之蝶说:“……****娘应该说****母亲的,这就文明了!”正是因为在语义上这样辨析毫厘,贾平凹才显现出了独特的语言魅力。
贾平凹对传统小说趣味的追求看来十分着迷,《废都》中甚至有些模仿的痕迹,最明显的就是贯穿首尾的那个似疯非疯的收破烂的老头子了。他顺口念出来的歌谣都有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意味。这显然是从《红楼梦》中的“空空道人”那里套来的,但可惜的是这种模仿太坐实了,缺乏“空空道人”那种恍惚迷离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