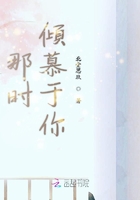李自成原来的计划,是准备在招抚吴三桂后,立即登极,然后派大军南下去完成他的一统事业。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吴三桂由一再拒抚到公开对抗了,他决定先东征吴三桂,凯旋后登极,再大举南下。在东征以前,他只能派遣少量部队向南行进。到东征前夕,李自成还一直认为麻烦都出在吴三桂身上,不认识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由他进入北京地区引起的。在进入北京地区以前,农民军的天地是比较宽广的,它可以从陕西到山西,或者经河南到南方各地,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它前进,它会不断壮大自己。而北京的明王朝与清廷的矛盾继续存在,农民军在反明或抗清的斗争中都处于有利的地位。自从进入北京地区,明王朝这座阻碍清军的挡风墙不存在了。虽然李自成暂时还没有想到清军南下的问题,但他感觉到了北京的食粮问题。北京的存粮不多,“用昌平知县李日晋为户政府从事,监各仓米,不满十万石”,有的记载是“不满四十万石,仅支数月”。李自成曾派遣了郭升、董天跋、白邦政、董学礼等先后率领一万多人南下山东和淮北地区。白邦政和巡漕方允昌领二千人索饷,至淮上,见明兵拒守而止。还有“四百人号数千,沿河而南,诡称催粮”。董学礼所部步骑五千人在淮、徐一带,受阻于南方明淮抚路振飞的军队,也不能前进。明军扼守淮河以抗农民军。北京得不到江南漕粮的供应,时间稍长便会发生粮食恐慌。李自成需要派很多军队去占领江南,才能获得漕粮的接济,但他这么做要受到山海关吴三桂军队的牵制,一旦大军南下,北京防守力量薄弱,吴三桂很可能袭击北京。当时李自成还没有把清军将要进攻北京地区的情况考虑在内。《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自成命刘宗敏、李过等东御吴三桂,别遣贼将南犯淮、徐。贼破京师,兵渐分,粮不足,既守城,复防边,支吾不给”,北直各地都驻有农民军。这就是农民军进入北京后面临的困难。即使李自成消灭了吴三桂的军队,也不能解决北御清军,同时又要南下江南的难题。明降官纷纷建议李自成派大军南下,王孙蕙在三月廿日进表中说:“燕地既归,宜拱山河而受箓;江南一下,当罗子女以承恩。”
廿一日都司董心葵被释出狱后,“备言中国情况及江南势要,自成大赏之”。写劝进表的周锺常说:“江南不难平也。”魏学濂上三疏,其中一疏是粮,一疏是平江南。明尚宝司卿吴家周甚至“见牛金星,言南方脆弱,愿包纳饷银数十万,免其刑掠”。几乎是一片南下声。李自成曾试图用招降的办法去解决南方问题。他在三月要明降官吏史可程写信劝他的哥哥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投降,驰檄左良玉、高杰、刘泽清投降,檄文说:“大顺国王应运龙兴,豪杰响附。唐通、吴三桂、左光仙(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赐彩缎黄金,所将兵卒先给四月军粮,俟立功日升赏。抗命周遇吉身具五刑,全家诛戮,刑赏昭然。尔等当审时度势,弃昏就明,身享令名,功垂奕世,孰与弃身亡卤,妻子戮辱。大福不再,后悔噬脐,檄到须知。”这些招降活动都不成功,除史可程的信未送达外,有的不愿降,有的要观望形势,农民军的大队人马不下江南,不但不愿降的不会降,就连有可能迫降的也不会降,不用武力就解决不了问题。
在吴三桂问题的干扰下,李自成把大举进兵江南的事放下来了。对吴三桂的招抚自然更是失败了。吴三桂在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听说北京已被农民军攻下,就率兵退守山海关。李自成在北京找到吴三桂的父亲明京营提督吴襄,要吴襄写信去招降吴三桂,由牛金星代笔,信上说:
“汝以君恩特简,得专阃任,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计,而汉高一见韩、彭,即予重任,盖类此也。今尔徒饬军容,徘徊观望,使李兵长驱直入,既无批吭虚之谋,复乏刑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吾君已逝,尔父须臾。呜呼!识时势者亦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不若反手衔璧,负锧舆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而尔殆有疑于括也。故为尔计,至嘱至嘱。”李自成派明降将唐通持这封信去山海关,携带四万两银子犒赏吴三桂的军队,并令农民军二万人跟去守关。这封信以吴襄署名,表达李自成的意思,至少牛金星写好后要念给李自成听,得到李自成的同意。信中提到的“强敌”,指的是清军。信中说:“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哭,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分明指出吴三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弃汉归魏,即投降农民军,一条是违楚适吴,隐指吴三桂投奔清廷,因为吴三桂要仿效伍子胥违楚适吴,这个吴国除掉是清政权外,别无一个政权可以作为吴国让吴三桂去适,如果吴三桂要渡海逃到江南,那就不是违楚适吴的问题了,而且吴三桂有几万人马,也不能都渡海而逃。这说明农民军是知道吴三桂有投奔清廷这条路的,错误在它认为吴三桂投降农民军“易”,投奔清廷“难”,看不出这两条路对吴三桂并没有那么大的难易之分,吴三桂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会弃“易”就“难”。事实逐步表明了这一点。吴三桂看信后,起初同意赴北京投降,让农民军守山海关,但走到中途变卦了,又回师袭破守关农民军,据山海关反抗李自成。吴三桂曾提出希望面见明太子,因此李自成同其他首领计议了一番,派人在四月四日见到吴三桂,答应送给他定王,不送明太子,作为农民军再次招抚他的条件。吴三桂的回答是:必得太子而后止兵。他送交了一封绝父书,发布了讨李自成的反动檄文。吴三桂在绝父书中说:“侧闻圣主宴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
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这是要吴襄自杀。吴三桂在发布的檄文中说:“闯贼李自成以么麽小丑,荡秽神京。日色无光,妖氛吐焰,豺狼突于城阙,犬豕据于朝廷。弑我帝后,刑我缙绅,戮我士民,掠我财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寿凄风;
元勋懿戚之诛锄,鬼门泣日……诚志所孚,顺能克逆。义兵所向,一以当千。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打着恢复明王朝的旗帜来对抗大顺农民政权。反动檄文在北京产生了一些影响。吴三桂迟早要投靠清廷了,檄文写得这么猖狂,而山海关不过是弹丸之地,吴三桂只靠本身的力量能经得起李自成大军的进攻吗?不能,这里有弦外之音,但李自成没有听出来。被李自成忽视的清廷,没有在沈阳睡觉。多尔衮在三月没有接到农民军对清国书的复函,也没有获得农民军占领北京的情报,但他从迟起龙的回报中知道农民军东进和占领大同的消息。有一件事引起多尔衮的注意,就是三月六日吴三桂放弃宁远等六城入关,过了几天清军发觉了,占领了宁远等六城,十六日向清廷报信说:“大兵既下前屯等城,宁远一带人心震恐,闻风而遁。”
为什么在这时“闻风而遁”呢?多尔衮自然不了解吴三桂放弃宁远的经过,但他会猜想到这与农民军由大同近逼北京有关。在他主持下的清廷,“随下令修整军器,储糗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战云出现在天际了。四月四日,是崇祯下葬的一天,也是李自成招抚吴三桂完全失败的一天,清大学士范文程向摄政王多尔衮上进占中原的奏启:“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
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殆悔将来者亦此时。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况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也。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邮,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范文程不知道农民军已占领北京,明廷在上月就覆灭了,仍以明廷作为清军进攻的对象。但他感觉出来现在是清军“进取中原”的时机,不可丧失,并且不再拘泥过去清廷要联合农民军来夹攻明廷的方针,主张清廷单独派兵去占领内地,这也适应清廷当前的实况。范文程认为:“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意见,他看出清军“进取中原”的成败,决定于同农民军角逐的胜负,而不在击败明廷。明廷这棵大树在范文程的心目中业已枯槁了。而攻取北京和东征吴三桂的农民军,却始终没有把清军作为主要敌手来观察问题。过去的政策对范文程不能没有影响,例如他说:“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这是皇太极时的语言,他仍然保留下来,和奏启中富有进攻性的主要精神相矛盾。“进取中原”是范文程提出的长远目标,“直趋燕京”是他建议这次清军南下的目标,万一情况不许可,他主张在关内占有一个据点,“顿兵而守,以为门户”,作为以后进兵的基点。前两个目标尽管过去已有人提过,但只有到这时,它们对清廷才比较具有现实的意义。多尔衮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因此范文程到盖州汤泉养病去了。过了一两天,农民军占领北京的消息传到沈阳。多尔衮认为清军南下是刻不容缓了。过去清廷认为在明王朝存在的情况下,清军虽略取关内的一些土地,这些土地终不为清廷所有,汉民“携贰”不服,特别是当农民军势力壮大以后,清军入塞后更有遭到明军和农民军夹击的危险。所以清廷才送国书给农民军,企图与农民军“协取中原”,利用混战在关内取得立足点,一步步达到占领内地的目的。现在农民军覆灭了明廷,替清廷减少了一个敌人,清军只要击败农民军,就可以夺取中原了,问题变得简单起来,用不着有很多的顾虑了。多尔衮还不清楚吴三桂的情况,不过发生了这种变化,清军南下的道路总是平坦多了。到盖州的范文程被召来计议,范文程自然竭力主张进击农民军,认为农民军“可一战破也”。又说:“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谈到了“统一区夏”的问题。四月七日,多尔衮祭庙。九日他统领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三分之二兵力以及汉军恭顺等三王和续顺公兵,共计十几万人南下。到达辽河时,多尔衮询问洪承畴关于军事上的一些问题,洪承畴先称颂清军“天下无敌”,“流寇可一战而除”,接着说:“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提醒多尔衮不能轻敌。洪承畴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
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提出加强政治宣传工作,整肃军纪和规定赏罚条律等事项,改变过去清军沿途掳掠的作法。关于进攻农民军的战术,洪承畴主张采用偷袭的办法,说:“今宜计道里,限日时,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收其财富以赏士卒,殊有益也。”多尔衮同意洪承畴的这一番建议,却未接受洪承畴关于辎重在后,精兵在前的意见,仍整队而进。清军渡过辽河后,于十四日进入蒙古村落住宿。这次清军走的仍然是过去几次入塞的路线。虽然清军已经占领了宁远等六城,但多尔衮并不想走山海关这条路,因为从墙子岭一带进入密云,不但到达北京的路程最近,又无重关阻挡,更重要的是,正如洪承畴所说,可以“出其不意”地对农民军发动突然袭击。在战云密布的天空下,李自成既和吴三桂的冲突日益激烈,又面临着清军的进袭,不久还会发生粮荒,难点很多。而农民军并不很清楚自己所处的困境。当时南方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有利于农民军用武力去占领。明南方统治集团以陪都南京为政治中心,内部矛盾很多,四分五裂,主要分成三种势力,代表人物是史可法,左良玉和马士英。史可法任明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控制着陪都、江南和淮扬地区。崇祯在二月令史可法以督师名义出兵“勤王”,史可法迟迟不动,到四月一日才出师。渡江至浦口,听说北京已被农民军占领,史可法立刻就回南京去了。其他“勤王”兵跟着散归。这种情况反映了明南都的虚弱,史可法虽能得到高弘图、张慎言、吕大器和姜曰广等一大批明官僚的支持,但缺乏军事力量,不敢北上与农民军交锋。在淮、徐一带阻挡农民军董学礼部的明总督漕运巡抚路振飞,手下的明兵大多是坊集的民兵。只要董学礼部得到增援,很快就能击溃路振飞的军队,从淮、徐南下。左良玉奉崇祯诏命镇守武昌,统治着湖广一带。他乘李自成远去陕西、山西,在二三月间进攻鄂北地区的农民军。崇祯在二月诏征天下兵“勤王”,左良玉不肯出兵赴援北京,却被崇祯封为宁南伯。在明南方统治集团中,左良玉的军事实力最强,拥兵二十万,但“多乌合,军容虽壮,法令不复相摄”。这支军队不但遭到马士英的忌恨和排斥,也不能为史可法所用,并且自朱仙镇败后,有畏惧和回避李自成军队的心理。农民军自淮、徐进取江南,即使不能招降左良玉,也不会受到这支军队的阻击。处在南京史可法和武昌左良玉之间的是明风阳总督马士英,他除有一些贵州兵外,主要依靠总兵黄得功的支持。黄得功在二月同样不肯出兵“勤王”,也被封为靖南伯。马士英与阉党分子阮大铖深相结纳,既反对左良玉,也排斥史可法。马士英的兵力比史可法强,弱于左良玉。以黄得功而言,所部不过数千人,经不住李自成大军的一击。高杰自山西蒲州南逃后,“沿途大掠”,江南北大震。刘泽清在山东不奉诏“勤王”,“大掠临清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这些明军此时不受任何约束,只知道抢劫焚杀,并无与农民军作战的斗志。分裂、混战和虚弱的明南方统治集团不但担心大队农民军的到来,风鹤为警,而且还担心江南各地佃户、奴仆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暴动。这类事件很多,如在太仓,“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杰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各置兵器,先造谣言,如鱼腹陈胜王故事,至于八月中大举。”在五月福王政府成立前,乌龙会人受到明军的攻剿。周锺所说“江南不难平也”,不是虚语。农民军大队人马从山东南下,在江南人民的配合下,会很快的攻占明南都,迫使明将领纷纷投降。农民军将在南方建立农民政权,与中原,西北地区连结起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兵力。留守北京的农民军仍将防御这座都城。不管清军的袭击和吴三桂的进攻会造成什么结果,农民军都不会遭到山海关之战的严重挫败。但李自成没有采取派大军南下的步骤,也没有在北京稳坐不动,决定暂停登极,先东征吴三桂,把农民军进攻北京的战略性错误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到了这一步,农民军的失败就不能避免了。关于李自成东征吴三桂前的状况,有的记载说刘宗敏等人“耽乐已久,殊无斗志”。事实是农民军从三月十九日进城,到四月十三日东征,只住了二十几天,不能说过得“已久”……而这二十几天的时间主要也不是用于“耽乐”,刘宗敏等人在山海关之战时仍然“死斗”……并非“殊无斗志”。记载又说:“关报既急,牛金星置酒集刘宗敏、李过、李岩、李牟、谷可成、白广恩、左光先、黑云龙、官抚民议出师,仓皇未定。营中诸贼大惧,私相问卜李闯有成否?闯王登极尚延几年否?出师不为关兵所杀否?得卜不吉,多涕泣。”这大概是封建文人为李自成编排的一次占卜场面,编得未免不合情理。因吴三桂虽然到处散布讨李自成的檄文,但他的实际兵力显然弱于农民军。农民军自进攻北京以来,节节胜利,士气甚盛,怎么会惧怕吴三桂到“涕泣”的地步?农民军首领们对东征是有不同意见的,但这不等于是恐惧。如果农民军首领们对吴三桂不是轻视而是恐慌,东征的事就搞不起来了。降清的明官僚刘余裕七月上清廷的启本说:“闯贼亡败,亦因于彼轻恃其强盛”。这种说法比较符合事实。李自成有些过于为吴三桂的檄文所激怒,也过于相信自己能迅速取得进攻山海关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