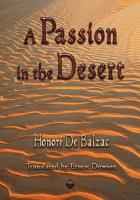萧老太爷头一栽,病倒在破草房子里。
老爷子赶车时受了风,岁数又大,不多时竟烧得人事不知。
一大家子人站在院里无甚法子,只能拿着热水不断地给老爷子擦着身子。
“大哥,求求村里的赤脚医再来一遍吧,万一父亲还有救呢?”萧涣然的爹爹萧天涟在院里走了几个来回。
“老二,赤脚医说爹莫得救了,再央来也没用。”
“那赤脚医怕爹断在他手上,跑得比脱了鞘的驴子还快。”萧家老大萧天澄扶着院里的石磨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如之奈何啊。
“老爹啊!”萧天澄终没忍住掉了眼泪。
“老爹啊!你可要挺过来啊!”萧天澄又一声长嚎。
“别哭了,别哭了,还没死呢,哭丧呢!”萧天涟又走了几个来回,不耐烦地朝着大哥吼道,却也红了眼眶。
挨着批斗、流放劳改全家都没掉一滴眼泪的萧家人此时却期期艾艾地哭了一院子。
萧涣然站在院子里安静地望着哭了一院子的人,转身狂奔出了院子。
“医生,医生!”萧涣然敲了赤脚医生的房门。
“什么事啊?”里面响起了移开门栏的声音。
“你救救我爷爷吧!再去看一眼吧!”
里面瞬间安静了下来,接着一阵响动,人似乎已经离开了门边。
“你爷爷我救不了,回吧。”人声传了出来。
萧涣然不再敲门,又跑了起来。
“管事叔叔,管事叔叔!”
“什么事。”村里管事的开了门。
“我爷爷病倒了,赤脚医说救不了。”
“等天亮了驾车去城里吧。”管事的说。
“管事叔叔,我爷爷可能熬不过今晚了!”萧涣然急了。
“那也莫得办法,晚上走山路太险了。”
院内有响动,一个老者从院里走了出来,扶上门边。
“老三,你回去。”老者说,管事的转身进屋了。
“小娃子,你爷爷怎么了。”老者摸了摸萧涣然的头。
“老爷爷,我爷爷受了风,烧的倒在了地上,村里的赤脚医说他过不了今晚了。”萧涣然抬头看着老者。
“这几年城里来的总有这样的,大抵都要鬼门关走上一遭。我给你出个法子,是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法子,可不保准能救得了你爷爷。”老者微微一叹。
“老爷爷您说,我爷爷就算真的到了命数也是赖不得您的!”萧涣然急忙说道。
“村东儿的后山上长着刺喇喇草和忍冬藤,你采回家叫上老爹搬个大缸子,教你阿爷坐进缸子里。”
“缸子里放着烫水,把喇喇草浇上老酒捣成汁水,忍冬藤和上温温的水砸成汤,一半兑进缸子里泡着。”
“另一半给你阿爷灌下,先灌混着喇喇草的老酒,半个时辰之后再灌混着忍冬藤的水!”
“老爷爷,忍冬藤我认得,赤脚医让采过给二嫂嫂治晕,喇喇草是何药草。”萧涣然急的脑门冒汗。
“就是山上缠着剌腿,茎上生着毛刺五片叶的野草!”老者大声地说,萧涣然拔腿就跑。
“小子,村里的劳改犯总有几个要历你阿爷这一劫,心火!心病还需心药医,告诉你老爹解解你阿爷的心结!让他好好宽宽心!记着点!”老者一面喊着一面关上了糟木门。
“记住了!谢谢您!老爷爷!”少年的声音远远传来,少年的身影已经逐渐消失。
老者在门后沉沉地叹气:“这世道还要苦多少人啊!”
“爹,您这话可不能在外面说。”管事的似乎一直都在屋内听着外面的话,出声提醒自己年逾古稀的老爹。
“知。”老者答应一声,踏过门槛回屋。
......
......
山间的夜里静极了,月光衬着黑色半枯枝干冷肃地悬在林上。
萧涣然倏的想起前几日村口老张家饿死的孩子挂到了东山的林子里。
这样饥荒的年头谁都不能保着自家的娃子能活过冬天。
一袭不论冬夏的破布衣衫,山上的树皮野菜,这样贫苦的日子注定了一场风寒便可以轻易要了人的性命。
何况这是流放劳改的村子,比起他处更要穷苦。
传说年纪小的娃子病死后怨气太大不能转世,只有挂在林子的高处吸收了日月精华散了哀怨才好去投胎。
村东的这片林子在这大饥荒的年代里便受到了村里许多人家的爱戴。
萧涣然瞅着脚下的草全身发寒,据说死过人的地上花草会立起逐渐变成人的模样。
还好,林子里的草都老老实实的爬伏在黑色的土地上。
可萧涣然又想了,就算是遇到了怨鬼,他也必然要找下去的。
哪怕他被怨鬼勾了魂魄,爷爷的魂魄也定然是不许黑白无常收了去的。
爷爷是家里的脊梁。一家人背井离乡被放到乡下时,就是因为站在门口的爷爷说了句:“总还是要回来的。”萧家老小便一滴眼泪都没流,毅然决然地转身上了路。
现在的萧家不能没有爷爷。
这处忍冬藤是村里人故意留着医治大病小情的,唯独喇喇草是平日里众人走路都嫌缠脚的。
如今这漆黑的晚林里可何处去寻。
对了,对了,对了!
是这样!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