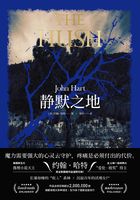贝菲猛地跳起来,拉开门,却见杨越进退两难地站在门口,远远的丁嫂过来朝她问:“贝小姐你在房里啊,你订的机票,少爷让我给你拿过来。”她低着头,不愿让人看到她脸上的泪痕残迹,哑声和丁嫂说了谢。杨越仍倚在门边,伸手欲扶她——看上去她像是一触便要倒,然而他手刚伸出去,贝菲便触电般地缩开,戒备地问:“你来做什么?”
“以后,”他亦嗓音喑哑,“以后你会遇到更好的人。”
“你来就是要说这些?”贝菲哂笑道,转过身往里走,双脚却直发软,不得不探手扶着床。杨越跟进来扶住她,她想挣开,却使不上劲,坐倒在床上,自嘲地问,“你不是不甘心吗,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会不会畅快很多?”看我像傻子一样,你三言两语,我便飘洋过海来寻你,这样的狼狈模样,会不会让你心甘得更彻底?
“我,”他的声音软弱无力,“我不值得你这样。以后……以后你总能遇到……”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下一个十二年,去认识第二个人,陪我去新藏线,带我去拉萨……什么都没有。”她语音无力,却格外的平静,像说一件于己不相干的事。
“不会的,凌少他,”他惶急地解释,贝菲却被激怒:“跟你说了我和他没关系!我不用你这样可怜,我没人要,也不需要你帮我找下家!”
她喘着气,眼红红地瞪着他,杨越哆嗦双唇,不知从何解释起,只茫然无依地望着她,进退不能。
“我不是可怜你……”他绞尽脑汁,不知如何劝解她,老半天才为难地说,“凌少……我觉得他是认真的……”
贝菲陡然安静下来,坐在床上紧紧地盯着他,杨越回避着她的目光,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不停地变换着交握的姿势,他皱着眉不知道该继续说些什么。贝菲恍然间明白了什么,冷冷地接下话头:“而且他有钱还有势,他逼你了是不是?”
杨越一惊,片刻后急忙否认:“没有,没有,他没有。”
“看着我。”贝菲冷冷地盯着他,早知道杨越不是这样决断的人——也许这不能算优点,但他确是从小就不记仇,即使是曾笑话他没有父亲的同学,如果别人来请教他题目,他也从未拒绝过。他总是委曲求全,当年夹在她和母亲之间,也总是两面逢源,只希望大家安安稳稳过日子。这样的人,从来只记得别人对他的一点好。
“看着我,你根本就不会说谎,他都开了些什么条件,送你去德国读书,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凌千帆开的条件,还是他姑妈?”
杨越摇摇头,极力地否认,然而他从来就不善于说谎,三言两语或许还能瞒得住贝菲,现在却是说多错多,索性沉默。他紧捏着拳,骨节分明,一看便知是在天人交战中,许久之后他才低着头愧疚地说:“他们没逼我,是我自己愿意的,我想去慕尼黑继续读书,可是我两年没进医院,再申请也不容易。这不是凌少的意思……你要知道,我如果得罪凌家,就算回北京去,也没有医院敢收我了。”
“不会说谎就不要学人装伟大!”贝菲怒气冲冲地从床上跳下来,她恨不得戳着他的鼻子问问他脑子到底长到哪里去了,他以为把自己编排得这样懦弱不堪她就会相信他的说辞么?他以为她贝菲是这么容易被骗到的人么?他以为她可以被当作一样东西这样礼让来礼让去么?
杨越你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傻瓜!她真想让他自己拿手术刀给自己开个颅,看看里面究竟塞了些什么东西。她扭开门锁准备去找凌千帆算账,然而拉开门的瞬间她就清醒过来,回过头来看到杨越焦灼的眼神。他在担心她,她知道的,天下之大总有一个小医生能混口饭吃的地方,他担心的是她——凌玉汝当年如何对许隽一家,他或许并不知道,然而做了两年的家庭医生,凌玉汝的为人他总该心里有数的。
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不怕,我光棍一个烂命一条我不怕,贝菲这样想。她不明白这件事到底是凌千帆的意思还是凌玉汝的意思,或者是谁的意思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和杨越确实谁也惹不起凌家。说一句有骨气的话是最容易不过的,可骨气不能当饭吃。
是凌玉汝给杨越开的条件吗?照凌千帆以前的描述,像是凌玉汝的手段,可是……许隽的父亲是个地方交通局长,凌玉汝尚且认为不配,今日的凌家又不同往日,她这样朝九晚五的小虾米,又怎能入凌玉汝的法眼?
那是凌千帆啰?她也不愿相信,固然他确实用尽一切可挽回的办法,希望她留在他身边,然而他对她向来是君子坦荡荡,岂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要挟杨越?
脑子里却分明闪过某天凌千帆极臭屁地指点她:“不懂得雷霆手段,怎配有慈悲心肠?”她忘了具体是为什么事,现在想起来浑身不寒而栗,凌千帆也懂得雷霆手段吗?下午她还觉得自己很了解凌千帆,现在却突然丧失那些笃定。
“我不会去找他们摊牌的,”她担心地看着他,杨越舒了一口气,她半晌才又低声道,“你好好照顾自己。”杨越欲言又止,然后重重点下头,他欲言又止,似乎不知道要和她说些什么,贝菲直觉悲愤——却无计可施,她不敢再牵累杨越,只能看着他一步步远走,每走一步她的心便往下沉了一分,是凌千帆吗?是凌千帆吗?她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他的手笔,可她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
她一声不响地蹲在门口,没察觉过了多久,听到凌千帆的声音:“蹲在这儿干嘛?我正找你呢。”
“找我?”
“是啊,以前我们说过交换明信片看的,你后天就要走了,再不给你看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凌千帆的笑容完美无俦,她努力想从中发掘一丝卑劣的迹象,却怎么也找不到,倒是他好奇地问:“你脸上怎么红红的?”
气红的,她想,却笑嘻嘻地答道:“晚上喝了酒吧,我看你开的红酒挺贵的,就多喝了几口。”
凌千帆伸伸手,大约是想试试她额上的温度,伸到半空却停住,醒悟到他已没有这样的资格,又生生地收回去。贝菲跟着他上楼,他的房间简约中不失精致,另一个特点是干净,干净得不染半点纤尘。贝菲从他手里接过一沓明信片,看纸面便知有些年头,却保存得十分平整,连个卷角都没有,显是十分珍惜的。
唐人街的青砖白瓦,西雅图秋叶飘零的雨雾,波士顿铅灰的海水,印第安人的遗迹,大峡谷的晨曦微光……轻狂年少时的色彩,如窗外被夏日午后阵雨涤荡过的青青碧草,不经意间展现着别样的鲜嫩,触到人心底很久未曾碰触过的地方。
她把明信片翻过来,纸背早已泛黄,陈旧皆如昨日的记忆,静静地停留一隅,在某个仲夏夜,一一陈列出来。密密麻麻的都是英文写的地址,因为是凌千帆寄给自己的,并没有任何祝词,只有时间和落款,右上角刚劲俊俏的一个个Lynn的签名,飞来晃去,错落缭乱。
桌上搁着杯咖啡,喝了一半,贝菲笑道:“大半夜的喝咖啡,还睡不睡觉了?”
凌千帆淡淡笑道:“我想用心尝尝,炭烧到底是个什么味。”
“尝出来没?”
凌千帆摇摇头道:“苦得厉害,你怎么就喜欢这个味儿?”
贝菲端起来把玩咖啡杯,慢慢地饮下残杯,凌千帆那双秋水横波目立刻挑了起来,闪着危险的光,颇带玩味地笑:“我喝过的。”沉淀下来的苦意在她舌尖上打转,明明是极苦的咖啡,却从胃里升起醉意。她仰着脸,朝他微微哂道:“你不就是想这样么,现在如了你的意,不好么?”
凌千帆皱皱眉,眼带询问,贝菲斜着眼挑衅地瞅着他,凌千帆若有所思地问:“我刚刚……听说杨越要去德国?”贝菲凑到他跟前,笑得有些讥讽,看在他眼里却别有风情,他微叹一声站起来,自嘲道:“贝菲,被人当备胎的感觉不好。”
贝菲神色微嘲:“你是备胎?”
凌千帆低眉敛目,笑得极是无奈:“难道不是吗?”他双手叉着腰踱了几步,笑得越发无奈:“感情这个东西,真他妈的——”他顿顿又笑道,“真他妈的犯贱,你为杨越犯贱,我为你犯贱,”贝菲托着腮帮子朝他直笑,他退了两步又冷冷自嘲道,“问世间情为何物,不过是一物降一物,这句话说得真他妈的对!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对吧,我凌千帆万花丛中过,结果栽在你的手里,这是报应,报应!”
贝菲咧开嘴笑:“凌少,做人不要太贪心,你要我回来,我回来了,你还嫌不够?”
凌千帆眯起眼,盯着她老半天后问道:“你什么意思?”
贝菲转过身来,靠在他的书桌上,明知道不该触怒他,却压不住那股怨气:“我知道我不值钱,承蒙凌少你看得起,我们不如明码标价。我要的不多,就你原来开的条件,送杨越去慕尼黑大学,我再加一点,从此以后你不许再动他一根指头。他要少一根寒毛,我就跟你拼命,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给盛遂波我只下泻药,你要是再动他,就没这么简单了。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说得出做得到!至于你要什么我不知道,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都随便你,什么时候玩腻了,我也绝不纠缠你,你看这个交易如何?”
她觉得自己真醉了,凌千帆原来极柔的眉线都锋利起来,他发起脾气来是什么模样?他的雷霆手段又会是什么模样?他会不会把她也碾碎成泥,挫骨扬灰,然后轻飘飘地弹弹手指衣袖,不沾一点灰尘?
凌千帆眯着眼,抿唇沉默良久,最后却笑起来:“我姑妈答应送杨越去慕尼黑?他答应了,他又不要你了,所以你就来找我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