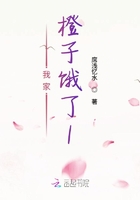他慢慢敛起笑容,一言不发地盯着贝菲付钱、上车,夏日的风打在脸上越来越痛,敞篷跑车在墨尔本一望无际的广袤原野上奔驰而过。她没法从凌千帆脸上看出什么,只看到时速表倏地转了大半个圈,逆着的风夹着暑气打在脸上,力度丝毫不亚于婺城冬日凛冽的寒风,贝菲这才明白,为什么别人说敞篷车是看着拉风,开着受罪。
齐刷刷的两排布里斯班红胶木在视野里逐渐清晰,凌千帆减缓车速,在临近花田时终于停下,他笑得有些疲惫,向贝菲轻声问道:“以后有什么打算?”
贝菲笑笑,凌千帆果然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手腕精明,他能利用的资源多不胜数,每一样都足以引诱到她。然而当这一切摆在天平上仍无济于事时,他亦能十分平静地接受,不至于为这点小事纠缠不清。她摇摇头道:“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不像是这么没计划的人。”
贝菲不以为意地笑笑:“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会先回婺城把工作交接清楚的。”
凌千帆偏过头来瞅着她,一双桃花眼竟望不见底的深,唇角弯起微涩的弧度:“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输,”他双唇微动,却静默良久才继续道,“我问这句话你也许会笑我,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你真的觉得值得吗?”
“我要是说没有值得不值得,只有愿意不愿意,你会不会觉得很矫情?”
凌千帆嗤了一声,萧索摇头:“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找我。”
这大概是所有分手词中最客套而绅士风度的那一种,贝菲也就同样客气地点点头:“你呢,接下来什么打算?”
“也差不多该回婺城了,千桅一赌气就跑过去,我还没来得及劝她。”
还真是个二十四孝,贝菲羡慕地笑道:“你们兄妹感情很好。”
凌千帆摇摇头:“都是被我惯坏了,也二十多岁了,还这么不懂事,姑妈那天还说她,她要有你一半懂事,我们也不用操这么多心,结果她就翻脸了。”
她听出他话中的欲言又止,也许他也是需要一个人倾听的,也许他辛辛苦苦地维护着每个亲人已经有些吃力,也许他也渴求一个出口,不过现在的她并不适合这个角色。恍惚间她竟有些同情他,在别人看来自然是风光无限,其实背后的辛酸又有谁会知道,以前她也许会揶揄这不过是有钱人锦衣玉食的烦恼,现在她却不得不承认,或许凌千帆并不比她活得轻松。
他时时刻刻都要顾及爷爷姑妈妹妹的心情,却找不到一个人来认认真真地倾听,他究竟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希望和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如此等等。
这样的凌千帆,和世上芸芸众生并无多大分别,他需要被倾听,需要被关怀,需要被爱。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终其一生,也不过是期望爱人,与被爱。
可惜她不是圣母玛利亚,她不能普渡众生,凌千帆以后还会遇见千千万万的人,而杨越只有她一个。
她打开手提包,取出洗干净叠平整的浅棕色格子手帕递还给他:“我洗干净了,谢谢。”
回到凌宅,杨越问她此行收获如何,贝菲思索半天,一时答不出来有什么感想——如同路上的旅人,以前只能遥见云端的雪峰,如今却能走到山脚下,仰望群山巍峨,心中自然升起无限的雀跃,想要一鼓作气爬到山巅,俯视苍茫云海。
却不知如何形容,因为知道大约已不会有那样的机会了。
据说今天凌兆莘钓鱼收获颇丰,连凌玉汝都兴致勃勃地要亲自下厨,凌千帆过去给她打下手。于是杨越陪着贝菲在农庄里四处游转,不知名的鸟雀在布里斯班红胶木上栖息,偶尔窜出来从人的头顶掠过,迎向西天的彩霞。花田里的兰叶随风荡漾起来,姿态摇曳,贝菲忍不住感叹:“真漂亮,这么大一片,不知道要费多少工夫。”
杨越不知在想什么,愣了片刻后笑笑:“从国内请了不少养兰的专家,我听工人说,前前后后花了八九年的工夫,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好像那个时候凌爷爷中风,凌少才把全家迁到澳洲,这里环境比较适合疗养。”说完他又笑道,“凌少真是个孝子。”
八九年,算算时间亦差不多,孝子,可不是么,贝菲心底暗嘲,不愿在关于凌千帆的话题上打转,她扭头问:“我要订票回去了,你这边收拾好了就回婺城找我,怎么样?”
杨越停住步子,咕哝了一句什么,像是德语,贝菲没听清,问:“听不懂德语,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我在想……也许去慕尼黑的医学院是个不错的选择。”
贝菲微讶,旋又想到可能是凌家有相熟的医学教授肯给杨越写介绍信,她虽不愿再承凌千帆的情,不过事关杨越的前途——怎么说杨越也给凌兆莘做了两年医生,这倒扯不到她头上来。“那也不错,”她点头笑道,却见杨越若有所思,欲言又止的模样,笑问,“你担心我?没关系啊,反正我也没去过欧洲,不如跟你一起呀……不过你得养我,我要趁此良机好好玩遍欧洲!我要去威尼斯、罗马、米兰,还有还有……”
看杨越凝眉不语,贝菲忙又摆摆手笑道:“吓你的,我会赚钱的,哪儿能饿得死我呀?不过——我们要一起出去的话,是不是得先结婚,再申请配偶签证?我以前没申请过这个,”她还在滔滔不绝絮絮叨叨地罗列以后可能碰到的各种问题,忽被杨越截断话题:“不是我们,是我一个。”
他垂头转过脸去,视线投向无垠的天际,太阳没入地平线,地平线上的天空由赤红转为青灰,仿佛燃尽的火堆,一点一点,消失最后的温度。
“杨越你再说一遍?”
他转过脸来,带着残酷的平静:“不是我们,是我一个。”
贝菲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话,费了好大劲儿坐到田埂上,问:“你什么意思——那你为什么要我过来?”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杨越踱开几步,似在斟酌词句,“我不甘心,才和你说气话,我真没想到你会来。所以……你真的找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感动,但是……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恨你。”
恨总是和爱相连的,贝菲终于明白他的意思,因为爱已消逝,所以恨也消逝。
而他们之间那么多的难以割舍,不过是不甘心而已。
时间是医治一切的良药,即使他们曾共同度过那些年少的日子,即使他在她到来时曾显得那样犹豫、期盼——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不甘心曾付出的迷恋、信任,却被她玩弄于股掌,所以徘徊踯躅,走不出这困局。等她真的到来时,一切如云开雾破,他才恍然曾狠狠捂住的伤口,骤然放开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痛。
“你这样,”贝菲惶急地笑,她直觉要找出什么来反驳他的话,却又找不出来,只得努力地笑,来掩饰这猝然而至的打击,“你这样,算是惩罚我?这样子……你就开心了?”
杨越双唇抿成一线,并不言语,贝菲只觉得狼狈——对,狼狈,她想,只是狼狈而已,她没有什么可伤心的,只是狼狈而已。她不断地这样说服自己,狼狈而已,这世上她仅余的最亲近的人,突然拒绝了她,她只是狼狈而已,没有伤心,没有伤心,一点也没有。
这是一件不值得伤心的事,既然别人都已经看开了,你还有什么必要苦苦抓住不放?她匆匆地跳起来往回走,杨越在后面叫了她一声什么,她也不回头,只朝后挥挥手笑道:“没事没事,我知道了,我回去收拾行李。”
进门时撞到凌千帆,差点摔个踉跄,凌千帆好笑地拎起她:“走路看路,还没过年,别给我行这么大礼。”
凌千帆是出来叫她和杨越去吃饭的,晚餐是全鱼宴,凌玉汝对贝菲很是热情。明明贝菲早上已说过要订票回婺城了,谁知凌玉汝仍是一脸惋惜,又支使凌千帆:“难得来一次,为什么不多玩玩,你明天带小菲去悉尼玩,别跟我扯工作忙!”
贝菲心道凌姑妈你这和我玩的是哪一出,这么快就从贝小姐升格为小菲了。凌千帆也极疑惑地在贝菲和姑妈之间不断瞟来瞟去,含含糊糊地唔了一声,赶紧扯开话头。只有杨越默默地吃饭,十分超脱的样子,贝菲偏过脸不去看他——心底又不断地唾弃自己,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就是被人拒绝了嘛,地球照样转动太阳照常升起,又不是没了谁就活不下去!
草草吃完饭,逃也般地回客房,也没开灯,就坐在床边的地毯上——跟凌家人吃饭是很累的事,尤其是还有杨越在场。回到房里只觉得浑身虚脱,像抽过水一样,四周黑沉沉的,像有万钧之力压下来一般,她整个人也被压成一张纸片,轻飘飘的,连落脚之处都找不到。
真的再无落脚之处了,像习容容说的那样,她总是吵吵嚷嚷着要嫁人,要成家,其实说到底不过是想有个落脚之地。世间万苦,无一样比得上寄人篱下,这样的苦处,是没有寄居生活的人所无法体味的。倒不是说所有人都像她大伯那样没良心,而是那种漂泊无根的感觉,无处可言说。
和杨越格外亲近,大约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那些可以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同学们眼里,他们都是异类。
从未想过,杨越会第二次放手,且这第二次机会,是她亲手递给他的。
她伏在床头,肩头微微耸动,却哭得艰难,眼泪也断断续续。明明有决堤的悲伤想涌出来,却总有层层阻挡,让她连哭也无法哭得畅快,呜咽也发不出声音,原来这么多年,她连哭都不会了。
“杨医生,你也来找贝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