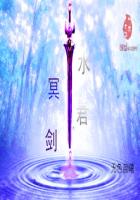天光刚亮暨晚便醒了,然,越不想发生的事情越是发生了。
怀里的人面色潮红,浑身发烫,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是沉睡不醒的模样,暨晚不懂医理,却也知晓墨白生病了。
心中慌乱,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听她开始喃喃低语,迷糊不清,把耳朵靠近,才听清她在轻唤‘君上’。
羲和斋,千城一袭青衫坐于矮几前,矮几上的水壶冒出热气,执起水壶倒入紫砂壶里,茶叶入水后清香弥漫。
千城动作闲适,神情怡然,一头如墨黑发倾泻如瀑的垂在青石地板上,他推了一盏茶到矮几对面。“如何?”
墨白喝了一口,一双绿眸窘迫。“烫。”
“不懂辨味。”千城看了她一眼,语气中却无责怪。
“君上。”墨白蹙眉,起身跪坐他身边,挽上他的手臂。“我不想学茶艺,太难。”
千城只回转身问她。“那你觉得什么不难?”
君上教自己术法,觉得难,君上教自己布阵,觉得难,现在君上教自己茶艺,还是觉得难,墨白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不难的,于是撒娇耍赖。“君上,要不明天再学?”
千城也不恼,看着她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墨白眨巴着大眼,狡黠道:“那不学茶艺好不好?”
“好。”千城起身,牵着她走到书房。“我想练字是不难的。”
墨白一下气馁了,其实她就是想玩,不想学东西。“可好多字认得我,我却不认得它们。”
“所以要学。”千城微笑,把她带到书案前,铺上宣纸,研墨调水,毛笔蘸了墨递给她。“现在,我说你写。”
墨白执笔,只听千城说:“水,有容可纳百汇,有养可育万物,翻腾可惊巨石,狂躁可灭生灵,柔且刚,遁之于水,五感六识闭两感三识,即......”
墨白写着写着便不知道该怎么写了,她抬头。“君上,遁字怎么写?”
修长的手指握住她,一笔一笔落成遁字,千城身上淡淡的青草气息,墨白只觉清幽怡神,舒适无比,贪婪的呼吸着,不自主的说道:“君上,我后面的字也都忘记了。”
无奈,千城只好握着她的手,把水遁术的法诀全部写了出来。“你不愿意学东西,就多写字,这是水遁术,多写几遍你就记得了。”
自墨白上次落水后,千城便留心要把水遁术教给她,以免自己不在她身边时发生意外。
“这是水遁术?”墨白还不知道自己写的是法诀,她惧水,却也好玩水,她笑起来,浅浅酒窝浮上脸颊。“那我就不会被淹死了,真好。”
本是开心,不想千城严厉说道:“不得胡言!”
君上少有厉色的时候,墨白不明白自己哪里说错了,讪讪抬眼看他的神色,却见他目中有了温和。“墨白不会死。”
知他没有怒自己,墨白又撒娇。“君上最好了。”
暨晚耳边,墨白断断续续呓语。“君上,我会好好学......君上,不要恼我......”
想是睡梦中见到了君上,暨晚轻叹。“墨白,连生病了也如此记挂他么?我一直陪在你身边,你可有在意?”
不由伸手抚她的脸,却发现已经滚烫,暨晚知道不能再耽搁,连忙背起她往前面赶路,希望快点找到一个城镇,寻个医师给她诊治。
背上的人继续轻唤君上,暨晚难受不已,可当墨白变得安静又不免担心,时不时要看看她的状况再继续赶路,一颗心竟是浮摆不定,只为她纠结。
出了树林,自然又遇到许多流民,这些流民不知道,其实后方蓉城已被占据,天下之大,他们何以为家?
次日,黎明时分,暨晚背着墨白赶了一天的路终于到了淮城。
淮城本被叛军攻下,当时城中百姓没来得及逃走,也没负隅反抗,是以叛军没有屠城,又因不是兵家重地,只留下五千将士驻守,便前往蓉城攻打,后来援军赶至收复了淮城,现已恢复了正常生活。
不得不说是好运,否则叛军驻城,他们是进不了城的,城中只有一部分害怕的百姓逃走,大多还是留在了自己的故土。
暨晚蒙上墨白的眼睛,背着她进了淮城,遇到守城侍卫盘查,就说她眼盲,而且她一身滚烫,脸色发红,一看就知她患有烧热,所以,进城并没有遇到阻碍。
不管肚中饥饿,暨晚先找到一家药堂,医师一触墨白额头,就道:“哎哟,烧得如此滚烫,脑子都烧糊涂了罢。”
连忙叫人打来冷水,吩咐暨晚时时更换,暨晚这才知道该怎么照顾墨白。
其实,魔族人少有生病,加之暨晚生于皇族,一切皆有人照料,不曾病过,他只受过几次伤而已。
不多时,药堂的医师端来汤药递给暨晚。“先把这药喂给她喝了。”又拿出打包好的药材吩咐。“然后把这药拿回去以小火煎熬,四碗水熬成一碗方可,一副药熬五次,一日服用三回。”
“多谢。”暨晚接过药碗,小心扶起墨白,让她枕在自己肩头,才开始喂药。
药苦,墨白烧得迷迷糊糊哪里喝得下,几乎喂多少吐多少,暨晚只好把药含在嘴里,强行灌她喝下去。
唇瓣相触温软,这是暨晚第一次如此亲近她,曾无数次幻想的情景,此刻却是以这样的方式,无关亲吻。
药汁的苦味,及不上心里那卑微索取她一点点爱意的苦涩。
药师见他俊朗不凡,却对一个瞎眼的伴侣还能如此的好,不由宽慰他。“只是烧热,不是什么大病,回去好生照料,不日便能大好了。”
“有劳了。”暨晚付过诊金药资,背上墨白就近找了家客栈住下,安排好一切才顾得上吃饭。
一顿饭还为墨白换了三次毛巾,不放心把药交给客栈的人熬制,自己借来小炉,一边守着熟睡的墨白,一边守着药炉。
第一晚,墨白依然沉睡,第二晚,仍旧说着胡话,自然,那些呓语都是千城,直到第三天她的烧热才退下,幽幽转醒。
墨白未曾生过病,此刻只觉浑身无力,想要起身都难,一旁守着药炉的暨晚见她醒来,忙移步床头扶她坐好。“感觉怎么样,好些了吗?”
环眼四周,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房间,墨白想起先前她与暨晚躲在树林,后来睡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便问:“我怎么了?”
“那晚你受了风寒,就一直昏睡不醒。”暨晚取下她头上的毛巾摸了摸她的额头。“不烫了,看来烧热已经退下。”
原来是生病了,难怪一身无力难受,墨白说:“我们现下在客栈咯?”
“这里是淮城,曾被叛军攻下,又被援军夺回,应当会平静一阵子。”暨晚把她扶到床头靠好,径直端了凉好的汤药。“先把药喝了,你已经三日未曾进食,需吃些清淡的东西,我去叫小二送点清粥来。”
“嗯,是有些饿了。”墨白接过药碗,浓稠的汤药苦味弥漫,光闻着就觉难以下咽,真不知自己昏睡时是怎么喝下的。
暨晚回来,见她还没喝药,开口说道:“怎么还不喝,难道要我喂你。”
本是玩笑话,许是烧糊涂了,墨白张口就道:“那你怎么喂我的?”
暨晚默,耳根发烫,墨白才反应过来自己说话荒唐,他定是十分细致喂自己吃药,否则自己怎么会好?当中,难免两个人会靠得很近,思及此,端着汤药一口气喝了下去。
暨晚把碗拿走放到桌上,再给她倒了杯清水漱口。“你病后初愈,不宜赶路,况且也不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否会有战乱,且在这里休养几日再做打算,你看如何?”
自己现在连动一动都觉吃力,若路上再遇战乱,如何能全身而退,纵然心急,墨白也明白不能任性。“好,听你的。”
暨晚扶她躺下。“那你在房中好好休息,天凉了,我去街上买身厚衣裳,顺道打听打听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想来是这几日他一直在照顾自己,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买,而自己的一双绿眼,实在不宜在外面走动,墨白点头。“好。”
在暨晚快出门时又叫住他。“暨晚,路上小心。”
乱世之下,世人皆如浮萍,他们两人亦是。
他们在危难中相互关心,这便够了,暨晚心里说不出的开心,脸上却是淡淡一笑。“我很快回来,别担心。”
他是魔尊长子,在权力斗争中习惯了喜怒不形于色,现在的他走在街上却是笑意盎然,走进一家服饰店,见一袭水绿长裙,颈间一圈白色毛领,当下就觉得穿在墨白身上一定好看,一问价钱竟要十五两,比寻常衣服贵了近十倍,看了看为数不多的银两,往后不知道还会经历些什么,不过仍是决定买了下来,自己则随便挑了一件长衫,和两件帷帽披风。
出了店门,又见街边小贩卖簪花,几个姑娘站在摊前挑来挑去,虽没见过墨白戴什么首饰,但这种簪花十分好看,暨晚便凑过去,想给墨白也挑一朵。
将将走近,就听见几个姑娘的闲聊。
“知道吗,子雉将军带援军打过来了,听说不到两月就能带兵到我们淮城。”
“当然知道,子雉将军所向披靡,已经收复了十几座城池。”
“你们的消息都太不灵通了,知道子雉将军已经打到哪儿了吗?”
几个姑娘都看向最后说话的这位姑娘,眼神迫切,暨晚也盯着她,不为别的,只为她提到子雉,千城君上座下的四弟子,便名子雉。
看见他们的神情,那个姑娘满意的笑了笑。“已经打到濮城来了。”
“当真?”
“自然当真,我兄长在他部下当兵呢,今日才收到了兄长的家书,岂会有假。”
“也就是说,不出月余,子雉将军就能到我们淮城了?”
“......”
后面的话暨晚没有再听,簪花也没再选,却是快步赶回了客栈。